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6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64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叶圣陶和黎锦熙这两位伟大的教育家,提出了在世人看来似乎相左的观点,几乎困扰了整个教育界,时间波及20世纪中后期,可能还有延伸。叶圣陶以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显然在强调“读”;黎锦熙提出了“写作重于讲读”,这肯定是在强调“写”。但是,当我们审读这两位大家在各自语境中的思想时,会惊奇地发现,其实他们是在谈论同一个话题,即针对语文教学问题,读是基础,写是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手段。只是我们误读了他们的思想。
一、叶圣陶的写作观
1.读什么:“普通文”
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观,是针对20世纪初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他认为,教育之本是“应付生活”、“应需”,即追求语文教育的“实用”、“应用”价值,实行文化扶持,使语文普惠于全体国民的生活。基于此,他奠定了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核心范式: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实用—吸收型”语文教育范式①。也因为这样的范式,为“应付生活”之需要,叶圣陶十分重视“普通文”,他说:“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②叶圣陶的这一要求,将阅读、写作与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为生活需要而读,为生活需要而写,为生活需要而将读写结合。这无疑是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大叛逆,是一种开创性的思想。当然,正因要面对“普通文”,学生的阅读状态可能会要被动些,因此,叶圣陶更关注“阅读”,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1955年8月,叶圣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向北京市语文教师作《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专场报告,提出了语言、文学分科的必要性,以及文学的重要性③。不管是自愿还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叶圣陶这一认识的转变都是巨大的,原先的“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而此时的“文学”成为了主要内容。而后来的众所周知的语文课程的快速转向,其实又回到了叶圣陶原先所设想的路途上。
2.读与写的关系:阅读本位
我国的传统教育注重写作,阅读的目的,就是最终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是,“从清末民初开始,语文教学便表现出逐步侧重于阅读,教材以文选为主体,教学中以对文选的讲解为主。”④叶圣陶显然顺应了这一形势,并建立了具有代表性的现代语文教育范式。也因这范式,“吸收”便成了语文教育或者写作的根本,叶圣陶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因此学生阅读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话也就没听人提起过。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写作程度有迹象可寻,而阅读程度比较难捉摸,有迹象可寻的被注意了,比较难捉摸的被忽视了,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⑤叶圣陶在此阐明了阅读与写作的功能与相互关系,并指出写作的“根”在阅读。叶圣陶在1962年提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他说:“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看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像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常常有人要求出版社出版‘怎样作文’之类的书,好像有了这类书,依据这类书指导作文,写作教学就好办了。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⑥在此,叶圣陶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阅读和写作不是两回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二是“怎样作文”之类的书,作用有限。
叶圣陶这种由先前的阅读“根”论到后来的“基础”论,完成了“阅读本位”理论的确立。“阅读本位”本是极深刻的认识,却在学校教育中显现了另一种情形:学校教师的强势地位,使得“老师教”大行其道,而“学生读得好”却日渐式微,“写”自然就没有了“根基”。
3.读与写的融合:教学方法
实际上,叶圣陶在1940年12月发表的其私拟的课程标准(正因为是私拟的课程标准,就更能体现其思想),正反映了其听、说、读、写全面结合的教学思想。
叶圣陶的《六年一贯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在“教法要点”中规定“精读部分”⑦:
⑴为养成阅读之优良习惯起见,每授一篇,必先令学生预习。预习之工作为:①运用工具书、参考书,以解决词语、典实方面的疑难,获得作者及文体方面之认识;②从作者的意念发展之途径,观及表达方法;③通读全文,由了解而进于领会;④解答教师所提示,或自己发现之问题,预备于上课时间讨论之,等项。
⑵学生预习所得,必令书于笔记簿,以备参考。(注:一般笔记簿仅书教师板书之注释与表解等,非学生自力攻究之成绩,殊未得笔记之用。)
⑶关于预习各篇之具体方法应有教师提示之。于初年级,提示务须详尽。由中年级而至高年级,渐次减少,期学生自为发现。(注:所谓具体方法,如疑难词句之摘出,参考书籍之搜取,作者身世之了知,时代背景之认识,文章组织与风格之分析等。)
⑷上课时应取讨论方式,就学生预习所得而讨论之。其有不合,则为之订正;其有未尽,则为之补充;其有弗及,则为之阐发。整篇由教师讲解之方式,足以阻遏学生阅读能力之发展,以少用为宜。
⑸讨论之结果,必令学生书于笔记簿,以与预习所得相比较。
⑹所授文篇,教师必为范读(语体之读法,以运用国语之腔调为原则)。并令学生于不妨碍他人工作之范围内,按篇诵读,不求强记而自臻纯熟。
⑺精读文章,应于相当时期予以复习,或取一组之文篇而复习之,或于各组中提出有关之若各篇,令为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
⑻随时考查成绩,其方法为:①讲解,②问答,③测验,④默写或背诵,⑤轮流报告及讨论,检查笔记等项。
我们看出,其“阅读本位”教学,并非“灌输性的讲读”教学,而是与听、说、读、写紧密结合的综合性的阅读教学,除了读本身的价值之外,主要还是指向写和说,尤其是写。也就是说,“阅读本位”意在强调学生“自力攻究”、“自为发现”、“讨论”、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并“书于笔记簿”的阅读姿态和阅读方式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一种读写结合的方式。
“阅读本位”教学,实际确定了学生的阅读姿态、实现阅读的方式和内容范畴,以及实现的条件。
第一,学生自主阅读姿态,也就是阅读取向问题。教学要求“必先令学生预习”,且随着年级的提高,讲解的“具体方法”要“渐次减少,期学生自为发现”。这都为学生的自由思考提供了便利,也为学生作真正的笔记提供了可能。叶圣陶还对“笔记”作了区隔,即笔记不是简单的记录,如仅“书教师板书之注释与表解等”,而真正的笔记,应是“学生自力攻究之成绩”,要达到“得笔记之用”的程度。
第二,实现阅读的方式:一是作学习性的读书笔记。学生读书,应将读书所得、疑问“书于笔记簿”,在课堂讨论后,将讨论结果再“书于笔记簿”,并作两相对照,发现差异,产生成功感。这本身就是写作的一种。二是阐释性的写作。教师还要在“相当时期”内,“复习”笔记,“或取一组之文篇而复习之”,“或于各组中提出有关之若各篇”,“令为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并写出评论文。这里的“复习”显然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学习和再发现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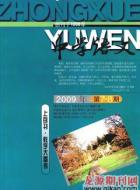
-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 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若干要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 王本华
-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 从钱梦龙“三为主”教育思想看新课程改革 / 潘冠海 陈 敏
-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 孔子的教育之道(七) / 韦志成
-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 语文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 何新华
- 化“综合性课程”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 陆 培
-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育观的影响探析 / 柯华桥
- 浅谈朗读在语感教学中的作用 / 王 颖
- “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知识更新 / 荣维东
-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 / 任明新
- 语文名师与当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建构 / 陈元辉
- 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歌的人生智慧 / 李晓颖
- 语文教育与人的完整性建构 / 赵 蕾 曹明海
- 经世致用与诗意人生 / 吴智勇
- 与心灵接触的情感教育:语文教学的灵魂 / 赵 蕾 曹明海
- 矫正中学作文的浮躁之弊 / 石修银
- “细读”举隅 / 史绍典
- 怎样才能达到议论的深度 / 朱庆和
- 新课堂中对文本主旨解读的反思 / 茹红忠
- 为高中作文教学号脉 / 侯志林
- 语文课堂设计的文本意识 / 武立伟
- 苍凉,抑或温暖的叙说 / 高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