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5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57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当孙绍振的学生至今已有30年了,时间太长了,感觉变得多少有点麻木、迟钝。可以述说的实在太多了,生怕漏失了什么,也担心无法写出先生的神韵,弄得自己无从下笔。同时又担心笔下会有所偏颇或溢美,在顾虑重重下勉强提笔,老是有言不达意、力不从心之感。
孙绍振先生的形象是很“洋派”的。鼻梁上架一副硕大的玳瑁眼镜,贝雷帽、西装,风度翩翩,举止潇洒,属于一见面就能让人感受到大学教授气派的那种。由于他的专业主要是“文艺理论”(说“主要是”,是因为他涉及的领域太多了,先教写作,然后研究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后来还成为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导师),而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基本是“舶来品”,所以作为这个专业的教师也就多少沾上了点洋气。而且他有多次国外游历、讲学的经历,眼界开阔。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始终是很前卫的。
但他“骨子”里是很“中国”的。他待人诚恳、热情,天生具有亲和力。对老师、同学、朋友,他都很念情谊。他的一位小学老师生活拮据,他得知后每年都记得寄一笔钱过去,希望老师晚年能过得宽裕些。在得知一位老同学病逝了,并留下累累债务时,他寄去了两万元。在钱的问题上他是很洒脱的,称得上“知足常乐”。面对晚辈和学生,他是仁厚亲切的父亲、兄长、朋友,不论是谁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有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哪怕办不到他也会竭尽全力。无论是与他过往密切的还是和他偶有接触的人,无不受到他学识和人格双重魅力的吸引,感受到他的仁爱与温情。但是嫉恶如仇的他对自己所不屑的人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可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也。
有一种人,经过岁月精心地镂刻磋磨,愈老愈显得优雅、雍容、爽朗,先生就是这种人。他年逾古稀心理上依然年轻、俊逸、豪迈。我与他相处了几十年,都没怎么见他发愁,也罕见他发怒,他总是乐呵着、悠然着。他心胸豁达、精神矍铄、头脑机敏。和他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他从不缺乏听众,因为和他聊天是快乐的。他是一个演说家,谈话高手,往往一聊起来就停不住:思维催逼着语言,雄辩簇拥着思想,幽默文饰着机智,口若悬河、滔滔汤汤、一泄千里。他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会老的。
先生原来只是我们的先生,而今已然成为全中国语文老师的先生了。多数语文老师认识孙绍振,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8年,先生以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发教育改革、高考改革之先声。与此同时,那场旷日持久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揭露出语文教育存在的种种积弊,其影响远远超越了语文学科,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和关注。就是从那时起,孙绍振成了这一语文改革大潮的风云人物,他和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遥相呼应,成为语文界瞩目的焦点。人们开始把眼光投向这位大学教授。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热衷于语文课改的中学老师而不知道孙绍振的,估计为数不多;将他视为老师和知音的则不计其数。
孙绍振祖籍福建长乐。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中文系工作一年,由于“反右”时期曾为“右派”辩护之旧账,被重新分配到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文革”时期被下放,1973年被调至福建师范大学,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横跨写作学、美学、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为当代学者所罕见;博闻强记、才华横溢、机智雄辩,令学界同仁折服,有报刊赞曰——奇才!
他确实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早年读过的诗文,至今还能背得琅琅上口。读中学时,有一次他和几个自认为聪明的朋友比赛,在考生物以前,只许看一遍书,看完后大家一起去玩,结果他考了99分,据老师说那1分是因为字迹潦草而被扣掉的。他现在还能流畅地用中学时修的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歌。他在“文革”期间靠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自学了英文,后来居然在美国大学用英文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文学。他才思敏捷,写作速度惊人。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朋友、学生都喜欢和他聊天;他还常被外聘讲学,时常出差,难得闲暇。尽管如此,他一点没少发表文章,书是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每年的研究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同行中都名列前茅。
他从不以“才气”自矜,而且对一些晚辈或学生,如颜纯钧、王光明、南帆、舒婷、陈仲义、陈晓明、谢有顺、陈希……称赞不已,说他们的天分都比自己高,他们的才华是他无法企及的,他自己只能算比较聪明一点的,他总是更多地看到他们身上的优点。认为唯一让自己感到自豪的是“识才”,能一眼看出初露锋芒的晚辈的才华。他曾不止一次说起对他们才能的钦羡,总是不遗余力地赞扬和提携他们。他在南帆刚开始写散文时,就发现了这位个性风格鲜明的散文大家。后来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读南帆的著作,写了《当代智性散文的局限与南帆的突破》《审智散文:迟到的艺术流派——评南帆在当代散文艺术发展上的意义》等论文,对南帆的“智性”和“冷峻”大加推崇;他对文学界新星谢有顺的关爱也是无微不至,学业、事业上的扶持不必待言,谢有顺刚毕业时曾经遇到过一些波折,单为他找工作单位孙老师就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每次说到谢有顺,他眼里就满溢着慈爱。
在学术上,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批判家、挑战者。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大约都还记得,孙绍振以一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横空出世,该文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发起了挑战。孙绍振认为这批年轻诗人的诗歌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与传统美学原则的分歧在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走出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进而概括了这批“朦胧诗”的三个美学原则,即“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面。”他的文章和北京大学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吉林大学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后来合称为“三个崛起”)一道,吹响了文学理论革新的号角。为此,他挨了批判,吃了不少苦头。《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篇闪烁着犀利的思想锋芒和充满生命激情的新美学宣言,现已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和当代文艺思潮史。其手稿已经为现代文学馆所收藏。
80年代中期以后他进入了学术的黄金期,创作一发不可收:《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与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幽默逻辑揭秘》《未来的文化空间》《文学性演讲录》等10多部美学、文学学术著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研究和一般“文艺美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的从理论到理论的路子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年轻时热爱文学,热衷创作,原以为老师会讲出“文艺理论”这门课许多有趣的艺术奥秘,使人的感觉精致起来,学会欣赏艺术,甚至提高创作水平,结果却非常失望。他不满于传统的“文艺理论”课一上来就讲艺术的起源——不是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劳动,讲来讲去,始终没有讲到形象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讲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更令他感到沮丧。对当时流行的一个权威命题,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他认为这是废话。他想,如果反过来说,美不是生活,难道就没有道理?这种理论实在太让人厌烦了。他觉得传统的文艺理论似乎都是与人的审美阅读经验(和文学创作经验)为敌的。另一种严重的不满来自于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引进的五花八门的理论,这些理论有的只有纯理论的价值、历史的价值,用它们来解读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常常是无效的,是文不对题的,硬要用一下也是削足适履。他认为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解读作品——我们经常见到的或经典性的作品。同时,他还希望文学理论有一点操作性,不仅是解读的操作性,而且是创作的操作性。文学理论的最高任务应该是培养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这就是他的一切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认为这与以往的理论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根本理念不一样。以往的理论关注的是认识价值,或狭隘的功利价值,而他关注的是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突破了认识价值的“真”,确立了艺术假定的审美价值,以假定论取代传统的真实论。二是方法论的不同。传统的方法论要求研究形象和对象的一致性,而他恰恰相反,要研究事物对象和艺术形象之间的矛盾,把矛盾揭示出来,抓住原来的与想象出来的艺术形象之间的差异不放,进行分析。由此建构起了以真、善、美价值错位理论与形象的生活、情感、形式三维结构为核心的文学审美和创作理论体系,并进而将审美判断深化到“审智”的范畴。他为文本细读和文学创作实践敞开了堂奥。他“取得了无愧于本土先贤也绝不逊色于当下西方权威的文化理论所达到的成就”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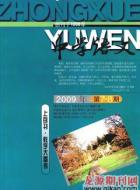
-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 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若干要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 王本华
-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 从钱梦龙“三为主”教育思想看新课程改革 / 潘冠海 陈 敏
-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 孔子的教育之道(七) / 韦志成
-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 语文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 何新华
- 化“综合性课程”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 陆 培
-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育观的影响探析 / 柯华桥
- 浅谈朗读在语感教学中的作用 / 王 颖
- “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知识更新 / 荣维东
-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 / 任明新
- 语文名师与当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建构 / 陈元辉
- 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歌的人生智慧 / 李晓颖
- 语文教育与人的完整性建构 / 赵 蕾 曹明海
- 经世致用与诗意人生 / 吴智勇
- 与心灵接触的情感教育:语文教学的灵魂 / 赵 蕾 曹明海
- 矫正中学作文的浮躁之弊 / 石修银
- “细读”举隅 / 史绍典
- 怎样才能达到议论的深度 / 朱庆和
- 新课堂中对文本主旨解读的反思 / 茹红忠
- 为高中作文教学号脉 / 侯志林
- 语文课堂设计的文本意识 / 武立伟
- 苍凉,抑或温暖的叙说 / 高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