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78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78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语文教育的实质是文化传承、改造、创生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①,而“每一种文化就其实质来讲都有地域性”②,“文化的完形是地区性的,而和种种集团之间的已知的关系并不甚关联”③。这种带区域性特征的文化我们称之地域文化,它“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④
地域文化深刻影响了主体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影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熏陶,处在地域文化背景中的人是“如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任何具体的语文教学都回避不了这种背景,语文教师应该充分挖掘这种原生态生活的课程资源的价值,以展示语文学科的生命能量。《新课程标准》就明确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
以语文教学的视角,关照地域文化,是每个具有前瞻意识的语文教师的教育使命和文化责任。地域文化以何种方式关涉我们的语文教学,是我们首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地域文化是教学主体思想沟通的语境。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语境”概念,他发现不结合说话内容和当时语境,就不能准确理解话语意思,他又将语境分为“文化上下文”和“情景上下文”,“文化上下文”指讲话者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⑤。实际上,这只是从语义理解的角度承认文化语境的作用。我赞同,语文教学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成以符号为媒介的一种交往活动,想要达成广域的教学主体交往,交往的内容、手段,以及主体的知识、经验、情感、态度等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语文教学中,基于不同地方文化积淀而产生的交往冲突是毋庸赘言的。还应认识到,由于知识视域的差异,很多老师和学生除了学业上的沟通,似乎难以另辟共同话题,殊不知本地文化现象是鲜活的第一手资源,教学主体对这种资源的认识是耳濡目染,亲身体验而得到的,以地域文化现象作为师生谈论主题,真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岂不避免了因知识缺失而产生的单通道信息传递?在信息对流的过程中,创设和谐师生关系,保证学生主体角色实现,这对语文教学是有积极作用的。
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方言的意义更不可忽视,以前国家提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以说好普通话作为语文教学目标,有普通话一元排它的倾向。目前,各地对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进行反思并“反正”,如上海提出“推广普通话,学会上海话”,其他各地也出现这种回归的潮流。
方言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更深层次的,它能够增加同一方言区人民的认同感,从而增加地方凝聚力。对于教学活动来说,持共同方言交往的双方也能够产生一种亲缘感,能部分地消除心理隔阂。崔颢《长干行》云:“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正是乡音这条纽带,让两个陌路之人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兰州籍相声演员王海在他的博客里谈到他的成功是沾了兰州方言的光,“兰州人太喜欢自己的乡音了,爱屋及乌,他们把对乡音的热爱,甚至把对这一方热土的感情都转嫁到你身上而已”,方言的情感纽带是不能忽视的。
方言的理解对交往双方的语义沟通也有影响。我国虽正式划分了八大方言区,但还存在着其他多种方言区,而不同的方言区可能会存在同域语用差异,所谓同域语用差异,是指“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内部,因方言不同等种种原因所引发的语用差异”⑥,这种差异毫无疑问会影响言语交往的质量。如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农村),开口称“大哥”,给人朴实亲切感,但在山东一些地方,由于受武松与武大郎的故事影响,人们忌讳被称为“大哥”,而乐于被称为“二哥”。但是在安徽南部一些城市里,“二哥”又成了贬称,与“乡巴佬”同义⑦,如果语文教师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生活,对类似语言现象缺乏认识,可能会引起交往冲突。
其次,地域文化为文本解读创造新视野。如果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我要续上一句,地域的才是民族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割裂其在生活地的文化经历,抹杀地方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正所谓鬓毛虽衰而乡音难改,世事消磨而镜湖旧波。所以解密他们作品中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无疑会为阅读者新开一扇窗户。很多入选高中教材的文学作品带有浓浓的地域文化色彩,对这类作品的解读如果仅局限于一般意义的诠释,可能会导致理解抽象化符号化;如果能更好地解读文章中隐含的地域性文化密码,则会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文章的理解。
古诗词鉴赏中,地域文化的差异更会因时代的间隔而影响学生的阅读,比如李煜的《捣练子令》,如果仅把“断续寒风断续砧”的“砧”理解成“捣衣声”,学生很难体会到本诗的意旨。“捣衣”这种民俗活动在70年代陕西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如今却很少见。中国古代,尤其关中一些地方,每逢秋风兴起,家人就要为征戍他乡的亲人赶制棉衣,他们用杵在捣衣石上捶打,使米浆进入布料。所以古诗中“砧”或“捣衣”一般象征闺妇的思亲怀远之情。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就有“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古诗词中,这种体现地域文化特点的意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现代文阅读中,通过对地域文化密码的破译,我们也可以加深和拓宽对文章的理解。在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中,“父亲”蹒跚地爬过栅栏为“我”买“橘”,读者一般只注意其中感人的细节描写,为什么“父亲”是买“橘”而非其他食物?这里面大有深意。“橘”江浙称之“福桔”,因其成熟期恰在岁末,当地风俗以“红”见好,且“桔”与“吉”音似,有吉祥如意之意。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中也有写长妈妈要求吃福桔的事情,这样,我们更能体会这随笔中的真意、无声中的惊雷了。
而且,当师生厌倦于传统的课文分析时,是不是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另辟蹊径呢?我认为,很多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的篇目都可以尝试。比如鲁迅的《祝福》,“祝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人们通过极其庄重的仪式向祖先祈福,以获取保佑,它是中国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体现最为鲜明的活动,它是祥林嫂命运变化的根本原因,“祝福”场面的热闹、合家的团圆不是更衬托出祥林嫂命运的悲惨吗?《边城》中湘西人民的对歌风俗,是翠翠的爱情和命运变化的核心要素,也是湘西人民淳朴善良的见证,热情执着的象征。对于这些我们一般是视而不见的,殊不知,这类地域文化元素既体现了也塑造了人们的性格、价值观。作家的情感个性逃脱不了这种无形的规范和限制,作品人物形象的情感个性亦如此,文学作品的地域文化分析也就是作家和作品形象分析的定向爆破。
再次,地域文化是言语能力成长的沃土。课本的语言材料毕竟是固态的、有限的,地方方言本身既是普通话词汇的主要来源,是普通话保持活力的源泉,又是动态创生的,具有无限延展性和包容性。各地人民在劳动生产,文化生活中,创造了丰富的具有地域风情的语言形式,其中包括词语、谚语、歇后语,它们或短小精悍、含蓄隽永,或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表现出原生态的韵味。例如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上海民歌选·瓜不离秧》(初版)第62页有这样一段话:“瓜不离秧,孩不离娘,中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⑧,我想把“孩”改成四川方言的“娃”,鄂方言的“伢”,北方方言的“丫”,从修辞的角度看也比原文高出一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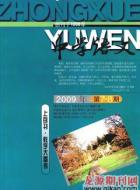
-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 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若干要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 王本华
-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 从钱梦龙“三为主”教育思想看新课程改革 / 潘冠海 陈 敏
-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 孔子的教育之道(七) / 韦志成
-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 语文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 何新华
- 化“综合性课程”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 陆 培
-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育观的影响探析 / 柯华桥
- 浅谈朗读在语感教学中的作用 / 王 颖
- “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知识更新 / 荣维东
-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 / 任明新
- 语文名师与当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建构 / 陈元辉
- 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歌的人生智慧 / 李晓颖
- 语文教育与人的完整性建构 / 赵 蕾 曹明海
- 经世致用与诗意人生 / 吴智勇
- 与心灵接触的情感教育:语文教学的灵魂 / 赵 蕾 曹明海
- 矫正中学作文的浮躁之弊 / 石修银
- “细读”举隅 / 史绍典
- 怎样才能达到议论的深度 / 朱庆和
- 新课堂中对文本主旨解读的反思 / 茹红忠
- 为高中作文教学号脉 / 侯志林
- 语文课堂设计的文本意识 / 武立伟
- 苍凉,抑或温暖的叙说 / 高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