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8期
ID: 359193
语文建设 2015年第8期
ID: 359193
吴研因语文课程标准研制思想研究
◇ 翟志峰 王光龙
吴研因是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学校教学、教材编写、理论研究、教育行政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是1923年《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的起草人,与叶圣陶、胡适一并开启了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科学化的历程。此后,他还参与了1929、1932、1936等年份小学国语课程标准的研制。研究吴研因的语文课程标准研制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1923年国语课程纲要,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发展史。
一、引领——研制语文课程标准的实践
1922年壬戌学制颁行后,学界有众多人士提出拟订学科课程标准的问题,吴研因也是其中一员。囿于当时缺乏拟订课程标准的客观依据,自称“一个心急的人”的吴研因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在这没有客观标准的时候,姑且由各个有思想有经验的教育者,用主观的眼光,拟定各种课程草案,报告公众;再由公众集合讨论,选择一个流弊似乎最少的课程草案,作为临时试用的临时课程。一方面再用测验法和精密的调查研究,赶定一种正式课程,预备起代临时课程”。考察1923年课程纲要的研制历程可知,吴研因的这个办法成了当时各科课程纲要研制的基本路径。
民国初年,俞子夷担任江苏省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任时,聘请吴研因担任该校教员。期间,吴研因与俞子夷紧密配合,积极开展国文教学改革。也就在此时,吴研因有了拟订课程标准的动机。他说,“当时我觉得国文课程有改组的必要,所以曾经拟订一个改组的计划,提出于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请在会各学校通过”。1922年,吴研因应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离开江苏第一师范附小,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同时兼任该馆私立尚公小学校校长。是时,“新学制”初行,吴研因认为“新学制建设中,第一个顶要紧的问题,就是要讨论各级学校的课程,究竟应该怎样”,且“国语课程不可不从事建设”。于是,他和尚公学校同人讨论之后,拟订一个草案,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初等教育组提出,并经该组成员讨论、修改。1922年11月,吴研因又把草案递交江苏省教育会国语推行委员会讨论修订。该案后被录送给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研制各科课程标准而组织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下简称“起草委员会”),以供拟订新学制课程标准参考。同年12月6日至8日,“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吴研因作为江苏省代表与会。会议通过五项议案,并决定根据已议定的毕业最低限度标准,“分中学小学两组,编定各学科课程要旨,分请专家拟订各科目课程纲要”。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已经过几次修订的吴研因拟订的国语课程纲要草案在该次会议上得到了大家较高的认可,甚至“议决各科课程纲要的形式,都要把本案的格式做标准”。1923年1月,吴研因收到“起草委员会”的正式通知,由他负责起草《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吴研因遂在原有纲要草案的基础上再加修订提交“起草委员会”。4月20日发行的《教育杂志》第15卷第4期刊载了这份课程纲要;同年,吴研因在《初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上刊登《国语课程纲要草案说明书》,对纲要草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4月25日至5月5日,“起草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委员会,将已拟好的小学、初中各科课程纲要逐科复订。6月4日至8日,“起草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委员会,再次复订小学初中各科目纲要。当月,由“起草委员会”编辑的《新学制各科课程纲要》在南京印发。1925年6月,《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经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而正式刊布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与《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在一些地方再次做出修订,主要为:第一类,语言文字的调整,如将“能听国语的故事讲演”改为“能听国语的故事演讲”;第二类,难易程度的调整,如将“能速写楷书和行楷方三四分的每小时约二百字”提高为“能速写楷书和行楷方三四分的每小时二百五十字”;第三类,内容的增加,如在“方法”部分新增“作文注重应用文的设计,研究和制作”。
通过上述对研制历程的爬梳,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吴研因拟订一份语文课程标准经历了怎样“切磋琢磨”的过程。也许课程标准文稿就是一人在两三日内拟订的,但其后蕴藏的一定是研制者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与对学科本体的深刻省思,是厚积薄发之作。正是“经过五六年的酝酿,数十个教育专家的讨论修正”后,才使这份纲要为大家“承认大致不谬”。
而“起草委员会”之所以聘请吴研因、叶圣陶、胡适分别负责起草小学、初中、高中国语课程纲要,可能的解释是,在国语科成立初期,教育部官员只是接受了国语运动、文学革命者的主张,将“国文”改为“国语”,但对如何借助注音字母和语体文完成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听说等任务的“国语”课程实施问题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曾对此进行过前期实验研究的专家,自然最有发言的权力。吴研因经过两番修订、多个场合讨论通过的课程纲要草案,胡适在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国文研究部所做《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均是在“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的时期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的蓝本。
二、向生性——研制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学制、课程建设中采取何种价值取向,各取向间如何调剂,是壬戌学制研制过程中讨论的问题之一。陶行知主张先依据学科体系划定一个课程内容的基本范围,然后再依据社会和学生的需要进行筛选。陶行知认为学制、课程应包括三种要素,即“社会之需要与能力”“个人之需要与能力”和“生活事业本体之需要”,其中的“生活事业本体之需要”是指,“按着各种生活事业之需要划分各种学问的途径,规定各种学问的分量”。简言之,学制、课程应从社会、学生和学科三个方面考虑。在研制课程时应“先依据各种生活事业之需要,规定各种学问之分量,再就社会个人的能力所及,酌量变通,以应社会与个人的需要”。
与陶行知不同,吴研因认为社会和学生是两个主要的方面,而学生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不赞同在小学阶段以学科为主要考量因素。吴研因在讨论课程建设这一新学制建设中第一个顶要紧的问题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即学生和社会,分别研究他们究竟需要什么,然后把两者需要的定在课程里。如在社会方面,他提出“和共和国体适宜而不相抵触的”“是本国社会所缺少而需要的”“可供全国通用而多留各地方活动余地的”等标准;在学生方面,他提出“适合学生生活,和他的某一发展期的智力感情意志不背驰的”“限度最小,是优秀学生的基本,平庸学生也一定能够学习的”等标准。而在“社会”和“学生”这两个维度上,吴研因更注重学生的需要。一方面,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他要求学校课程要为全体学生着想,不可专为优秀学生设想。学校的课程要“将中等生一定能够学的,列在课程内,作为最小限度的课程”,以此使中等学生可以有所学,优等学生也有一“同样的基本”。另一方面,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他不仅构思开设必修科、选修科和随意科,以便于学生学习;还提出课程内容的排列要从心理的到伦理的,从具体的到抽象的。他批评过去“不自然”的教学,“教书的往往死守着教科书,看他好比‘金科玉律’一般,依照了教下去;也不管他时期颠倒、程度深浅、分量多少、学生是否需要”。他提出要做到自然的教学,不外乎依据“学生自觉的需要”“学生已具的动作和经验”“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吴研因看来,小学校儿童学习文学,他们所注意的是内容趣味,不是文法形式,文学的课程不该只用文法排列,而要按照学生学习的心理来架构课程内容;当学生到高年级的时候,学得许多具体而零碎的知识时,方可用论理的排列,加入抽象的东西。
基于上述向生的课程理念,吴研因反对在小学阶段强硬向学生灌输成人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主张给予方法教育。新学制研制过程中,不少人士认定“小学教育之旨趣,在完成国民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与技能”;“小学教育授以儿童必须之知识与技能,以养成公民人格为宗旨”。吴研因认为:“所贵乎学校教育的,虽说一面要给学生以必要的知识技能;但又一面也不过使学生得到一些学习的方法,和养成些学习的习惯罢了……知识技能是无限的,学不完的,学校教育时限中,即使竭力把知识技能给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到社会上做事,仍旧不够用的,惟有学习方法,和学习的习惯,是用不完的。”
正是吴研因在学生、社会和学科三者之间坚定地站在学生这一边,明确反对在小学阶段以社会需要、学科系统压抑学生的发展,使得其这种向生性的课程观深刻影响到国语课程纲要的研制,加之当时“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也就无怪乎“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文学’做了中心”。
三、国语、文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内容
吴研因在研制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时主张将学科名称由国语科改为国语文学科。因为在他看来“国语”两字兼指包含社会地理自然研究等学科的实质的语体文并不妥当。理想的状态是:“国语教材中,加入儿童的文学,而把包含各科实质的材料,划归各科里面去实地考察,亲身研究。”经过如此一出一人的改革,“国语中加入儿童文学后,就改称国语文学”,学科的课程目标“包含语言文字的练习,和缀法,书法,和文学的读法”。虽然吴研因修改学科名称的主张因故没有得以实现,但前述“国语文学”科的目标在修订后的纲要中以“目的”项得以确定:“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该目的中,“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是国语科的总目的,为达成这一总目的,又分为读文的目的、语言和作文的目的两项,“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为语言和作文的目的,其余为读文的目的。
为落实“国语”“文学”的课程目标,吴研因在识字、阅读、写作、说话等之间进行了细致的筹划。
吴研因研制的《国语文学科学程纲要》将识字与阅读结合在一起,有重合之处,但识字主要以日常实用文字为对象,阅读以儿童文学为对象。在第一学年,学生从“教室等处用文字标记的物名人名”“用文字代语言布告的简短语句”“故事挂图中重要文句”“用文字记述已熟儿歌谜语”等处学习识字;而同年学生阅读内容,除前述四项之外,主要以“字句多重复的童话、故事的诵读表演”“儿歌的吟味”“谜语的推解诵读”等为主。正式刊布的课程纲要中,虽然简化了对识字学习的规定,但依然是“重要文字的认识”,即“社会所习用的文字”。阅读的材料则是形式更为多样的儿童文学化的作品,以落实“引起读书趣味”,“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的课程目标。兹列表于下:
在对“神话”“传说”“寓言”等具体内容的解说中,吴研因或列出符合上述内容的具体篇目,或收录一篇符合要求的作品。前者如在小说——“演进节录”项下举《孔明借箭》《智取瓦口隘》二例;“新旧长篇节录”项下举《王冕学画》《郭孝子遇虎》《武松打虎》三例。后者如在记载要项的童话故事——“口述故事全部而记载全部要项”后举一例如下:一只老猫令付三只小猫自求生活,三小猫各拿兵器去打猎,岂知兵器都被老鼠衔去,只得空手哭回,老猫说这是不学无术所致,因教三小猫读书,而三小猫而始勤读不辍。上述形式多样且儿童文学化的阅读范式,不仅是1923年《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的最大亮点,而且直接影响了1929至1948年数份小学国语课程标准的研制,成为整个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特征之一。
关于写作,吴研因没有按照传统读写一致的原则来设计课程,走的是读写分离的路子。第一、二学年安排为,以“日常教师儿童相谈相约的语言”为代表的“简单语言的记录发表”;第三学年为颇具实用特色的“通信,条告,记录的设计,和实用文”;同时自第三年始,学生开始说明文、议论文的作法、研究、练习。整个写作注重的是“应用文的设计,研究和制作”,目的在于“养成发表能力”“令人了解大意”而已。
吴研因将“语言”(说话)单独列为一类,使其从过去阅读教学的附庸中解脱出来,具有了独立的课程价值。按他的构想,“语言”教学分别由“演进语等”(含演进语、命令语、游戏动作),会话,童话讲演,笑话、史话、小说的讲演,普通的演说,辩论会等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的部分组成,使其成为既与阅读有一定的联系同时又独立于阅读的说话训练体系。
此外,基于“所贵乎学校教育的……使学生得到一些学习的方法,和养成些学习的习惯……惟有学习方法,和学习的习惯,是用不完的”这样的认识,吴研因在课程纲要中特意加入了“加授检查字典的方法”这一课程内容,并将其作为毕业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一部分:“能用字典看与‘儿童世界’或‘小朋友’程度相当,生字不过百分之十的语体文”。
四、过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中的缺憾
吴研因拟订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正式刊布后,黎锦熙和沈颐不久后提出了《修正“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案》,认为吴研因“所拟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中,竞把第一学年‘首宜教授注音字母’这个法良艺美的规定删去,只在初小‘毕业最低限度标准’项下,载明‘并能使用注音字母’一语”,“对于‘国语教育’这一点”是一种“退步”。
起草1923年《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后,吴研因还参与了1929、1932、1936、1940等年份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而“这几份(指1929年和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笔者注)课程标准中都没有吸纳当时研制出来的语法、修辞、作法知识”,对此,有学者提出这“与其认为这些知识用处不大直接相关”。
不论是批评吴研因未将教授注音字母列入课程纲要,还是推测吴研因影响新的语文知识进入语文课程标准,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就是吴研因所秉持的向生性的课程观。因强调“学生自觉的需要”“学生已具的动作和经验”“学生学习的兴趣”,吴研因主张小学生识字应当以“造字之意指导学者”,批评在认识汉字之前先教注音字母不仅无法达到“易于认识汉字”“可以矫正汉字读音”等问题,而且于当时教育现实不符。因强调“学科和学生的经验,要相互凝结”,吴研因便有可能认为那些知识与学生的学习心理不合,与学生“注意的是内容趣味,不是文法形式”相悖,遂明确提出“不知文法的了解活用,也都和经验有关系的;读书多了,自然会有文法上的经验,谆谆告诫是无用的”。
吴研因在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上具有独特的贡献,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并从标准形式上为后来的标准提供了范本。另一方面,他基于强烈的向生性课程观研制出的语文课程标准“使‘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达到最高点”,使得说明文、议论文等实用文的阅读在小学阶段严重减少,并为日后“鸟言兽语”之争埋下伏笔。虽然吴研因提出在“讨论各级学校的课程”时要顾到学生的生活和社会的环境,但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他研制的课程滑向了学生的一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会和学科这两个维度,未免失掉了平衡。
参考文献
[1][3][13][14][17][20][22][23][25]吴研因.小学校和初级中学校的课程草案[J].教育杂志,1922,14(号外).
[2][4][6][7][26]吴研因.国语课程纲要草案说明书[J].初等教育季刊,1923,1(1).
[5]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S].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1—2.
[8]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4.
[9]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A].胡适.胡适文存:卷一[c].合肥:黄山书社,1996,161.
[10][11][12]陶行知.评学制草案标准[J].新教育,1922,4(2).
[15][16][32]吴研因.文字的自然教学法[J].教育杂志,1922,14(3).
[18]佚名.新学制运动[J].教育杂志,1922,14(2).
[19]佚名.三志新学制运动[J].教育杂志,1922,14(4).
[21]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J].中华教育界,1936,23(11).
[24]本处文字引自《国语课程纲要草案说明书》。正式刊布后的“目的”与上述文字有变化,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
[27]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会议”上所议决的“毕业最低限度标准”中小学国语的规定为“能读与‘儿童世界’或‘小朋友’程度相当之白话文”。
[28]黎锦熙.教育部定国语课程标准之检讨[J].文化与教育,1934,(19).
[29]张心科.语文课程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129.
[30]吴研因.识字教授之商榷[J].教育杂志,1918,10(3).
[31]吴研因.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J].教育杂志,1924,16(1).
[3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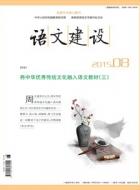
- 卷首语 / 佚名
- 从“去中国化”谈语文教材改革 / 周正逵
- 语文教材呈现传统文化的原则 / 黄厚江
- 也谈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材 / 张心科
- 语文教材古代诗词选编刍议 / 胡根林
- 充分发掘汉字的文化内蕴 / 郑飞艺
- 积极语用:为真语文教学注入科学内涵 / 潘涌 杨培培
- 请给文学写作一席之地 / 佚名
- 语文教学也须讲求顶层设计 / 刘仁增
- 关注教学的起点和落点 / 周康平
-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四):意境 / 孙绍振
- 那些“看不见”的精彩 / 张小兵
- 《透明的红萝卜》主题的多重意蕴 / 王新惠
- 生而孤独,慰藉常因距离 / 冯永清
- 高考语言文字运用考查的新探索 / 秦思梦
- 高考作文还可以这样考 / 张晋军
- 吴研因语文课程标准研制思想研究 / 翟志峰 王光龙
- 民国国文教材中的胡适新诗 / 刘绪才
- 议论文知识不能如此重构 / 安杨华
- 例谈小学高年级散文教学策略 / 张海滨
- 语言规划范式下的语文教育 / 刘昌华
- 传承经典 文化养心 / 谢惠
- 知天下之脉络 / 赵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