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4期
ID: 140257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4期
ID: 140257
王朔:玩世表皮下的沉重
◇ 徐雪瑾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在各式传统小说和各样先锋小说无论怎么卖力似乎都难以招来读者热情的时候,王朔洒脱而恣肆的面孔出现了。他发着橡皮光泽带着橡皮质感“招摇过市”,顿时吸引了无数好奇的目光。于是,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竞相谈论王朔的现象,并且跨过2l世纪的门槛,一直延续到今天。
若从形态上看,王朔的创作经历了“从纯情到邪恶”,又“从邪恶到玩世”的过程,《=空中小姐》、《浮出海面》是第一阶段,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是第二阶段,到了《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别把我当人》、《永失我爱》等作品,情况与之前又大为两样了。他的作品有自身的联系和发展,与小说领域的潮涨潮落关系甚微,是地道的“中国制造”。若就小说自身的艺术价值看,王朔是长于对话的,这是他的异彩所在。痞子腔,最新市井语汇,被他写得活灵活现。王朔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是最具特定时代性的产物。王朔小说的社会认识意义远远超越了他小说本身的价值。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最新的社会心态。应该说,主要不是他小说的艺术性使他成功了,而是他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生活态度和精神特征使他成功了。为什么王朔的小说与我们这个在崩溃与再生中暂时脱了节的社会一碰撞,就会发出巨大的回声?为什么王朔的小说不但年轻人喜欢读而且文化层次较高、年龄偏老的人也喜欢读?特别是生活中的失意者、碰壁者、苦闷者更喜欢读呢?这里正有深意存在。
一般说来,王朔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大量读者,首先在于它外表的平易、单纯,语言的通俗化、生活化,情节的丰富性、刺激性。一般的读者猜够了象征、魔幻、意识流的谜语,王朔的作品清新可人,又常常植入推理、侦破的故事圈套,读来不累,反能得到片刻轻松和解脱,又何乐而不为呢?
王朔小说赢得读者的第二个表层原因,是具有“补充体验”的功能。读者的心理往往是:我无法体验的生活要借作品体验一番,我体验过的生活则要看看别人与我的体验有何不同。王朔笔下的顽主世界,那些沉浮在现代都市底层的浮浪子弟和无业游民,他们关于金钱、犯罪、财博、性感、游戏的种种想法和做法,是一般人无法体验到的陌生生活。他们彻夜不息地打牌,化装成警察大敲作奸犯科的外国阔佬的竹杠,倒卖彩电、汽车,在大街上齐声嚎叫“我不悲哀!”,故意冲撞文质彬彬的路人挑起事端,甚至粗心制造一起假杀人案捉弄警察……真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对此人们不可能不感兴趣。
读王朔的小说,常常会让人联想到舞台上孙国庆演唱《一无所有》的情景,那嘶哑、放浪、不顾一切的吼声,与王朔小说的境界颇为吻合——那种流浪汉的自由,我行我素的放任,无所畏惧而“豁出去”的洒脱。不时被种种凡尘俗事纠缠得苦不堪言的人们,将从这样的小说或歌声中获得片刻的解脱。
所以,王朔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一个真实的“我”的魅力。这个“我”可以是张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于观(《顽主》)、方言(《玩的就是心跳》)等带有明显自叙色彩的叙述主体,也可以是李白玲、吴迪、马青、高晋、刘炎、凌瑜这些“哥儿们”、“姐儿们”。因为王朔的人物虽然个性鲜明,但在个体意识上共性突出。这个“我”不装腔作势,不遮遮掩掩,更不自我美化;这个“我”是顽主,是“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这个“我”认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这个“我”并非不知道死亡的威胁,“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这个“我”也愿意承认他的恐惧:“我一生中一直恐惧的是什么?不就是怕白活?”显然,这是一个看透了一切的、告别了天真与纯朴的、洒脱的、富于破坏性的“我”。
那么,王朔小说中究竟还有没有痛苦呢?尽管顽主们齐声说“我不悲哀,乐着呢!”,我们仍有相当理由认为,这种拒绝承认痛苦的反复表白,正是深藏痛苦的表现。顽主们正是通过否定一切价值来安慰自己,来维系自我的尊严的。如果没有痛苦的体验,小说中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不痛苦”的细节和笑料了。王朔小说里有种非常深刻的情绪,那就是他们以“局中人”、“过来人”的眼光看到,某些少男少女在当今社会存在着沉沦的危机,有股不能自拔、阻挡不住的下坠力,这决非冠冕堂皇的社会分析可以解释得清楚。
顽主不顽,在玩世的表皮下还是裹藏着一些沉甸甸的东西,其中我们不难听到一种沉重的追怀往事的叹息声。这是一种接近于波德莱尔的美学情感,往往能够凝聚社会的复杂和龌龊面,通过残酷而抵达深层。这就是王朔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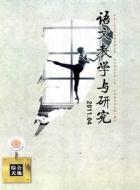
- 想象:打开阅读教学另一扇窗 / 赵建林
- 我在哪里丢失了你 / 范小青
- 培养学生从文体特点入手解读文章 / 邵松
- 熟悉的陌生人,陈青山 / 陈青山
- 新课程理念呼唤语文教师的角色转换 / 闫兄平
- 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策略浅探 / 罗新莲
- 议论文中事实材料的运用 / 胡传虎
- 从《安恩和奶牛>的教学谈写作训练 / 蔡丽霞
- 将阅读进行到底 / 王春红
- 加强中学生语文课外阅读应对策略 / 杜大玲
- 初中有效写作教学策略探微 / 刘蕾
- 引导学生互评互改作文的几个明确 / 何永杰
- 例谈人物描写的生活化 / 何芳
-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 / 殷丽娟
- 生活化作文源自生活体验 / 冉中正
- 朗读是语文教学的法宝 / 陈春清
- 如何提高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 高秀英
- 语文课堂导入的环节及其原则 / 余进
- 语文教学中的愉快教学 / 王西凤
- 他山石助文思 / 刘金乐
- 语文教学中的空白艺术 / 刘世攀
- 让语文课堂走向生活 / 许亚峰
- 让提问走向有效 / 杨锁群
- 目标教学与语文课堂高效 / 朱成
- 利用语文课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 王苗红
- 情感教学:开启语文殿堂的钥匙 / 张桂艳
- 谈古典诗词鉴赏的教学策略 / 顾金龙
- 个性化:化腐朽为神奇的利器 / 匡立庆
- 巧借科学整合语文课堂 / 张鹏
-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法 / 马锐
- 学案教学打造高效课堂 / 胡杨
- 提高课堂效率的几种方法 / 施德霞
-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艺术 / 周涛
- 试析《鸿门宴》中的项羽英雄心理 / 李彬
- 美文《散步》的多角度解读 / 李清瑛
- 语文自主学习能力培植 / 侯良艳 宋国童
- 浅谈文言文教学理念的转变 / 王晓杰
- 《背影》的心理维度研究 / 王霆
- 《始得西山宴游记》探究一得 / 肖艳盛 董安
- 读解《地球上的王家庄》 / 方好
- 苏轼在何处“起舞”:再解《水调歌头》 / 黄洋
- 《故都的秋》赏析 / 史世毅
- 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写作技巧 / 李加春
- 在语文活动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 王艳玲
- 初三语文试卷评讲的若干原则 / 黄小敏
- 研究 指导 服务 / 夏丽红
- 初中生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葛洪波
- 中职语文口语交际校本教材的开发 / 傅卫莉
- 突破现代文阅读作用类题型 / 李峥嵘
- 新课标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研究 / 马红玲
- 作文复习四步骤 / 李寒
- 《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之比较 / 王琴
- 孔夫子论孝不荒唐 / 程云秋
- 刘禹锡是在自我标榜吗 / 潘军
- 考场作文的现状与反思 / 王晓云
- 作文解题思路一谈 / 王冬梅
- 对语文试卷评讲的点滴思考 / 杨兆红
- 高中文言数词用法举隅 / 聂翰贤
- 语言品味的几种方法 / 许志强
- 《庖丁解牛》中“踦”的异议 / 刘红梅
- 叠词妙用出奇效 / 刘军
- 王朔:玩世表皮下的沉重 / 徐雪瑾
- 截止与截至之辨析 / 方厚防 王丹丹
- 《唐诗宋词》选修课教学初探 / 窦桂玲
- 半江瑟瑟半江红 / 邓红霞
- 《伟大的悲剧》教学设计 / 高景兰
- 试析李白诗中的夸张修辞 / 黄冰洁
- 《雨霖铃》赏析式教学案例 / 燕淑梅
- 李杜的生活经历对创作风格的影响论 / 宋旭华
- 康进之的幽默喜剧 / 李冬梅
- 改善中学生作文现状的几点对策 / 董旭午
- 新课程选修课教学中的策略 / 刘荷花
- 《先秦诸子选读》教学法的探究 / 王安逸
- 《五柳先生传》教学设计与教学反思 / 邓晓丽
- 《蜀道难》教学设计 / 华宏玲
-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说课稿 / 聂蓉
- 古代三才女 / 程祖灏 杨羽
- 读贾平凹农村题材的小说 / 焦银生
- 当代现实主义同传统现实主义比较 / 兰琳玲
- 无悔的追求 / 文秀勤 王风云
- 写意山水话漓江 / 刘道生
- 构建自主互助学习型课堂 / 朱林波
- 成长的记忆 / 李于文
- 痕迹 / 周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