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57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57
《小妇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再分析
◇ 皮艳玲
摘要:美国著名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成名长篇小说《小妇人》是在美国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作而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键词:传统观念 女权主义 《小妇人》
引言
《小妇人》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马奇家四姐妹的成长和爱情故事。南北战争时期,马奇先生参加北军出征,当随军牧师,而马奇夫人则留在家中,凭借自己的善良、淳朴、无私、智慧和宽容陪伴,教育着四姐妹。小说以这一普通家庭的生活琐事和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为线索,生动地描写了大姐梅格、二姐乔、三妹贝思和四妹埃米的成长过程,不仅体现出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 也折射出时代特征与文化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下妇女力争解放的愿望,获得个性发展这一社会转型期对人物形象的道德价值产生巩固、建构和修正的正面影响力。
一、女权主义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与反奴隶制运动和南北战争前的其他进步运动紧密联合,尽管《小妇人》创作时正值美国夫权至上时期,女性的个性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但奥尔科特并不认为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品,她希望通过小说的创作唤起女人的觉醒,鼓励女性在人生中展示个性,获得自由。《小妇人》中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梅格是马奇家的长女,承担起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的责任;乔经过努力最终当上了作家,她是小说中最典型的女权主义代表,摒弃了女性身上应有的一些特质,其行为与个人偏好与传统意义上对妇女的诠释背道而驰;贝思拥有美好的音乐梦想;埃米梦想当上世界出色的艺术家,婚后并没有像传统妇女那样把家庭当作自己的一切,而是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1]这充分体现了奥尔科特笔下四姐妹寻求自立自强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思想。
二、美国文化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形象
美国早期主流民族除部分英国人外,相当一部分来自欧洲移民,包括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德国人和瑞典人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文化源于西方文化,推崇尊重人格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而人格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个体从事个体本身认为需要做的事情, 并且因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从心里上感到满足。[2]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人格的驱使下,《小妇人》四姐妹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不受任何外界的束缚,即便是马奇夫妇也不会因为身为父母而对子女多加干涉,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当埃米因为违反老师戴维斯先生的规定将腌酸橙带到学校取悦同学而受到戴维斯先生的体罚后,不想再去学校。马奇夫人一方面支持埃米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不忘对她进行开导和教育。虽然当时的女性都崇尚女权主义,但这并不是要以个人为中心,也不是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尽管马奇太太内心不太愿意马奇先生远在前线,但她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最终也同意了,这充分体现了受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下马奇夫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三、家庭教育下的女性形象
(一)传统观念下的女性形象
19世纪的女性作家在创作家庭类小说时仍然摆脱不了传统女性形象的影响,奥尔科特也不例外。她在支持女权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观念。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对家庭忠诚,对长辈孝顺。尽管女孩们对家务感到厌烦,有时候也要洗碗、打扫房子。空闲时,她们也常坐在一起编织毛衣、做针线活或种植花园。当然,她们也有懒惰的时候,某周末,马奇夫人为了教训她们,专门给汉纳放假,让孩子们自己承担所有的家务。她只是想让孩子们明白大家都能分担家务,每天做一点儿会更好。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四姐妹对生活充满了感悟,通过锻炼,她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
(二)家庭影响下的女性形象
《小妇人》四姐妹的鲜明形象与马奇夫妇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作为家庭主心骨的父亲尽管远在前线,也经常与家人保持书信来往。其中的一封信中,他在对孩子们表达爱和祝福的同时也在教育孩子们在等待的时候应该工作而不是虚度光阴。母亲作为孩子们的人生导师,在给她们传达人人都有追求自我权利信息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良好品质沿袭给了她们。母亲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既为自己树立了威信,又为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还为家庭营造了异常活跃、宽松、愉快的生活氛围。她在潜意识中希望四姐妹长相漂亮、学业有成、品格高尚、受人爱慕和尊重。奥尔科特通过对马奇夫妇这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和循循善诱的、开明的教导方式以及马奇先生对四姐妹的影响的刻画,塑造了四个性格迥异、在艰苦中寻求幸福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1.贤妻良母型——梅格
梅格是马奇家的老大,她热爱跳舞,也很优雅,自尊心很强,喜欢被人羡慕和表扬的感觉,主要在家料理家务,偶尔承担写剧本和演出的工作,代表着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母性十足,总是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妹妹。同时她也有着较强的责任感。圣诞前夕,姐妹们发现母亲的拖鞋已经很破旧后都争先恐后为她购买时,梅格却站出来强调,她来买这双拖鞋,既然爸爸不在,作为老大,她就是这个家庭的男人。她渴望、羡慕别人的富裕生活,曾经爱慕虚荣,梦想进入上流社会以便能够拥有漂亮的房子和漂亮的服装。她因贫穷而自卑时也不忘采取其他方式来弥补自己认为的缺憾。在莫法特一家参加聚会时,非常羡慕安妮·莫法特的富有,但她也不甘落后,用很多法语词只谈论时尚并被姐妹们打扮成看似有钱的女人,以弥补内心穷苦而感到的落差,但后来她意识到爱情比金钱重要,最终放弃了虚荣,在贫穷却很善良的布鲁克先生那里找到了真爱。
2.率真、直爽、倔强——乔
马奇家的二女儿乔与其她姐妹相比,性格截然不同,是《小妇人》中的核心角色,批评家一致认为,乔这个人物形象是奥尔科特的部分现实写照。她颇具男孩子气,与传统意义的淑女形象格格不入,讨厌那些本该属于女孩做的事情,如不想化妆、穿裙子、却想和父亲一起参加战斗。作为女孩,却憎恨那些充满女孩子气且满腹牢骚、傻乎乎的毛丫头。她说话直言不讳、缺乏心机。第一次见到姐妹们都很敬畏的邻居劳伦斯先生时,尽管有点害怕,但还是当面直言劳伦斯先生不如自己的祖父英俊。她热爱阅读和写作,渴望成为作家,在照顾马奇婶婶期间,一有空闲就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和练习写作。她内心尽管很倔强,脾气不好,却很有担当。当她知道自己花了几个月心血写的书被埃米烧掉时,怒火中烧,不依不饶。埃米知道惹恼了姐姐,不断试图缓和关系,倔强的乔都置之不理。一次,埃米主动接近与劳里一起溜冰的乔,乔明知有危险,却不告知,险些让埃米丧命。事后她积极施救,却不断地自责和内疚。除此之外,乔还有着较强的责任心,在贝思感染了猩红热的时候,她不分昼夜地照顾贝思。但她也有较为脆弱的一面,当她发现贝思已经认不出大家,感觉上帝的距离很遥远的时候,眼泪也禁不住流下来。[3]
3.腼腆、单纯、善良——贝思
马奇家的三女儿贝思单纯、善良、娴静,爱弹奏钢琴,是一个非常纤弱的小天使。她的懦弱、胆小和羞怯使其无法正常完成学业,只能和家人平安地呆在家里,帮忙料理家务。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贝思也勇于突破自我。在劳伦斯先生家,劳里的祖父知道小女孩喜欢钢琴,却又很羞怯,便主动谈到他很想教人弹钢琴,还问到有没有人想要学习。对于贝思而言,一方面因为自己的钢琴陈旧,另一方面无人教她,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于是她羞答答地表示自己想学,但要劳伦斯先生确保没人能听到她弹琴,她就愿去。可见,贝思的天真无邪和腼腆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母亲的感召和熏陶下,贝思也乐于帮助别人,但在照顾赫梅尔太太的孩子时染上了猩红热, 而永远离开了。贝思的离去预示着传统的女性角色已过去,唤醒当时的女性站起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平等和自由,以提高女性的地位。
4.自强自立而不拘礼教——埃米
马奇家的四女儿埃米聪慧活泼、纯洁美丽。她追求完美,对艺术的追求很执着。小时候因为被乔不小心摔跤了,导致鼻子变成了平鼻子,但她很渴望自己有一只尖鼻子,于是画了成百上千个尖鼻子,从此就变得擅长画画了。她希望能去罗马,成为世界上出色的艺术家,成为一名上流社会的“淑女”。尽管如此,她也有自己为人的原则,她告诫自己会努力做到不贪慕虚荣。 奥尔科特把埃米塑造成自强自立,不拘泥于传统的新时代女性,为当时的青年妇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她很自信也很坚强,不甘于受传统观念的控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恰当的方法、技巧,为自己赢得了幸福。
五、人物形象对比分析
奥尔科特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精准刻画,将一篇普通的家庭日志型小说提升到美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披露和展示。马奇家四姐妹在人物性格特征方面有着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共性在于四姐妹都生活在一个氛围宽松、和睦、团结、友爱、贫困的家庭,共同拥有慈爱的父母、较强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家庭和朋友的忠诚,对理想的执着,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她们善良仁爱、相互帮助、自立自强。但她们有着不同的理想和命运,性格方面也有着鲜明的个性,代表着新时代的不同女性。根据作者的情感流露和创作思路,不难发现,马奇家的四个女儿中,慷慨大方的梅格与自私的埃米之间尽管性格不同,但关系较为亲近。[4]同样因为性格的反差和互补,乔和贝思也成了知己。尽管埃米和乔都不具备音乐天赋,但她们都非常向往独立,对传统观念中限制女性的条条框框表示痛恨。事实上贝思和乔在四姐妹中最具奉献精神。语
参考文献
[1]郭莲.美国女权运动的变迁[J].国外理论动态,2002(11):30.
[2]徐洁.奥尔科特《小妇人》中反映的美国文化传统[J].南京师范大学,2006(4):2.
[3]冯川.弗洛姆文集[C].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19
[4][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M].付蓉译.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201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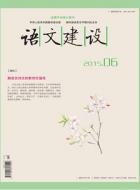
- 解读古诗文的教育价值观 / 王瑾 陈珊
- 《名人传》之价值探寻及其启示 / 邱宗珍 肖文艳
- 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与变异 / 王焕玲
- 解构与续造:语文教育功能的失范与矫正 / 孙文亮
- 基于文化图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李代丽
- 对儿童阅读的思考 / 国庆丰
- 让阅读根植课堂内外 愿书香带来生命精彩 / 程淑芝
- 通识教育理念下的高校学生语文教育分析 / 段晓先
- 关键是思维品质的培养 / 张蕾
- 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 胡青宇 石舞潮
- 对外汉字写字教学基本策略研究 / 耿红卫
- 语文教学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 赵明
- 认知诗学下英美文学教育研究 / 张静 崔莹
- 随文象格习作:抵达语用的澄明之境 / 欧加刚
- 英美文学教学设计 / 于嘉琪
- 《论语》的教育思想与艺术表达 / 何小江
- 论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作用 / 行玉华
- 高等教育管理下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岳朝杰
-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的比较与借鉴 / 胡赤兵
- 解读卡夫卡《变形记》的语言意蕴 / 闫继苗
- 托妮·莫里森《秀拉》中的女性人物诠释 / 曹佳璠
- 探讨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 张文波
- 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 / 王琳琳
- 论《小雅》诗群的乡土情结 / 苗珍虎
- 艾丽丝·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探析 / 刘艳芹
- 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探讨 / 喻晓薇
- 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女性视角的审美解读 / 宋元源
- 《老人与海》悲剧式英雄的特征论析 / 黄麟斐
- 《麦琪的礼物》的艺术特色简论 / 刘海燕
- 《小妇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再分析 / 皮艳玲
- 解读《小世界》的反讽艺术 / 许瑛
- 创新与突破 / 杜嘉
- 《觉醒》中的象征主义 / 张丹
- 《檀香刑》中的狂欢化色彩赏析 / 赵彬彬
- 探析我国唐代体育诗的勃兴与审美内涵 / 陈荣浩
- 论唐代诗词中体育活动描写研究 / 付宏
- 浅析《乐府诗集》中诗与乐的完美结合 / 黄彬
- 试论《史记》的语言特色 / 孙利华
- 汉语词汇的西化现象及影响探析 / 张颖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陈昌学
- 《说文通训定声》用于形声字教学的探索 / 郭常艳 刘在鑫
- 隐喻理论下浅析《到灯塔去》中的叙事策略 / 陈江宏
- 语言交际中基于合作原则的语用预设研究 / 李彦美 刘秀云
- 论语言学中话语分析理论与语境研究 / 王冬梅 张菅 胡文华
-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与内涵 / 卢丙华
- 北京延庆县方言元音格局的实验研究 / 王泉月 杨春霞
-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英国诗人雪莱诗歌评析 / 户晓娟
- 浅析“X+死我了”结构 / 刘欣朋
- “疋”族字探析 / 余高峰
- 探析《围城》中的比喻艺术 / 孔瑛
- 浅析约翰·契佛小说的反讽语言艺术 / 韩丽
- 模因论下对“正能量”一词的解读 / 李伟
- 《红色英勇勋章》中幽默语言的教学设计 / 金红卫
- “孤平”新解 / 王定康
- 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研究 / 吴新
- 语文阅读技巧在英语阅读中的运用 / 王康妮
- 语文教育语境下大学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 梁杰
- 论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 / 陆晓蓉
- 《老人与海》译本的翻译美学语言赏析 / 樊初芳
- 高校德育工作中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路径 / 薛珊珊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初探 / 张益君 徐永军
- 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述略 / 靳长青
- 教改语境下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路径 / 康宇
- 汉语借词英语现象看西方文化的影响 / 尚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