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28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28
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与变异
◇ 王焕玲
摘要:莫言善于突破语言的常规,对其小说的语言进行创新和变异,这种创新和变异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修辞的创新和变异,这也形成了莫言独特的语言风格。但是创新和变异一定要符合语境,切合主题,否则会割裂文意,削弱作品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莫言 语言 创新 规范
引言
莫言是一个敢于大胆突破创新的作家,这种突破和创新不仅表现在他的创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小说语言的突破常规的运用,他善于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和变异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
一、词汇的创新与变异
语言的贫乏与语言表达对象的丰富这一矛盾对作家来说似乎是永恒的,这就迫使他们通过另一途径来扩大语言的表现能力——在现有的词汇外自创新词。莫言说:“创作就是突破已有的成就、规范,解脱束缚,最大限度地去探险、去发现,去开拓疆域……”莫言善于在现有的旧词或固定短语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从而创造出一个新词,这种方法在莫言的语言中表现为四种类型:
(一)变换语素(字、词)
莫言作为一个新派作家,他在小说中非常注重词语的变异,在碰到一些老词和熟语的时候,首先是改变词语的构造成分,从而在旧词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词,以取得特定的修辞效果,使新词在小说语言中的表达更具体、更贴切。
(1)那些矿山机械是黄色的。黄色令人昏昏欲醉。(《酒国》)
(2)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白棉花》)
(3)一驴当先的沙月亮,拉住驴缰,停住驴步。(《丰乳肥臀》)
在例(1)中,作者将“昏昏欲睡”中的“睡”换成“醉”,例(2)将”妙语如珠”的“珠”换成了“糖球山楂葫芦”,例(3)将成语“一马当先”中的“马”变换成了“驴”,这种做法在修辞学上叫做“仿拟”。仿拟可以是语素的模仿,也可以是词语、句子甚至是段落的模仿和替换,这种在不改变原义的前提下,变换语素(字、词)的方式,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使表意更加符合小说的语言环境。以上例句的成功在于符合情境的需要,顺应了感情的表达,因文制宜,既精确恰当地表现了事物的特征,同时又造成新颖幽默的效果。
(二) 拆词重组
拆词重组是指故意将一个相对稳定的词语拆开后重新组合或者是将词语拆开后中间增加一些其他成分。拆词重组后,词语固有的紧密程度虽然弱化,原有的结构形式也被改造,但其语言的表现功能却被拓展,语用价值得以实现。在莫言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拆词重组的例句。
(4)庞大男人接过枪,连准都不瞄,托平就放,砰砰两声响,清脆欲滴,震耳欲聋。(《丰乳肥臀》)
(5)我随着儿子往红树林子深处走。愈往里进美景愈不胜收。(《食草家族》)
汉语中的离合词结构比较松散,在这种离合词的中间可以加入别的成分,如“洗澡”——“洗了一个澡”等,但汉语中这种词语很少,大部分词语结构比较紧密,不能随意岔开,例如例(4)中的“瞄准”不是“离合词”,被临时分拆用成两个词, 例(5)的“美不胜收”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固定短语,被拆分后变成了“美景愈不胜收”,语义无差别,但语用功能增强了,让读者感到了新颖,更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造成了读者的审美愉悦。
(三) 语素(字、词)颠倒
(6)丁钩儿说:“我舍不得打死你。吓唬你。不要人仗狗势。十点多了,早该开大门!”(《酒国》)
(7)您这些话犹如醍醐灌顶,使我顿开茅塞。(《酒国》)
(8)我因有把柄留在他手里,不敢争竞。自我安慰地叹息一声。(《食草家族》)
例(6)故意将成语“狗仗人势”中的“狗”和“人”两个语素的顺序颠倒,讽刺了利用大黄狗吓唬侦查员丁钩儿的看门人,充满了讽刺意味。例(7)将成语“茅塞顿开”的前后两个字颠倒,例(8)将“竞争”颠倒为“争竞”,除此之外,还有诸如 “彩光”“诉告”“诉哭”“啸叫”等颠倒词。一般来说,故意改变词或短语的语序的做法是不符合词汇规范的,但是,如果能够合境应情,因文制宜,倒序型造词仍然是成功的词语创新。
(四)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异
(9)小老舅舅既不坐拖车,又不骑骏马;人各有志,不得勉强。(《食草家族》)
(10)“快松手,滚出来,你们这些混蛋女流氓!”我跺着脚吼叫。(《食草家族》)
“人各有志”本来是褒义色彩的词语,可是用在例(9)中,却变得不伦不类,因为小老舅不想坐车,也不想骑马,与人的远大志向毫无关系,这样使用给人一种啼笑皆非的荒唐的感觉。“混蛋”“女流氓”都属于贬义词语,在例(10)这个特殊的语境中使用,却表现出了主人公看到这些漂亮女孩子身处险境时的担心和忧虑。
二、语法的创新与变异
莫言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只是完全按照小说语言创作的原则和规律,他敢于突破常规,在有悖于固定语法原则的基础上去创作,他在语法上的创新与变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语法义变异、能指所指关系的重构。
(一)语法义变异
(11)爷爷灰溜溜地爬起来,羞羞答答地蛇行到桌前,挺不好意思地说:“活了一辈子,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食草家族》)
(12)马儿们吃得香甜,肚子渐渐圆溜溜,眼睛也更加光彩。(《食草家族》)
例(11)中,“蛇”本来是一个名词,在这里活用作状语,表示“像蛇一样地爬行”,莫言将之临时变异为可以修饰动词的状语,恰当地表现出了爷爷在看到好吃的食物时馋嘴、害羞的神情。例(12)中的“光彩”常用作名词,在这里被副词“更加”修饰,这种特殊的临时用法,打破了“更加有光彩”这种常见的结构模式,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更能衬托出马儿吃饱之后的神采。
(二)能指所指关系的重构
莫言在修辞实践中,常常有意打破语言原有的固定的音义关系,在特定语境中重构一种临时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使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陌生化,表达一种独特的意义。
(13)我奶奶是一个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娘婆”,她认为瓜熟自落。(《蛙》)
(14)马儿们哦哦叫着,弹动着轻松愉快的蹄子,与我的姐妹们耳鬓厮磨着。(《食草家族》)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意思是什么也不做,以使天下得到治理。现在只取其字面义,用于表示什么也不做,等待小孩自己从娘肚子里出来。“耳鬓厮磨”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的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意思,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固定短语,在例(14)中作者用它的字面意思,描写出马儿们和那些漂亮的女孩们惬意相处的和谐场景,这种打破常规的用法,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三) 定语或状语的移位
定语或状语的移位都是根据作者的审美诉求与主观感情的需要来表达的,更体现了作者使用词语的任意性,显示了作者思维的活跃。
(15)大虎被他们这种微笑的冷淡激怒了。(《红树林》)
(16)小王八蛋家油黑大门禁闭,几枝腊梅开得火旺,从墙头上鲜红欲滴地探出来。(《奇死》)
以上的这些搭配在平常看起来都是有逻辑错误的,但在莫言笔下,却是词语灵活运用的体现,作者驰骋的思想感情在笔下就表现为词语的任意搭配,这种用法反而会起到突出重点、强化主观感觉的效果。如例(15)中,正常应该是“冷淡的微笑”,但在作者或主人公看来,真正激怒他的是“冷淡”,尤其是虚情假意的“微笑的冷淡”,所以从逻辑或传统语言规则来看这句话是搭配错误的,但其实是再精确不过的了。例(16)中明明是“鲜红欲滴的腊梅”,作者却将定语移位,起到了强调修饰语的效果,而且显得语言灵活多变,新颖俏皮。
三、修辞的创新与变异
修辞的创新和变异主要表现为通感构成的超常搭配。通感是指人的五官功能出现了互相补充、互相转换的沟通现象,它常常运用在感情或感觉的个人化的超常搭配中,却又别具特色。
(17)老头脸上腻腻地响了一声,仰面朝天摔在地上。(《狗道》)
(18)大哥和二哥用小板凳打击高马脑袋的沉闷而潮湿的声响在耳边回响着。(《天堂蒜苔之歌》)
在莫言的小说中,所有的感觉系统仿佛都被充分利用,完全置入情景之中。例(17)中的听觉被转化为触觉,似乎更生动。而(18)听觉上也转为具体可触的触觉,新颖形象,更具有效果性,所以说,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手法,将各种感知刻画得更为绘声、绘色、绘形,更加容易同读者分享。
四、对莫言小说语言创新与变异的理性思考
莫言小说语言突破了已有的语言规范,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让读者感觉到新颖、独特。但是作者在创作中有时为了刻意地追求创新,却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影响了作品意思的表达。
(19)疯骡起初还尥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撅着屁股承揍。(《蛙》)
(20)……则寥若晨星,凤其毛,麟其角…… (《酒国》)
例(19)中的“承揍”显然是作者的生造词,词义晦涩难懂,不如直接写“挨揍”,更加口语化,更加通俗。一般来讲,词语的形式与内容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融合性,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运用。在例(20)中不拆分“凤毛麟角”刚好可以和上面的“寥若晨星”相对应,可以清楚完整地表达出珍贵稀少的意思,作者却又将其拆分为“凤其毛,麟其角”,修辞效果不明显,反而使读者理解起来更费力。
结语
总之,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与变异已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享受,但是语言的变异一定要以语言的表达效果为前提,如果仅仅为了追求怪异,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反而会影响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语
参考文献
[1]胡永刚.我的故乡,我的创作灵魂——访著名作家莫言[J]. 新作文(高中版),2004(10).
[2]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20.
[3]李宏亮.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元话语运用分析[J].语文建设,2013(35).
[4]林建法,徐连源.当代作家面面观[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64.
[5]王丽.奇异瑰丽 灵动活跃——莫言小说语言特点分析[J].语文建设,201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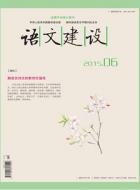
- 解读古诗文的教育价值观 / 王瑾 陈珊
- 《名人传》之价值探寻及其启示 / 邱宗珍 肖文艳
- 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与变异 / 王焕玲
- 解构与续造:语文教育功能的失范与矫正 / 孙文亮
- 基于文化图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李代丽
- 对儿童阅读的思考 / 国庆丰
- 让阅读根植课堂内外 愿书香带来生命精彩 / 程淑芝
- 通识教育理念下的高校学生语文教育分析 / 段晓先
- 关键是思维品质的培养 / 张蕾
- 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 胡青宇 石舞潮
- 对外汉字写字教学基本策略研究 / 耿红卫
- 语文教学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 赵明
- 认知诗学下英美文学教育研究 / 张静 崔莹
- 随文象格习作:抵达语用的澄明之境 / 欧加刚
- 英美文学教学设计 / 于嘉琪
- 《论语》的教育思想与艺术表达 / 何小江
- 论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作用 / 行玉华
- 高等教育管理下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岳朝杰
-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的比较与借鉴 / 胡赤兵
- 解读卡夫卡《变形记》的语言意蕴 / 闫继苗
- 托妮·莫里森《秀拉》中的女性人物诠释 / 曹佳璠
- 探讨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 张文波
- 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 / 王琳琳
- 论《小雅》诗群的乡土情结 / 苗珍虎
- 艾丽丝·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探析 / 刘艳芹
- 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探讨 / 喻晓薇
- 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女性视角的审美解读 / 宋元源
- 《老人与海》悲剧式英雄的特征论析 / 黄麟斐
- 《麦琪的礼物》的艺术特色简论 / 刘海燕
- 《小妇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再分析 / 皮艳玲
- 解读《小世界》的反讽艺术 / 许瑛
- 创新与突破 / 杜嘉
- 《觉醒》中的象征主义 / 张丹
- 《檀香刑》中的狂欢化色彩赏析 / 赵彬彬
- 探析我国唐代体育诗的勃兴与审美内涵 / 陈荣浩
- 论唐代诗词中体育活动描写研究 / 付宏
- 浅析《乐府诗集》中诗与乐的完美结合 / 黄彬
- 试论《史记》的语言特色 / 孙利华
- 汉语词汇的西化现象及影响探析 / 张颖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陈昌学
- 《说文通训定声》用于形声字教学的探索 / 郭常艳 刘在鑫
- 隐喻理论下浅析《到灯塔去》中的叙事策略 / 陈江宏
- 语言交际中基于合作原则的语用预设研究 / 李彦美 刘秀云
- 论语言学中话语分析理论与语境研究 / 王冬梅 张菅 胡文华
-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与内涵 / 卢丙华
- 北京延庆县方言元音格局的实验研究 / 王泉月 杨春霞
-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英国诗人雪莱诗歌评析 / 户晓娟
- 浅析“X+死我了”结构 / 刘欣朋
- “疋”族字探析 / 余高峰
- 探析《围城》中的比喻艺术 / 孔瑛
- 浅析约翰·契佛小说的反讽语言艺术 / 韩丽
- 模因论下对“正能量”一词的解读 / 李伟
- 《红色英勇勋章》中幽默语言的教学设计 / 金红卫
- “孤平”新解 / 王定康
- 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研究 / 吴新
- 语文阅读技巧在英语阅读中的运用 / 王康妮
- 语文教育语境下大学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 梁杰
- 论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 / 陆晓蓉
- 《老人与海》译本的翻译美学语言赏析 / 樊初芳
- 高校德育工作中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路径 / 薛珊珊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初探 / 张益君 徐永军
- 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述略 / 靳长青
- 教改语境下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路径 / 康宇
- 汉语借词英语现象看西方文化的影响 / 尚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