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3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35
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 胡青宇 石舞潮
摘要:语文难教,不仅因为语文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因为我们没有准确把握语文之“文”的人文内涵。只有准确地把握了语文之“文”的人文内涵,理解了语文是什么;抓住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理清了语文应该教什么,才有可能解决语文怎么教的问题。
关键词:语文教学 人文内涵 人文支点
引言
语文难教是业内公认的。怎样才能教好语文?这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个理论问题——它涉及到语文之“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要探讨怎样教好语文,我们必须从探讨语文之“文”的内涵开始。
一、语文之“文”的形式之争
语文之“文”究竟是什么?自从1950年“语文”作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出现以来,对“语文”的解释就争议不断。
对“语文”最狭义的解释是:语文=语(口语)+文(文字)。这一说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它突出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忽略了其人文性,容易使语文教学被简化成语言技能教学。
为了凸显“语文”的人文性,有人提出:语文=语(口头语)+文(文字+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作品,积淀了丰富的人文信息。只不过,这些信息都经过了文学艺术的加工,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的。因此,学习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以审美的方式走近、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
然而,把“语文”之“文”仅仅解释为“文字”与“文学”,还不足以囊括语文这一学科全部内涵。为此,有人进一步提出:语文=语(口头语言)+文(文字+文章)。如此一来,则“语文”这一概念就把所有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作品都囊括其中了。这一说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语文的外延,但也失之于太宽泛,使语文无所不包,从而使之有不能承受之重。
从对语文之“文”的各种解释可以看到,争议主要集中在“文”究竟是文字、文学还是文章的形式之争。大家于此各执一词。
二、语文之“文”的人文内涵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形式之争来理解语文,则语文之“文”究竟是文字、文学还是文章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文字、文学还是文章,都只是“文”的形式,而不是“文”的实质内容。换句话说,不涉及“文”之实质性内容的形式之争,对语文课程的建设是没有理论价值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2003年的《语文课程标准》撇开了对语文之“文”的形式之争,高屋建瓴地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这里虽然没有对语文下定义,但却揭示了语文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并从理论上回答了语文教什么的问题——即教学生掌握民族语言交际工具;教学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因而,语文工作者要追问的就不再是语文之“文”的形式是什么,而是语文之“文”的人文内涵是什么。
众所周知,“人文”是一个无限广延的概念。凡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属于人文范畴。其表现形式千姿百态,不一而足。但具体到语文之“文”的人文内涵,我们可以把它高度概括为“知、情、理”三个主要方面:
知,即以器物文明和技术文明为代表的知识。真实可靠的知识,可以增进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拉近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丰富人的经验,提升人的生存能力。让人在充满风险的世界安然栖居。
情,即情感。丰富美好的情感,是人生获得成功与幸福的关键因素。因为丰富美好的情感不仅是健全人格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的才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人类丰富多彩的情感,在文艺作品中展现得最为动人,也给予人类自身的成长以最丰厚的滋养。
理,即道理。正道与真理,教导我们分辨真善美与假丑恶,让我们懂得忠孝仁信礼义廉耻;引导我们遵循科学的规律与自然相处,遵循正确的价值规范与社会相处,教导我们作智慧、正直、高尚、有价值的人。
这三方面,是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语文课程的教育目标——把人培养成德才兼备、情感丰富、内心幸福的人。
三、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把握了语文之“文”的人文内涵,也就找到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知、情、理。语文教学只有把握这三大人文支点,凸显其人文性,才可能更好地实现其课程教育目标。
(一)知——广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2]
语文承载的文化信息特别丰富,并因此而具有特殊的育人功能。所以,孔子教导子鱼从学语文开始认识世界:“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
语文承载的信息特别复杂:特定的文字,其释义在其他课程中都是相对单一的,而在语文中却必须是多维的、全息的;特定的篇章,其释义在其他文本中都是明确、清晰的,而在语文中却是多义的、复指的,难求甚解的。人类所创建的知识体系的广泛的互文性,在语文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每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涉及到其他的任何事物;所有的思想联想和传统都可以合法地变成一个文本的一部分;每一个文本都可以通过新的阅读而发生别的一些联想;各种文本是相互联系的。”[4]知识体系的互文性,使得语文课上遇到的问题,经常需要借助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互文”,才有可能阐释清楚。语文的全息性和多义性,也经常使得不同人对相同的教材,解读出的信息,在量上不对称,在质上不对等。
一般来说,从同样的语文教材中解析出的人文信息越是丰富,“互文性”越是广泛,就越是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语文的人文价值。因此,没有承载丰富的人文信息,不可能成为一堂好的语文课;没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和广博的知识视野,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语文老师。
当然,要求语文课承载尽量广博的人文知识,不只是为了让学生多学一些知识,更是为了让知识相互印证,达到求“真知”的目的。因为学习者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越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事物,从而更有可能获得“真知”。
(二)情——美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5]
文学作品,因为饱含美好的情感而彰显出其艺术美、人文美;人,同样因为美好的情感而彰显出其人格美、人性美。
情感性,是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因此,文学作品是情感教育的最好材料;而情感教育则对人格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看到了语文课程与情感教育、与人格成长之间的这种关联,所以,2003年的《语文课程标准》郑重指出:“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6]
人类的情感丰富细腻,但不是每一种情感都很美好,比如仇恨与嫉妒,傲慢与偏见。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如此。美好的情感养成的是健全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丑陋的情感养成的则是残缺的人格与粗糙的心灵。因此,语文教师要善于发现、欣赏美好的情感,并以此教导学生向善、爱美,懂得爱与宽容。
(三)理——真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7]
语文不仅承载了广博的知识,能够传递丰富的情感,也积淀了深厚的“道”——既包括天道,即自然法则;也包括人道,即世俗伦理。由此而论,语文不仅承担了传播真知的使命,承担了情感教育的使命,还承担了传道的使命。
作为自然法则的“道”,多数时候是作为确凿的知识出现在语文教材里的,都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真理,只需要以经验来印证。而作为世俗伦理的“道”,介于其自身是一种价值尺度,所以它受人文传统、社会现实、利益立场的影响十分明显,素来有正道与邪道之分。正道教养的是高尚健全的人格;邪道塑造的则是畸形残缺的人格。因此,语文教学在“传道”的时候,尤其要传播正道、传播真理。
结语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课不仅是以知识内容来教育学生。同样的知识内容,在一个教师手里能起到教育作用,而在另一个教师手里却起不到教育作用”。[8]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善于挖掘教材的教育价值。具体到语文课,同样的教材,有的老师讲得很精彩,有的老师的课却很乏味,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理解语文的人文内涵,有没有把握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作为一门综合性人文课程,语文教学中只要抓住了“知、情、理”这三个人文支点,语文课就不难教。当然,具体到某个语文篇目,因其写作的着重点不同——有的重知、有的重情,有的重理——教学的重点也自然因之而不同,而无需面面俱到。语
参考文献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2]庄子.庄子·逍遥游[M].北京:中华书局,2007:3.
[3]论语·阳货[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4]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7.
[5][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
[8]邵宗杰,裴文敏,卢真金主编.教育学(修订三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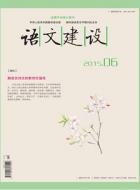
- 解读古诗文的教育价值观 / 王瑾 陈珊
- 《名人传》之价值探寻及其启示 / 邱宗珍 肖文艳
- 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与变异 / 王焕玲
- 解构与续造:语文教育功能的失范与矫正 / 孙文亮
- 基于文化图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李代丽
- 对儿童阅读的思考 / 国庆丰
- 让阅读根植课堂内外 愿书香带来生命精彩 / 程淑芝
- 通识教育理念下的高校学生语文教育分析 / 段晓先
- 关键是思维品质的培养 / 张蕾
- 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 胡青宇 石舞潮
- 对外汉字写字教学基本策略研究 / 耿红卫
- 语文教学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 赵明
- 认知诗学下英美文学教育研究 / 张静 崔莹
- 随文象格习作:抵达语用的澄明之境 / 欧加刚
- 英美文学教学设计 / 于嘉琪
- 《论语》的教育思想与艺术表达 / 何小江
- 论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作用 / 行玉华
- 高等教育管理下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岳朝杰
-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的比较与借鉴 / 胡赤兵
- 解读卡夫卡《变形记》的语言意蕴 / 闫继苗
- 托妮·莫里森《秀拉》中的女性人物诠释 / 曹佳璠
- 探讨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 张文波
- 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 / 王琳琳
- 论《小雅》诗群的乡土情结 / 苗珍虎
- 艾丽丝·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探析 / 刘艳芹
- 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探讨 / 喻晓薇
- 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女性视角的审美解读 / 宋元源
- 《老人与海》悲剧式英雄的特征论析 / 黄麟斐
- 《麦琪的礼物》的艺术特色简论 / 刘海燕
- 《小妇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再分析 / 皮艳玲
- 解读《小世界》的反讽艺术 / 许瑛
- 创新与突破 / 杜嘉
- 《觉醒》中的象征主义 / 张丹
- 《檀香刑》中的狂欢化色彩赏析 / 赵彬彬
- 探析我国唐代体育诗的勃兴与审美内涵 / 陈荣浩
- 论唐代诗词中体育活动描写研究 / 付宏
- 浅析《乐府诗集》中诗与乐的完美结合 / 黄彬
- 试论《史记》的语言特色 / 孙利华
- 汉语词汇的西化现象及影响探析 / 张颖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陈昌学
- 《说文通训定声》用于形声字教学的探索 / 郭常艳 刘在鑫
- 隐喻理论下浅析《到灯塔去》中的叙事策略 / 陈江宏
- 语言交际中基于合作原则的语用预设研究 / 李彦美 刘秀云
- 论语言学中话语分析理论与语境研究 / 王冬梅 张菅 胡文华
-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与内涵 / 卢丙华
- 北京延庆县方言元音格局的实验研究 / 王泉月 杨春霞
-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英国诗人雪莱诗歌评析 / 户晓娟
- 浅析“X+死我了”结构 / 刘欣朋
- “疋”族字探析 / 余高峰
- 探析《围城》中的比喻艺术 / 孔瑛
- 浅析约翰·契佛小说的反讽语言艺术 / 韩丽
- 模因论下对“正能量”一词的解读 / 李伟
- 《红色英勇勋章》中幽默语言的教学设计 / 金红卫
- “孤平”新解 / 王定康
- 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研究 / 吴新
- 语文阅读技巧在英语阅读中的运用 / 王康妮
- 语文教育语境下大学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 梁杰
- 论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 / 陆晓蓉
- 《老人与海》译本的翻译美学语言赏析 / 樊初芳
- 高校德育工作中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路径 / 薛珊珊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初探 / 张益君 徐永军
- 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述略 / 靳长青
- 教改语境下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路径 / 康宇
- 汉语借词英语现象看西方文化的影响 / 尚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