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4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
ID: 423045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的比较与借鉴
◇ 胡赤兵
摘要: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传递出两位大家身为人父幸福又烦恼的情绪,反映出他们对待子女的责任,折射出特定时代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两位作家《儿女》的创作背景,通过不同视角比较朱自清与丰子恺在作品中所折射出的不同情怀,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观和作品特色大有裨益。
关键词:《儿女》 幸福 烦恼 责任
引言
1928年,由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在第19卷第10号上同时登载了他的两个好友朱自清和丰子恺的同题散文《儿女》。那一年,同庚的朱自清和丰子恺都是5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刚好步入而立之年。这两个私交甚笃、志趣相投的挚友,在他们的同题散文《儿女》中从不同角度真切地表达了身为人父的种种复杂感受,研究二位大家的作品对于探索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特色及文学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儿女》的创作背景
朱自清的《儿女》与丰子恺的《儿女》都表达了父亲对待儿女的深情厚谊,同时也彰显了两位作家不同的背景经历。朱自清出生于书香门第,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朱鸿钧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所以父亲在生活上对朱自清格外疼爱,同时在学习上对其严加管教。30岁时,身为5个孩子的父亲,朱自清一如当年父亲对自己一样,对孩子们既严厉又慈爱。1928年,朱自清写作《儿女》时,第一任妻子武仲谦还在世。1916年与武氏结婚时,朱自清才十九岁。二十一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十年间,5个孩子就接踵而来。虽然朱自清初为人父时还很年轻,如野马一般,难以忍受这些累赘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的羁绊,但身为人父所带来的幸福感觉也不时流淌在心间。
丰子恺作为丰家的独子,备受宠爱,打小就被包裹在众星捧月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伴随着他的成长,浸透在他的性格里,铸就了他“慈父”的情怀。他“常常抱孩子,喂孩子吃食,替孩子包尿布,唱小曲逗孩子睡觉,描图画引孩子笑乐;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1]在他的心目中,儿童“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2]他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笑了,他觉得比自己笑更快活;孩子们哭了,他觉得比自己哭更悲伤。对孩子温柔悲悯的情怀,使丰子恺比常人更用心去体味为人之父的幸福。孩子们的任何举动,在他看来都是天真无邪、可爱至极的。在创作《儿女》 时,丰子恺是带着艺术情怀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将孩子的种种幼稚与调皮进行了“美化”,如孩子的幼稚在他的笔下美化成了小英雄的不凡气概。他能够常常以孩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由此他和孩子的心灵息息相通,因而内心恬静悠然,他的《儿女》也就是以此为标准。
二、《儿女》折射出的作家情怀
朱自清与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中折射出了作家不同的情怀,可以分别从幸福、烦恼、责任三个视角解读。
首先,从幸福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朱自清在《儿女》中,说起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他如数家珍:“五个月的阿毛,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想出去溜达时就大声喊叫;三岁的闰儿,是个逗人开心的小胖子,口齿不清,发音模糊,‘好’经常说成‘小’,走起路来蹒跚可笑;七岁的阿菜,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而且不管你爱不爱听,每天都会在饭桌上喋喋不休地给大家报告学校里的人和事;十岁的阿九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没事就坐着或躺着看书。5个孩子,脾性不一,性格迥异。”朱自清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儿女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寥寥数笔就点石成金,把孩子们的稚气可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朱自清一向强调写作的“至诚的态度”,他在文中所叙之事都是些生活小事,看起来琐碎平庸,但字里行间倾注着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体现出其幸福情怀,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丰子恺在《儿女》中描述了他和四个孩子坐在地上吃西瓜的场景是其幸福情怀流露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丰子恺作品中,三岁的阿韦边吃西瓜边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的“ngam ngam”声,五岁的瞻瞻马上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七岁的软软与九岁的阿宝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用散文和数学的兴味归纳为:“四个人吃四块西瓜。”对此,丰子恺的点评是:“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面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人在吃西瓜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3]经丰子恺用艺术家的妙笔一点,这个日常的生活细节立即让人过目难忘。不仅表现出天伦之乐给予丰子恺的幸福,把他舐犊情深的心理描摹得入木三分。
其次,从烦恼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1928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对立的动荡时期。作为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既不满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为,又对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不甚了解,因此一时间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这种苦闷和彷徨的情绪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就演变成了由家庭拖累所产生的种种烦恼,包括身为人父的烦恼。带着一群孩子就像“蜗牛背了壳”,虽是叶圣陶的比喻,但却是朱自清的切身感受。《儿女》中对每天“如两次潮水一般”的午饭和晚饭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一群孩子的喧闹中无可奈何地郁闷。面对孩子们的吵闹和不听招呼,朱自清有时会很不耐烦,会叱责孩子,甚至会在孩子们身上落下自己沉重的手掌。丰子恺虽然极其喜欢孩子,但孩子们的淘气顽皮同样给他带来过烦恼。他在家乡石门湾平屋中的小书桌上规规矩矩地摆满了笔墨纸砚,不喜欢任何人乱动。但是孩子们一旦爬上去,一切就乱了套。挥洒自来水笔弄得一桌子一衣襟的墨水点,把笔尖蘸在浆糊里,撞翻茶壶,打碎壶盖……孩子们的这种捣乱、破坏和损毁行为,也会让丰子恺不甚其烦,忍无可忍,于是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丰子恺写道:“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显而易见,年轻的父亲不堪孩子们扰闹,想要独自清净。但对丰子恺而言,孩子们带给他的烦恼只是瞬间的,他立即就会为自己对孩子们的态度感到后悔,所以骂过之后立刻换上笑脸,夺了孩子们的东西之后马上加倍奉还,骤然举起的手会在半空中变软,对孩子小脸的批打顷刻间会变成抚摸。
最后,从责任视角解读作家的情怀。朱自清在《儿女》中谈到朋友黄少谷、丰子恺、叶圣陶为孩子们操心、付出时,深感惭愧。同时,对自己做父亲的责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首先要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要给孩子们力量。孩子们将来能否大学毕业,能否成才,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朱自清也没有“一定的主意”,但他深知教孩子“怎样去做人”是最重要的。孩子的人生观和职业等,可以由他们自己去定,家长须尽的是指导责任,要帮助孩子们去发展自己,培养孩子的胸襟与眼光是作为父亲最迫切的任务。朱鸿钧曾经写信叮嘱朱自清好好培养阿九,信中写道:“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想起父亲的仁慈及谆谆教诲,朱自清更是感到自己之前对孩子们的体罚和叱责是多么的残酷。在对自己过往的行为进行忏悔和自责之后,他决定“好好地做一回父亲”,承担起身为人父的责任。丰子恺一直是儿童崇拜者,他对孩子总是充满着长辈的慈爱。在他看来,“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4]所以,丰子恺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摆家长的架子,他和儿女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对于父母应对子女承担什么责任,丰子恺虽说“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其实他早已了然于胸。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丰子恺始终奉行的是“儿童本位”的理念。他不仅疼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对普天之下的儿童都具有一种爱心和同情心。他主张成人要站在孩子的立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孩子所想,尊重和呵护他们。不要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丰子恺认为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人”,故而保护孩子们的童心不受现实世界的浸染,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
结语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从问世至今已近一个世纪,朱自清和丰子恺以他们的父爱情怀与读者分享了为人之父的酸甜苦辣。虽然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有诸多差异,作为父亲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但二人在各自的文章中表现出的那种与儿女之间至爱至仁的骨肉亲情却如出一辙,作品中展示的作者情怀为后世父亲带来深远意义的启示。同时,朱自清是以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为背景来写的这篇文章,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处体现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家庭生活的种种反感。而丰子恺则是以艺术为背景来写这部作品。让自己与孩子们的世界融入起来,形成了自然和谐的局面。二位作家的创作特色及情感在作品中具有明显的体现。解读二位大家的作品,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观和作品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语
参考文献
[1]丰子恺.《子恺漫画选》自序[A].丰子恺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丰子恺.儿女[A].丰子恺散文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3]朱自清.儿女[A].朱自清经典散文集[C].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1.
[4]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A].鲁迅杂文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白马湖作家群散文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4ZC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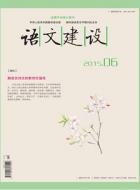
- 解读古诗文的教育价值观 / 王瑾 陈珊
- 《名人传》之价值探寻及其启示 / 邱宗珍 肖文艳
- 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与变异 / 王焕玲
- 解构与续造:语文教育功能的失范与矫正 / 孙文亮
- 基于文化图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李代丽
- 对儿童阅读的思考 / 国庆丰
- 让阅读根植课堂内外 愿书香带来生命精彩 / 程淑芝
- 通识教育理念下的高校学生语文教育分析 / 段晓先
- 关键是思维品质的培养 / 张蕾
- 语文教学的人文支点 / 胡青宇 石舞潮
- 对外汉字写字教学基本策略研究 / 耿红卫
- 语文教学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 赵明
- 认知诗学下英美文学教育研究 / 张静 崔莹
- 随文象格习作:抵达语用的澄明之境 / 欧加刚
- 英美文学教学设计 / 于嘉琪
- 《论语》的教育思想与艺术表达 / 何小江
- 论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作用 / 行玉华
- 高等教育管理下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岳朝杰
- 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儿女》的比较与借鉴 / 胡赤兵
- 解读卡夫卡《变形记》的语言意蕴 / 闫继苗
- 托妮·莫里森《秀拉》中的女性人物诠释 / 曹佳璠
- 探讨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 张文波
- 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 / 王琳琳
- 论《小雅》诗群的乡土情结 / 苗珍虎
- 艾丽丝·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探析 / 刘艳芹
- 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探讨 / 喻晓薇
- 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女性视角的审美解读 / 宋元源
- 《老人与海》悲剧式英雄的特征论析 / 黄麟斐
- 《麦琪的礼物》的艺术特色简论 / 刘海燕
- 《小妇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再分析 / 皮艳玲
- 解读《小世界》的反讽艺术 / 许瑛
- 创新与突破 / 杜嘉
- 《觉醒》中的象征主义 / 张丹
- 《檀香刑》中的狂欢化色彩赏析 / 赵彬彬
- 探析我国唐代体育诗的勃兴与审美内涵 / 陈荣浩
- 论唐代诗词中体育活动描写研究 / 付宏
- 浅析《乐府诗集》中诗与乐的完美结合 / 黄彬
- 试论《史记》的语言特色 / 孙利华
- 汉语词汇的西化现象及影响探析 / 张颖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陈昌学
- 《说文通训定声》用于形声字教学的探索 / 郭常艳 刘在鑫
- 隐喻理论下浅析《到灯塔去》中的叙事策略 / 陈江宏
- 语言交际中基于合作原则的语用预设研究 / 李彦美 刘秀云
- 论语言学中话语分析理论与语境研究 / 王冬梅 张菅 胡文华
- 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与内涵 / 卢丙华
- 北京延庆县方言元音格局的实验研究 / 王泉月 杨春霞
-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英国诗人雪莱诗歌评析 / 户晓娟
- 浅析“X+死我了”结构 / 刘欣朋
- “疋”族字探析 / 余高峰
- 探析《围城》中的比喻艺术 / 孔瑛
- 浅析约翰·契佛小说的反讽语言艺术 / 韩丽
- 模因论下对“正能量”一词的解读 / 李伟
- 《红色英勇勋章》中幽默语言的教学设计 / 金红卫
- “孤平”新解 / 王定康
- 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研究 / 吴新
- 语文阅读技巧在英语阅读中的运用 / 王康妮
- 语文教育语境下大学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 梁杰
- 论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 / 陆晓蓉
- 《老人与海》译本的翻译美学语言赏析 / 樊初芳
- 高校德育工作中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路径 / 薛珊珊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的创新路径初探 / 张益君 徐永军
- 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述略 / 靳长青
- 教改语境下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路径 / 康宇
- 汉语借词英语现象看西方文化的影响 / 尚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