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8期
ID: 140640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8期
ID: 140640
有感于“用网络语言玩转文言文”
◇ 彭慧
去年年底,成都市外国语学校周密老师“用网络语言玩转文言文”的作法在报纸、电视、网络各类媒体中纷纷得以报道,这种将新兴元素融入课堂的教学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为单调乏味的文言文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给学生单靠死记硬背的文言文学习平添了几分乐趣,周老师也因此被网友们亲切称为“最潮语文老师”。作为一名从事古汉语教学的一线教师,笔者同样受益匪浅、感触良多,但与此同时又不禁心生疑问:用“网络语言玩转文言文”固然可取,但却仅仅停留在人物品评、情感剖析的表面,而未触及文言文教学释读字词、疏通语义的根本。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兼顾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首先,古人和今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大相径庭,但他们的精神追求、思想情感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将现代社会的人情冷暖、喜乐悲忧适度融入对文言文情感内涵的理解中,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引导学生领会作品的主题。正如周密老师所言,张岱《湖心亭看雪》所表现的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寂寞”、“纠结”的情感,但这种“寂寞”并非忸怩作态、故弄玄虚,而是一种远离俗世、孤芳自赏的情怀,这种“寂寞”源于他幽远脱俗的情致和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高尚品质;这种“纠结”也不是庸人自扰、矫揉造作,而是一种人生渺茫、世事难料的感伤,这种“纠结”源于他难以排遣的满心哀愁和故国沦亡、壮志难酬的人生境遇。又如,在《桃花源记》中,作者陶渊明所描写的实际上是一次“放飞心灵”、“放飞梦想”的过程,是他对现实社会倍感厌倦、对世态人情深感忧心时为自己带来的一次特殊的“心灵旅途”。与此同时,桃花源中那阡陌交通而鸡犬相闻、男女老少怡然自得的生活又是作者在一次次的“纠结”和“矛盾”后对黑暗现实的一种“超脱”、一种“叛逆”。流传至今,“世外桃源”已成为一种和平宁静、安乐自得的象征,每当人们在现实中迷茫受挫、困顿不堪时,它便成为我们心头迫切的向往和渴望。
其次,从古至今,虽然汉语的词汇形式不断推陈出新、语法手段也代有革新,但它仍是一个不断发展而又前后相承的有机整体,因此我们可以从微观上将现实生活中具体可感的语言现象或词语表达引入文言字词的释读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学生掌握字词的用法。例如,通假字是文言文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学生学习中尤为不解的地方,对此我们可以巧妙结合今人书写中有意无意写别字的情况来加以说明。一方面,古今历史条件虽然大有改观,但古人和今人书写时趋简避繁的心理以及他们可能遇到的提笔忘字或形近字混淆不分的问题基本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为了迎合这种心理或解决这一问题,古人和今人采取的措施也基本是一致的,即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替代原字,如《伤仲永》中“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中以“扳”代“攀”、《大道之行也》中“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以“矜”代“鳏”,今人写字以“爱戴”作“爱带”、以“松弛”作“松驰”等。由此可见,通假字与错别字在形成原因和存在方式上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化雅为俗、变复杂为简单,充分利用前者来解释后者,以前者的具体可感性来融化后者的抽象陌生性。当然,作为古今不同时代的产物,两者的差异又是不言而喻:前者是在缺乏用字规范的情况下人们的一种用字习惯,带有集体性和约定性;后者是在用字规范既已形成的情况下人们的一种用字错误,带有个人性和偶然性。此外,词义的理解又是学生学习中至关重要而又倍感吃力的地方,对此我们可以充分调动成语、俗语、方言等一切积极因素来加强他们的记忆,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例如,《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红豆》“春来发几枝”及《春晓》“夜来风雨声”中的“来”皆非动词而是用作时间名词的词尾,但由于对汉语的发展演变缺乏足够的了解,学生或许感觉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将今人口头上常说的“有钱难买老来瘦”、“少年夫妻老来伴”以及“老来得子”、“老来俏”等适时援入其中,他们便会顿开茅塞。又如《陈情表》“晚有儿息”中“息”即“子、儿”之义,但受常用义“作息、气息”的影响,学生一时或许迷惑不解,但如果我们将“利息、儿媳”二词引入其中,并告诉他们利息就是由本钱而生的利润、儿媳就是以子喻子妇而为示区别又增“女”旁,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又如,同义词语“饥”与“饿”的区别也是容易混淆的地方,但我们只需介入“忍饥挨饿”一词,并形象说明动词“忍”与“挨”的对立,二者表意程度上的深浅之分便会昭然若揭、历久难忘。
总之,思想内容的阐发与字词义的疏通是文言文教学中是并重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后者又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我们汇通古今、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情,从而实现对作品思想情感的全面解读时,我们更需要援今入古、融今人之言于古人之语,以期获得对文言字词的准确认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最终实现语文课程语言应用的“工具性”和陶冶心性的“人文性”。
彭慧,河南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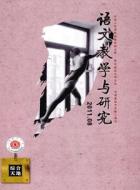
- 如何让学生自主学习 / 杨文娟
- 古诗文学习四法 / 毕庆
- 语文教学中的美育渗透 / 唐自新 罗尚英
-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 / 周晓平
- 中职语文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 / 董静
- 情感教育与语文教学 / 覃东雷
- 追寻课堂小练笔的实效性 / 陈桂程
- 学习应从培养兴趣开始 / 徐超
- 寻找语文课美的支点 / 曹文格
- 乡村事件 / 何丽萍
- 一朵花里看世界 / 陈青山
- 从移情说看高中阅读教学的情感策略 / 孙文芳
- 新课标理念下的高中语文生命教育 / 常利
- 怎样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 李东敬
- 文言文教学的猜读法 / 张杰
-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 苑文青
- 语文学习中如何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 王文明
- 作文语言的锤炼和素材的积累 / 敖林
- 初中作文情境教学法 / 杨佰玲
- 作文教学中发散思维的训练 / 杨红艳 许海涛
- 初中作文有效教学的思考与尝试 / 张丽
- 学生参与评改作文的六个步骤 / 袁治信
- 漫谈作文的批改技巧 / 周玉芹 赵培泉
- 网络化条件下写作教学的一点思考 / 于秉飞
- 作文教学的举三反一 / 陈鸿儒 陈严
- 阅读教学的个性化特色之我见 / 陈荣华
- 创建良好的家庭读书环境 / 吕正红
- 让学生真正走进文本 / 孙友江
- 如何提高初中生的语文素养 / 齐慧艳
- 从整合学科教学来提高学生作文能力 / 张婉红
- 教师写“下水”作文的意义 / 朱永涛
- 情景教学法在作文教学中的运用 / 钱冬宁
- 模仿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一种捷径 / 吴青松
- 我手写我心 美文出个性 / 曾祥兰
- “介绍作者与背景”环节的巧处理 / 鲍周生
- 写作教学中的三种语言训练 / 仓峰
- 语文阅读教学的三个步骤 / 王芹
- 教会学生阅读的方法 / 李刚珠 魏华
- 阅读在高中新课程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张继红
- 语文课堂中的模糊教学探析 / 龙莲明
- 备课与有效教学 / 黄丽芳
-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导入 / 申翠英
- 发挥学生学习课文的主动性 / 白春娟
- “活动单导学”课堂教学模式 / 司锦芬
- 例谈语文高效课堂切入点的选择 / 潘晓红
- 打造蓝色的语文课堂 / 钱文波
- 创建充满活力的语文课堂 / 李彩虹
- 第一课时教学内容的合理取舍 / 渠咏梅
- 品位课堂的三个层面 / 金庞 藤丽霞
- 课堂教学中的提问艺术 / 孙炜康
- 语文课改中创建高效课堂的几点体会 / 郑春玉
- 让智慧在语文课堂探究教学中闪光 / 王书月
- 让电影走进语文课堂 / 熊芳
- 走活语文课堂的第一步——导入 / 于翠丽
- 如何提高语文教师课堂教学技能 / 代伟锋
- 论教学设计的几个原则 / 李玉兰
- 巧用评价语言 激活语文课堂 / 刘玉春
- “元宵词鉴赏”创新教学设计 / 王晓光
- 中学语文高效课堂的打造 / 王爱勤
- 作文教学魂兮归来 / 胡向华
- 也说“木叶” / 乐建兵 朱国
- 浅析汉乐府中的妇女形象 / 张素梅
- 音乐诗的情感魅力 / 杨小兰
- 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 郭旺仙 周菊英
- 试论《小团圆》结构上的艺术得失 / 宋秀红
- 读《心声》 / 杨俊锋
- 也释“敢以烦执事” / 章玲芳 赵火夫
- 有感于“用网络语言玩转文言文” / 彭慧
- 从歌词中学语言 / 金红 程正祥
- 《醉翁亭记》和《前赤壁赋》的比较 / 杨丹华
- 一字之差的“情” / 姚建礼
- 《阿房宫赋》课堂教学实录 / 李翔
- 《山中访友》一文确有败笔吗 / 王贤德
- 《钱塘湖春行》与《天净沙.秋思》教案 / 雷玲
- 如何提高诗歌赏析得分率 / 滕朝胜 程志新
- 《兰亭集序》说课稿 / 刘燕 周云波
- 古代诗歌鉴赏答题指要 / 张冬梅
- “仿用句式”说课稿 / 王敏
- 古代诗歌鉴赏中表现手法的分析 / 王薇
- 考场作文如何拿高分 / 韩世昆
- 语文教学也要效率优先 / 张蕊
- 应重视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 / 陈文君
- 多一点赏识 多一份收获 / 杨丽 唐峰
- 读《简.爱》有感 / 陈露
- 瞬间 / 熊晓彤
- 明礼慧心 谱写德育新篇章 / 黄万武
- 谈谈学生如何对待考试 / 隋淑娜
- 古诗赏析之望闻问切 / 所福亮
- 高中语文探究教学模式的反思与对策 / 叶士娟
- 文言文教学应重在文言 / 任志恩
- 文言文教学的新思考 / 李晓东
-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指瑕 / 余慧芬 郭西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