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0期
ID: 423192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0期
ID: 423192
多面孔的亨利
◇ 李振华 刘春瑜
摘要:《梦歌》是约翰·贝里曼的代表作,对现代西方诗坛影响巨大。贝里曼通过梦的日记形式记叙了亨利在世界上浪荡时所表现的个性,叙述了人类生活的各种主题,包括人类的情感以及人类的精神问题。在这部梦的日记中,贝里曼赋予了亨利不同的面目。亨利在诗中或受崇拜,或遭嘲讽,或被人同情,诗人则或远或近地站在一旁操纵,话虽出自亨利的口,却受了诗人的控制,这样的安排可以达到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的线性的多面视像的效果。亨利这个人物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代表美国的民族、历史和社会,他为美国历尽生活艰辛的、富于人性的中年白人树立了一个神话。
关键词:多面孔 叙述人称 聚焦 声音 距离
一、《梦歌》中叙述人称的变化反映多面孔
在第一人称叙述中,第一人称代词指叙述者(叙述成I或者self)和故事的一个角色。如果叙述者是故事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或她就是I作为主角。如果他或她只是配角之一,那他或她可以使I作为目击者,也可以作为共同主角。对于聚焦来说,第一人称叙述可以来自于叙述成I的事后叙述,也可以来自于故事中的角色I这个更局限和天真的层面。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被定义成叙述人I和故事中的角色I,当故事中的角色I扮演主要角色时,他就变成了讲述自己故事的主角。他当然参与了叙述活动,但他的叙述非常有限。他只能讲述他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观点。然而,他不能叙述其他人的想法。他的视角有固定的中心。既然主角叙述者可以直接呈现,那么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可以近也可以远,或者又近又远。第十四首是《梦歌》最重要的诗歌之一,它就是一首I作为主角叙述的诗歌。亨利厌倦了生活,感到现代生活的精神空虚。这首诗是“我”作为一个叙述者也是主角的真实想法的独白。读了这首诗后,读者不仅同意“我”在诗中说的,而且会同情“我”。所有这些都是I作为主角的功能。正如I作为主角模式,这个叙事框架的自然结果就是目击者没有更多地接近别人的心理状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向其他角色的无限的知识投降,他选择允许目击者把作为观察者能合理发现的内容告诉读者。对于其他人的心理状态,他可以在故事中告诉其他角色以得到他们的观点。他也可以对主角进行采访或者读信件、日记和其他文字性内容。与主角叙述者相比,目击叙述者有更多的流动性和范围更大种类更多的信息来源,因此在故事中发挥了从属作用。[1]在诗歌第四十八首中,叙述者就是作为目击者的。亨利变成一个说着上帝死在他无法理解的阿拉姆语的神秘人。他失去了他的爱,感到很沮丧。叙述者“我”作为目击者和倾听者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并想安慰他。无论“我”是作为主角还是目击者,读者可以得出亨利被不同的面具掩饰着来表达他的爱恨、恐惧和沮丧,尤其是他失落的感受。我们同样可以感受贝里曼的自我觉醒完全隐藏在亨利的话语、行动和思想中。
在第二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旁白和主角都是作为同一个人,存在于叙述的同一层面上。在这种环境下,就是一个完全一致的叙述。在一些戏剧性的独白和内心独白中,叙述者将他自己作为第二人称的“你”,向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像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贝里曼在诗歌第二十首用了这种叙述模式。在这首诗中,亨利向自己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和困惑。
第三人称叙述是角色中心叙述,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没有或很少涉及其中。叙述者、旁白和角色保持了一种综合结构形式和稳定的距离关系,在叙述中发挥各自的作用。这三者之间保持着一个规则的三角形,每一个都与另外两个保持着一定距离。《梦歌》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关系赋予第三人称叙述的。在第一百二十一首中,亨利作为一个评论家独自生活在蒙羞的人类世界中。他爱他的一个学生但却以失败告终。在这里,亨利是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和一个爱情失败者。
二、《梦歌》中的聚焦
无论故事在语篇中何时呈现,它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视野出发。这个视野与被看到的人或事之间的关系称为聚焦。聚焦分为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内部聚焦指一个角色作为一个演员参加故事同时起到一个聚焦设备的功能,这种内部聚焦也叫被缚角色聚焦。外部聚焦指位于故事外部的匿名代理人起到一个外部聚焦设备的功能。诗歌第四百零六首采用了“内心独白”这种明显的内部聚焦给读者一个对亨利内心状态的清晰认识。这一情节呈现出亨利情感的爆发。我们可以通过内部聚焦感知亨利的内心。他站在他父亲的坟墓上,带着对可怕的银行家的坟墓的愤怒和不屑。他甚至破坏了他父亲的衣物。读到亨利的这些行为,我们感到既同情又惊讶。他父亲对他做了什么,是什么让他如此疯狂?亨利的愤怒被如此鲜明地描述,这个场景的部分效果是来源于运用了内部聚焦。如果使用外部聚焦,亨利对他父亲的愤怒不能被刻画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和生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的心理复杂不能被展示得如此尖锐、清晰和感人。
第一百四十四首诗歌从内部聚焦变为外部聚焦。叙述者叙述了亨利身上发生的事和他周围的世界。通过叙述者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当亨利知道他的朋友死了会是什么样。他悲伤地连对女儿的第一个奖励也兴奋不起来,对他妻子的生气也毫不关心。叙述者既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像目击者一样没有人情味。因此,叙述者的聚焦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他的内心世界。他完全陷入了悲痛和愤怒。他看到一群灵魂在绝望的痛苦中。这里从第三人称叙述转为第一人称叙述,从外部聚焦转为内部聚焦既合理又自然。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完整地构思亨利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
在《梦歌》中,“我”不仅是叙述者,还是诗歌的主角。在诗歌中,叙述者往往比主角知道的更多,即使他自己就是主角,因此对于通过主角的旁白聚焦是有局限性的。读者倾向于接收亨利的观点。但是旁白聚焦有它固有的缺陷,它会产生偏见和限制。约翰·贝里曼往往让他的叙述仅仅呈现一个事实而给读者留出想象和猜测的空间。[2]在大部分的叙述中,亨利关注的事件是事情对他是怎样的和他那时的感受。通过内部和外部聚焦,读者可以轻松地读出亨利的多面孔。
三、《梦歌》中的声音和距离
声音指通过传递给观众事件和存在的事物的言语。叙述者在一部小说中可能是隐含作者,也可能是主角或者配角。隐含作者对全文负责,包括叙述者和隐含读者。约翰·贝里曼将《梦歌》创作成一种讽刺史诗,其中亨利是一个在漫长的战争中与所有想毁灭他的事物斗争的英雄。诗歌的语调有喜剧色彩,但是带有大量悲伤和压倒性失落和挫折的喜剧。这些情感也是对贝里曼自身情感的描述。亨利被死亡、沮丧、失望、绝望、婚姻失败、无聊、犯罪和酗酒所折磨。诗歌还包含了一些大的主题如人的不同情感、跟物质有关的内容、心理问题等。所有这些主题都通过叙述者的声音传递,有时叙述者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是亨利叙述了这个社会、他的爱情、他的友谊、他的绝望和对朋友和父亲的失落感。叙述同时包括两个声音:亨利的和约翰·贝里曼的。
声音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很少被精确定义的关键词。声音是一种常用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的声音可以包含在作者的声音中,创造出双重声音。在诗歌第一首中包含了现在时和过去时两种时态,这两种时态表达了不同的声音。通过I see his point, -a trying to put things over./ I don’t see how Henry, pried /open for the entire world to see, survived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隐含作者的声音。“Hard on the land wears the strong sea/and empty grows every bed”意味着亨利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他是预先确定的死亡和失败。在第一百五十首中,读者首先接收到叙述者的声音并知道亨利是一个著名的、努力的和有魅力的英国人。突然,作者的声音出现:渴望成名的乐趣在哪里?这里作者将他自己的声音转变成了亨利的声音。[3]看起来好像是作者和主角亨利之间有了交谈,在作者旁白的同时,亨利编织了一张网,这种张力增强了生命的空虚,即使亨利获得了声誉。
在读了《梦歌》全卷后,读者可以清楚地理解亨利传递的其实是贝里曼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利在相同的现实世界中承受了很多,他无法预言将要发生什么,但他能确定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必须面对和承受。约翰·贝里曼曾经说过,意图和物质,对于白人来说,诗人意味着代表自己和其他人的声音,其他人的声音代表他自己,这就是他的意图。其他人指谁?——美国人。虽然亨利与贝里曼非常相似,但亨利只是一个小说角色,他传递的是贝里曼多愁善感的、怀旧的和内省的声音。在某些方面诗人和亨利是相同的,然而,当贝里曼让自己秘密地从亨利中分离出来时,亨利是贝里曼一系列的想法。因此,贝里曼的自我觉醒隐藏于亨利的声音之中。亨利的声音暗示了层次性,塑造了一个美国中年白人的神话。
约翰·贝里曼的文学影响之巨大和广泛是毋庸置疑的,贝里曼通过叙述人称、聚焦、声音和距离这些独特风格的叙述手法,再以梦的形式,诗人很巧妙地将自我意识与亨利的经历融合在一起,再现了亨利这个人物的多面孔形象,塑造了一个美国白人的神话。
参考文献
[1]黄希云.小说人称的叙述功能[J]. 外国文学评论, 1996(04).
[2]孙绍振.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J].语文建设, 2008(03).
[3]胡蓉.《红字》中人物的圣经原型与意象剖析[J].湖湘论坛, 200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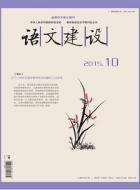
- 关于小学校本国学教育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 刘传启
- 反思“朗读”在现代语言教学中的价值 / 雷春华 饶振辉
- “先学后教”小学语文校本教研的研究与实践 / 高阿莉
- 现代教育技术在语文课中的运用 / 廉芹
- 古诗词朗诵对初中语文口语训练教学策略的影响研究 / 陈军民
- 高职语文教学在职业能力需求下的全新变革 / 刁晓丹
- 教材作业系统的变化与新课改下的文言文教学 / 王华
- 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与高考语文考试之区别 / 冯海英
- 从高校教师普通话课探析语文教学系统的断层 / 刘琰
- 感恩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饶宝美
- 大学语文改革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 符涛 李丽
-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生成性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 戚韵东
- 浅析语文课堂中教师的教学艺术 / 张晓凤
- 试论语文教育与大学生真善美教育的融合 / 许争昱
- 大学语文教学的审美功能浅论 / 毛德良
- 基于儿童叙事视角解读林海音《城南旧事》人性美 / 张艳辉
- 厄普代克《兔子富了》中喜剧氛围下的悲剧内涵 / 李小芹
- 论英国书信体文学的叙事模式 / 朱战炜
- 威廉·戈尔丁《蝇王》中象征内涵研究 / 陈彬婕
-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人物特点解析 / 郭鹏飞
- 冰心小说的创作艺术解读 / 杨荔
- 目的论视域下的《京华烟云》篇章解读 / 丁玲
-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生态理念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 朱秀芳
- 《红楼梦》的现代主义艺术特色研究 / 陈秀玲
- 试论《飘》中斯佳丽的人物形象 / 陈喜萍
- 《喧哗与骚动》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 安玮娜
- 《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的矛盾心理 / 李赟
- 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女性形象略谈 / 赵文娟
- 论《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象征与暗示 / 王晶虹
- 约翰·斯坦贝克《菊花》中的象征主义解析 / 韩荣
- 多面孔的亨利 / 李振华 刘春瑜
- 浅析《老人与海》中老人的独特品质 / 刘红
- 《生火》自然主义风格的意蕴表达 / 刘翔飞 赵芳华
- 《格列佛游记》中的讽刺艺术论析 / 王瑞琳
- 《名利场》中的艺术特色探略 / 樊宁
- 成功在于三转九弯: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意象探析 / 朱依理 胡梅红
- 《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主题思想新探 / 薛婷
-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流浪汉形象与表现艺术 / 陈述斌
- 《克拉丽莎》的女性成长简析 / 熊国芳
- 解读《一个人的遭遇》中困难主题的升华 / 武彦君
- 《镜花缘》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研究 / 康冬宁
- 论中西方文学中的武侠文化研究 / 许林海
- 王夫之《姜斋诗话》“情景”修辞语言生成解诂 / 李秀林
- 孔子的口才观研究 / 王莉
- 试论《简·爱》中的语言特点分析 / 闫晓雅
- 《红楼梦》中“的”字运用研究 / 殷宏雁
- 论言语交际中的认知语用研究 / 王予红
- 概念隐喻理论下卡明斯诗歌文本特征 / 陈晓丹
- 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研究 / 唐剑锋
- 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文本衔接模式 / 张平丽
- 浅析《绝望的主妇》中的语用移情 / 杨旭明
- 词汇视角下看语言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 / 刘燕
- 语文教育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 韩晶磊
- 高等教育管理下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冯卫梅
- 语文教学对思想素养的提升作用与融入路径 / 钱春芸
- 英语语法教学中汉语语法正迁移问题探究 / 张小燕
-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中汉语影响的弱化探析 / 陈宁红
- 语文教学审视下英语教学效果的提升思考 / 莫小芳
- 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中语文教育的功能再造 / 陆訸
- 论高校学生思想素养培育中语文教育功能的发挥 / 张艳丽
- 动漫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提升中大学语文教育的运用 / 潘明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