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0期
ID: 42318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0期
ID: 423185
试论《飘》中斯佳丽的人物形象
◇ 陈喜萍
摘要:作为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为故事背景展开的巨著,《飘》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作者通过其博大的笔触描绘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种植园经济社会的巨大生活画卷,更在于成功塑造了一系列经典鲜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刻画了斯佳丽这样一个魅力独特、性格复杂的女主人公形象。本文主要从家庭对斯佳丽的影响入手,从其表面特征、内心意志、两面性、自我追求等角度对这一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进行解读。
关键词:《飘》 斯佳丽 性格特征 人物形象
引言
《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也是倾注其全部心血的唯一作品。问世第二年,这部作品便获得普利策奖金,并于1939年被搬上银屏,成为好莱坞经久不衰的经典影片。小说以亚特兰大及其附近的一个种植园为故事场景,以美国南北战争为故事背景,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作品以斯佳丽对瑞德的爱情为主线,塑造了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斯佳丽、瑞德、艾希礼、梅勒妮等南方人形象,并着重刻画了斯佳丽这一矛盾、复杂又多面的核心人物。本文将从家庭对斯佳丽的影响入手对斯佳丽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一、家庭对斯佳丽的影响
女主人公斯佳丽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富足且颇有地位的种植园主家庭,父亲杰拉尔是爱尔兰移民,靠赌博赢得塔罗庄园的所有权,并开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编织自己的美国梦,他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母亲艾伦是美国东海岸法国移民的女儿,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道德观念,仁慈宽厚,深受白人庄园主的尊敬和黑人奴隶的爱戴。在内战爆发之前,斯佳丽就在这样一个奢华而舒适的家庭环境中渐渐长大。
有着大家闺秀风范的母亲自斯佳丽幼时便在她内心播撒了传统与纯洁的种子。她告诫斯佳丽在行为方面应当淑女而得体,要文静又可爱,在男士们谈话的时候,即便是自己真的比他们了解更多,也不能打断他们。于是,在斯佳丽身上有了天真与可爱的影子。对于只有十六岁的少女来说,在舒适散漫的生活中,生活的重心就成了掌握更多吸引男士的技巧。在成长过程中,除了母亲的教导,父亲杰拉尔的傲慢、固执对斯佳丽性格的形成也影响极大。她身上既有温和而过分讲究教养的贵族血统,又流淌着精明而凡俗的爱尔兰贫民血液,这样本不调和的质地在斯佳丽身上进行着混合。虽然她想沿袭母亲身上大家闺秀的风范,但骨子里父亲粗犷、豪爽、暴躁又不拘小节的性格因子又总会出现。因此,在父母旧式家庭教育的熏陶之下,斯佳丽表面上举止得体、温文尔雅,但实际上,端庄外表之下掩藏的是她那叛逆、反抗、倔强的真性情,也正是当时充满矛盾的环境造就了斯佳丽狂热奔放、敢爱敢恨、敢想敢做的性格特征。在这样的性格特征下,斯佳丽对社会陈规陋习的反叛与抗争精神得以充分展现。
二、斯佳丽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叛逆、倔强——鲜明的表面特征
在小说中,叛逆与倔强伴随斯佳丽的一生,并成为其鲜明的表面性格特征。与传统的贵族人物并不相同,斯佳丽的魅力在于敢于突破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旧制,尤其是繁复的传统社会规范。对于一个生活在男权社会的人物来讲,斯佳丽身上叛逆、倔强和反抗的精神与整个传统社会形成强烈撞击。
早在幼年时期,斯佳丽身上叛逆与倔强的特征便开始显现:她厌恶装作什么也不懂的样子,让男人来告诉他一切;偏爱与黑人孩子在一起玩耍;拒绝父亲杰拉尔为自己设计好的婚姻。后来,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下,她的叛逆愈加显露。当她站在旧有南方社会传统规范的对立面时,其反传统行为愈加明显而不加掩饰。在艾希礼拒绝与自己私奔之后,叛逆的斯佳丽突然决定与查尔斯结婚,在刺激艾希礼的同时挽回自己的面子,并真的在两周之后做了查尔斯的妻子。当查尔斯病死在前方后,斯佳丽突然变成了新寡妇。然而,这位新寡妇却并未悲伤,反而不顾卫道士们异样的眼光以及世人的非议,与“不怀好意”的巴特勒跳起她守寡一年后的第一支舞曲。她依旧我行我素,照样骑马、参加宴会,与男人调情卖俏。之后,为了保住塔拉庄园,斯佳丽更是将传统观念及礼教统统抛之脑后,利用谎言将妹妹苏伦的未婚夫弗兰克抢走。为了得到足够让她安心的钱,斯佳丽买下一个即将倒闭的木材加工厂,并利用各种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卑鄙”手段与同行竞争。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之后,斯佳丽又不顾亲友的劝阻与反对,无视整个亚特兰大上层阶级的鄙视,与瑞德结婚。在斯佳丽这一系列冲撞传统社会规范与礼制的行为背后,其叛逆与倔强的特征愈加鲜明。
(二)勇敢、坚强——突出的内心意志
从小说一开篇,与斯佳丽叛逆、倔强的表面特征紧密相伴的便是其坚强、勇敢的内心意志,而这种突出的内心意志同样一直伴随斯佳丽这一人物始终。斯佳丽一直爱慕艾希礼的绅士风度与英俊外表,并认为自己比梅勒妮更有魅力,在艾希礼即将宣布自己与梅勒妮订婚时,斯佳丽勇敢地向他表达爱意,并希望与之私奔。虽然,最终被艾希礼婉言拒绝,但这份勇敢表达爱意的勇气在当时那个虚伪保守的南方社会实属罕见。与斯佳丽形成鲜明对比,艾希礼懦弱无能、缺少激情与热情,显然他并不爱斯佳丽,但却并没有勇气面对斯佳丽并告诉她真相。于是在与艾希礼模糊的感情关系中,斯佳丽成了受害者。然而,即便艾希礼在感情上使自己蒙了羞,但斯佳丽仍不负艾希礼的托付,在内战期间留在即将临盆的梅勒妮身边悉心照料,并在战火纷飞当中载着刚分娩的产妇、婴儿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仆驾车赶路回家。于是,艾希礼由衷感叹斯佳丽具有“狮子般的勇气”、不懂害怕的含义。
实际上,斯佳丽不仅具有“狮子般的勇气”,更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在南方联邦军投降之后,内战终于结束,许多南方人都在为他们的失败而痛哭流涕、颓废不堪,而在斯佳丽的脑海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保住塔拉庄园尽快开始新的生活。即便是在最后,父亲去世,女儿夭折,梅勒妮去世,瑞德也离自己而去,生活中的一切光亮都消失殆尽,故事最终将以悲剧收场的时候,斯佳丽仍旧坚强,“等明天回到陶乐场再去想吧,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一切了,明天我会想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在故事结尾,斯佳丽的一句“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不仅给黑暗中的自己带来一线希望,也将其坚强的内心意志进一步强化。
(三)虚荣、贪婪——真实的人性两面性
《飘》中斯佳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复杂、矛盾,这种矛盾就在于其身上不仅有坚强、勇敢的一面,同时也并存着虚荣与贪婪的因子。斯佳丽身上复杂并矛盾的两面性使这一人物更加鲜活,也更加真实。
故事从斯佳丽对艾希礼炽热的感情讲起,然而,斯佳丽却并不了解艾希礼,她爱慕的仅仅是艾希礼绅士的风度与俊朗的外表,仅仅是因为艾希礼并不像其他男人一样猛烈地追求她、关注她。当她怂恿艾希礼与自己私奔但遭到拒绝之后,恼羞成怒的她给了艾希礼一巴掌。她对艾希礼虚幻的爱一直贯穿故事的始终,直至斯佳丽意识到“她的爱人只不过是她理想中的影子”,她对艾希礼那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出于征服欲与虚荣心之后,她不禁感叹,自己所爱的不过是一尊虚构的没有生命的偶像,她自己做了一套漂亮的衣服,然后就爱上了它。除了对感情的虚荣,故事中,斯佳丽性格中贪婪的一面同样展露无疑。斯佳丽对土地、金钱的强烈占有欲使她不顾社会道德规范以及舆论的约束,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并最终沦为一个唯利是图、憔悴不堪的庄园当家人。
尽管斯佳丽身上有着虚荣与贪婪的印记,但却并不使人憎恶,反而正是因为她身上体现着坚强与软弱、真实与虚荣、贪婪获取与无偿付出同在的复杂的人性两面性,这一人物才更加真实、鲜活、可爱。甚至我们会发现,斯佳丽有时很陌生,有时又那么面熟,像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又仿佛正是我们自己。
(四)女性意识觉醒——强烈的自我追求
《飘》的故事情节发生于当时正处在传统奴隶制与种植园经济体制下的美国南部,在这一片无垠的南部红土地上掩藏着深厚的男权主义思想。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经济上也不独立,她们往往要承受来自传统社会和男性的双重压制。而斯佳丽这一人物身上的女性意识却随着故事的深入发展不断觉醒,并得以加强,最终帮助她在社会上获得充分的话语权与自我价值。
在宴会上,斯佳丽因为嬷嬷要求自己像传统淑女一样做作而感到愤懑;当父亲将一段婚姻强加给自己时,她断然拒绝;当艾希礼拒绝与自己私奔时,斯佳丽气愤地称他为懦夫,称梅勒妮为百依百顺的傻小丫头。这些充满反抗精神与叛逆特点的行为和话语象征着斯佳丽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并开始萌芽生长。内战爆发后,女性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时期的斯佳丽开始更多地发现自己的价值,并真正开始从传统淑女的牢笼当中挣脱出来,走向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追求。在面临母亲去世、父亲发疯的窘境时,她没有被击垮,而是发出这样的呐喊——我要活下去,我绝不会再挨饿……上帝为我作证,北佬不会将我击垮。我要挨过这一关,等这一切过去我就不会再挨饿!后来,为了家人的生机,斯佳丽告别了高傲、骄奢的恶习,走进农田,在烈日之下组织家人采摘棉花;赤脚在荒地里为家人刨土寻找食物;为了保护家园,亲手杀死入侵家园的北方士兵。在内战当中,虽然斯佳丽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其女性意识也在这一阶段不断蜕变和加强,引领她冲破重重束缚与险阻,在困境中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内战结束之后,斯佳丽经营了木材厂,即便在已有身孕的情况下也不顾家人的劝阻忙于事业,后来她还经营了酒楼,并且生意愈来愈好。在这一阶段,斯佳丽身上的女性意识达到高峰,她已经从传统社会的贵族小姐成长为一个拥有充分话语权的成熟女性。她成功地从旧传统的牢笼和枷锁中挣脱出来,真正实现了其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Mitchell M.Gone With The Wind[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于丹.解读《飘》中斯佳丽的女性形象魅力[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02).
[3]任春梅,索明茹.《飘》中斯佳丽人物分析[J].电影文学,2010(16).
[4]焦悦梅.女性主义视角下《飘》中斯佳丽的人物形象[J].语文建设,201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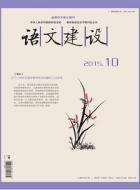
- 关于小学校本国学教育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 刘传启
- 反思“朗读”在现代语言教学中的价值 / 雷春华 饶振辉
- “先学后教”小学语文校本教研的研究与实践 / 高阿莉
- 现代教育技术在语文课中的运用 / 廉芹
- 古诗词朗诵对初中语文口语训练教学策略的影响研究 / 陈军民
- 高职语文教学在职业能力需求下的全新变革 / 刁晓丹
- 教材作业系统的变化与新课改下的文言文教学 / 王华
- 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与高考语文考试之区别 / 冯海英
- 从高校教师普通话课探析语文教学系统的断层 / 刘琰
- 感恩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饶宝美
- 大学语文改革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 符涛 李丽
-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生成性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 戚韵东
- 浅析语文课堂中教师的教学艺术 / 张晓凤
- 试论语文教育与大学生真善美教育的融合 / 许争昱
- 大学语文教学的审美功能浅论 / 毛德良
- 基于儿童叙事视角解读林海音《城南旧事》人性美 / 张艳辉
- 厄普代克《兔子富了》中喜剧氛围下的悲剧内涵 / 李小芹
- 论英国书信体文学的叙事模式 / 朱战炜
- 威廉·戈尔丁《蝇王》中象征内涵研究 / 陈彬婕
-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人物特点解析 / 郭鹏飞
- 冰心小说的创作艺术解读 / 杨荔
- 目的论视域下的《京华烟云》篇章解读 / 丁玲
-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生态理念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 朱秀芳
- 《红楼梦》的现代主义艺术特色研究 / 陈秀玲
- 试论《飘》中斯佳丽的人物形象 / 陈喜萍
- 《喧哗与骚动》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 安玮娜
- 《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的矛盾心理 / 李赟
- 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女性形象略谈 / 赵文娟
- 论《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象征与暗示 / 王晶虹
- 约翰·斯坦贝克《菊花》中的象征主义解析 / 韩荣
- 多面孔的亨利 / 李振华 刘春瑜
- 浅析《老人与海》中老人的独特品质 / 刘红
- 《生火》自然主义风格的意蕴表达 / 刘翔飞 赵芳华
- 《格列佛游记》中的讽刺艺术论析 / 王瑞琳
- 《名利场》中的艺术特色探略 / 樊宁
- 成功在于三转九弯: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意象探析 / 朱依理 胡梅红
- 《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主题思想新探 / 薛婷
-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流浪汉形象与表现艺术 / 陈述斌
- 《克拉丽莎》的女性成长简析 / 熊国芳
- 解读《一个人的遭遇》中困难主题的升华 / 武彦君
- 《镜花缘》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研究 / 康冬宁
- 论中西方文学中的武侠文化研究 / 许林海
- 王夫之《姜斋诗话》“情景”修辞语言生成解诂 / 李秀林
- 孔子的口才观研究 / 王莉
- 试论《简·爱》中的语言特点分析 / 闫晓雅
- 《红楼梦》中“的”字运用研究 / 殷宏雁
- 论言语交际中的认知语用研究 / 王予红
- 概念隐喻理论下卡明斯诗歌文本特征 / 陈晓丹
- 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研究 / 唐剑锋
- 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文本衔接模式 / 张平丽
- 浅析《绝望的主妇》中的语用移情 / 杨旭明
- 词汇视角下看语言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 / 刘燕
- 语文教育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 韩晶磊
- 高等教育管理下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冯卫梅
- 语文教学对思想素养的提升作用与融入路径 / 钱春芸
- 英语语法教学中汉语语法正迁移问题探究 / 张小燕
-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中汉语影响的弱化探析 / 陈宁红
- 语文教学审视下英语教学效果的提升思考 / 莫小芳
- 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中语文教育的功能再造 / 陆訸
- 论高校学生思想素养培育中语文教育功能的发挥 / 张艳丽
- 动漫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提升中大学语文教育的运用 / 潘明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