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19652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19652
《德伯家的苔丝》叙事空间分析
◇ 刘芳
摘要:托马斯·哈代的作品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作品向来是学术界、评论界的宠儿。对哈代作品的研究可谓是浩如烟海,研究流派更是百家争鸣。随着时代和文化语境的流转,对哈代作品的研究更多地从其文本本身转向写作技巧。《德伯家的苔丝》可以说是哈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品中苔丝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品中,与苔丝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有布莱谷、芙伦谷、棱窟槐、风神庙等地,故事发生地点的不同为我们从叙事学叙述中的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阐释《德伯家的苔丝》提供了可能,也为哈代小说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字:苔丝 叙事空间 命运
一、叙事空间在《苔丝》中的体现
叙事学近几年来是学术界的新宠儿,关于叙事空间,各家也有自己的观点。最早提出“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这两个概念的是《故事与话语》的作者叙事学家查特曼。查特曼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指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1]在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非苔丝这个形象莫属,托马斯·哈代将其称为“最纯洁的女人”,甚至为了这个虚拟的女人不惜和自己的妻子艾玛感情破裂,哈代在塑造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倾注的感情和心血。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在不断变换,成为我们重新解读苔丝命运的一种新方式。
哈代的“宿命论”总基调使苔丝也在劫难逃,但是作者在写《德伯家的苔丝》时的背景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已经是不可争论的事实,对西方上帝的理解也出现了最大程度的偏离,西方的福音书也因为过于理性化的形而上学使人类最大程度上偏离上帝。工业文明的铁蹄席卷整个英国,哈代心目中的自然也因为人类的文明而逐渐消失,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和上帝的相互偏离。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哈代的“维克塞斯小说”,其所采用的叙事模式是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而“全知的叙述模式一般不涉及自己的叙述行为的话语空间,而是直接把读者引入故事空间,在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状态中‘聆听’故事”。[2]在哈代的“维克塞斯”小说中,作者总体上将作品的大背景置于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发展的维多利亚时期,将爱敦荒原作为所叙述故事的大背景、大舞台,分别将布莱谷、芙伦谷、棱窟槐、风神庙等地作为苔丝不同人生阶段的发生地,并选择风神庙作为苔丝最后故事的终结地。而生养苔丝的爱敦荒原自始至终都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审视着大自然的女儿苔丝的悲惨一生,奠定了苔丝悲剧的总基调。不同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切换向我们展示了苔丝跌宕起伏的人生。布莱谷、芙伦谷、棱窟槐、风神庙这几个不同的地方与苔丝当时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呼应关系,从侧面衬托出苔丝坎坷的人生道路。在小说中,作者安排了苔丝三个不同人生阶段的话语空间不仅仅是为故事营造出更加真实的效果,还向我们展示爱敦荒原美丽多彩、地势多变的地理环境,在更多的时候,作品的话语空间与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寓意关系。
二、与苔丝命运紧密相关的空间
在哈代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都置于一个大的舞台背景之下,这就是爱敦荒原,在这个共同的背景之下展现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苔丝也不例外,作者为了表现出苔丝的坎坷人生路,又将苔丝人生中的不同阶段置于不同的小环境下,台上的每个人生阶段与其对应的自然环境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从侧面体现了苔丝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关系、更是体现了不同时期苔丝的不同命运,奠定了悲剧性的基调。布莱谷——奶牛场——棱窟槐是苔丝短暂的一生中三个最重要的生活坏境,这三个不同的地方同时也象征着苔丝命运的不同阶段、身处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时间分别对应着苔丝不同的人生阶段,达到了自然场景与苔丝命运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将苔丝的一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将苔丝的命运与自然环境、不同时间相呼应,与苔丝的内心发展相结合,体现出苔丝命运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向我们展现了爱墩荒原美丽的景色,更是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表现技巧。
(一)美丽富饶的布莱谷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一开头便向我们介绍了养育苔丝的布莱谷的一片繁荣景象:“这一片土壤肥沃、山峦屏障的村野地方,田野永远不黄,泉水永远不干。”[3] “全副景象,只是大山抱小山,大谷套小谷,而那些小山和小谷上,盖着一片连绵、丰茂的树,布莱谷就是这样。”[4]我们的女主人公苔丝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片富饶美丽的沃土上。当我们见到主人公时,此时的布莱谷正值万物繁茂、葱葱郁郁的五月,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主人公苔丝此时的生命也像这葱郁的自然一样富有生命力,虽然脸上还有童年稚嫩的神色,但已经称得上是一位端庄秀丽、身材高壮的美丽女子了。此时的苔丝含苞待放,也恰如这五月万物生长且即将成熟的月份。苔丝此时生活在布莱谷的精神面貌与这时的自然景象最为恰当地融合在一起:葱葱郁郁的植物、丰裕富饶的大自然、含苞待放的苔丝三者相互照应、融为一体,显示出自然与苔丝之间和谐的关系和苔丝这时风平浪静的生活。
(二)偶遇爱情的奶牛场
当苔丝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时,是受辱并失去唯一的儿子之后,此时的时间也恰是五月。这个五月不是布莱谷苔丝繁茂的生命力的象征,恰恰是将苔丝推向死亡深渊的爱情的诞生地。再次映入眼帘的苔丝刚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并为了开始新的生活而筹谋着第二次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奶牛场工作。一如哈代那为人“诟病”的写作风格,紧随着主人公苔丝的脚步我们也看到了奶牛场的景象。富饶美丽的奶牛场使苔丝有一种畅快爽朗之感,这里的空气清新、爽利、空灵,鸟儿的歌声听起来更是清脆动人,心境变了,苔丝似乎也变得更加美丽可爱。美丽动人的苔丝似乎还是没有察觉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在这恰如其分的时刻悄悄地来临了。在这里苔丝遇到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克莱尔,克莱尔是一个让苔丝又爱又恨的男人,是一个将苔丝推入死亡之谷的男人,结局是可悲的,但是爱情的开始总还是美好的。牛奶厂的繁茂景色也烘托出了苔丝对克莱尔的爱,她对克莱尔的爱正如她对生养她的大自然一样不含有一丝一毫的杂质。但是时刻相伴苔丝的爱敦荒原亲眼目睹了苔丝对克莱尔那纯洁无私的爱情破灭,而爱敦荒原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目睹苔丝沉醉于克莱尔那不切实际的爱情中无法自拔,这也与小说的总体基调相协调。
(三)冰封爱情的棱窟槐
棱窟槐可以说是苔丝生命当中最后一个重要的地方。苔丝来到这个条件最为艰苦的棱窟槐是被克莱尔无情地抛弃之后,是为生活所迫,更是为了弥补自己对克莱尔犯下的“罪孽”。“她来到这,仿佛是前生注定,非来不可似的。她一看周围的土壤那么贫瘠,就知道这里的活,一定是最艰苦的。”[5]荒凉高原的冬季奇景反映出了苔丝被克莱尔抛弃之后的低落情绪和悲凉的心境,也反映出克莱尔对苔丝的冷漠都不及这还能给苔丝一口饭吃的荒原。在条件最为艰苦地方的冬季,即使是极厚的皮手套也抵挡不住彻骨的寒冷,但是苔丝在此时的内心却还在奢求着克莱尔的原谅,而克莱尔对苔丝的态度不正是这悲凉的高原对苔丝的态度吗?棱窟槐也同时告诉我们:在这常人无法忍受的恶劣环境下,苔丝的心注也定要被冰封。
(四)“上帝”召唤的风神庙
风神庙作为苔丝出现的最后一个地点,可以说是情、景、人、心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那建于新时期的风神庙也与苔丝的处境、命运最为恰当地呼应:一边是现代社会文明和传统道德的牺牲品,一边是太阳神祭坛神灵的象征,场景与人物命运达到了最最高度的统一。作者选取这个在上古时代用来祭祀太阳的石阵——风神庙作为苔丝被捕的地点,有着自己的想法,因为红色是凶兆的象征,而太阳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是强大意志力的代表,像苔丝一样连养育自己的自然都不眷顾的底层人民又怎么可以与这强大的生命力对抗呢?而此时的苔丝误认为这个石阵是用来给上帝做牺牲的,不管是在太阳面前,还是在上帝面前,苔丝在这个诸神远离的时代不会受到任何庇护。就在次日的凌晨,当红日从石阵后升起之时,警察顺着太阳包围过来,苔丝的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正如哈代在小说的序言中所引用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李尔王》中的一句话:“神们看待我们,就好比顽童看待苍蝇,他们杀害了我们,为他们自己开心。”[6]
苔丝是大自然的女儿,哈代称之为“最纯洁的女人”,但是那又如何呢?工业文明的铁蹄已经席卷了哈代心目中的最后一方净土——爱敦荒原,此时的爱敦荒原在人类的过分行为下又能如何呢?自然也与亚雷口中的上帝达成了联盟,不再眷顾他的儿女们。爱敦荒原时时刻刻都陪伴在苔丝左右,可也只能用不同面孔从侧面反映苔丝命运,给予其最为委婉的暗示:美好繁茂的春夏象征着苔丝的生活安好,萧瑟冰冷的秋冬则预示着苔丝生活的落魄。作者安排了布莱谷、芙伦谷、棱窟槐、风神庙这四个不同的场景与苔丝不同的人生阶段相照应,不同的话语空间对应不同的故事空间,不仅为苔丝的生活故事营造出更加真实的效果,也全方位地向我们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净土爱墩荒原的美丽繁茂,更是表达了作者对自己家乡那份难以言表的情感。
结语
伍尔夫曾评价哈代是“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家”,在哈代的维克塞斯系列中,每部作品都是悲剧中的经典,《德伯家的苔丝》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谈论哈代的作品,很多人指责哈代的作品结构过于相近;主题近乎相同;人物失真化、过于理想化;情节线索单一……但是我认为正是这些帮助哈代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63.
[2]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8.
[3]肖伟胜.欧洲文学与文化[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3.
[4]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6.
[5]刘川.论哈代小说形式技巧的形成及意义[D].南京:南京大学,2012.
[6]吴笛.论哈代的创作中鸟的意象[M].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01:5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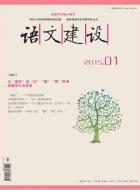
- 从“减负”说“记”“做”“悟”并举的教学行为变革 / 贺义廉 欧阳芬
- 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探讨 / 韩莹 孙福广
-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 顾青 吴魏
- 亦真亦幻 / 周灿美?严丽
- 对大学写作课堂活动有效性评价的分析 / 高惠宁
- 基于存在主义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龙倩彤
- 《远大前程》的课堂教学设计 / 牟英梅
- 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研究 / 张钧
- 高校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策略研究 / 李大鹏
- 高职语文的审美教育探索 / 杨利香
- 高职汉语言教学中的文学鉴赏 / 郑小娜
- 汉字书写教育应贯穿教育始终 / 王艳杰
- 情境作文 / 王宏兴 于桂言
- 基于审美体验的大学文学写作教学探索 / 王建英
- 扩大知识容量,强化情感体验 / 潘亦彤
- 论劳伦斯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 / 梁苑霞
- 论小说《1Q84》中人物的逃避与出路 / 李越
- 土地文化折射出的女性意识差异 / 孔倩云 王静
- 自然主义视角下对《棉被》的解读 / 吴婷
- 《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的孤独感解读 / 樊文琼
- 解读余华小说《兄弟》中的丑陋人性 / 于莹
-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象征意象解读 / 吴林 潘不寒
- 凸显与消解 / 董家丽
- 论《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的探索之路 / 冯建瑞
- 《德伯家的苔丝》叙事空间分析 / 刘芳
- 莫言《红高粱》的语言艺术特色分析 / 左文燕
- 略论《伤逝》的讽刺艺术 / 孙艺铭
- 《孔雀东南飞》婆媳形象的深度解析 / 陈正刚
- 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 艳春
- 空间理论观照下的梅尔维尔小说《比利·巴德》解读 / 杨晓君
- 伍尔芙《邱园记事》中的语言风格研究 / 谭杰
- 清初文人余怀诗词艺术特色探究 / 张晓娟?邢江平
- 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象征元素的生态解读 / 解学林
- 《古书句读释例》辨证 / 尹绪彪
- 诗化的江南古典园林文学 / 张晓辉
- 说“荇菜” / 赵祎缺
- 对惠特曼作品《草叶集》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 张丹
- 网络语言对青少年语言使用影响的研究 / 陈琳
- 构式语法理论下对流行语“今天你X了吗?”的解读 / 陈岩春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李陆萍
- 《红楼梦》“冷香丸”中的语言密码 / 郭孔生
- 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模糊语言的语用分析 / 翁向华
- 现代汉语存现句中“着”与“了”的使用考察分析 / 何大吉
- 概述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研究 / 李慎柱
- 论言语交际误解的语用学分析研究 / 贾萍
- 浅议文学作品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容琴
- 文化图式下文学作品语言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 梁艳红
- 英语写作中的汉语正迁移功能探微 / 张晓梅
- 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下汉语中的标识语翻译研究 / 张莲
- 语言中的文化基因及其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郭宪春?李侠
-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语言风格分析 / 王禄芳
- 语言教学方法策略研究 / 雍瑾
-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 刘娟?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