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19630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19630
亦真亦幻
◇ 周灿美?严丽
摘要:《蛙》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亦实亦幻的人物塑造,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段,以及最后九幕带有强烈魔幻色彩的话剧,将那个充斥着荒诞癫狂现实的历史年代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世人的审视与反思。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 人物刻画 叙事方法 荒诞夸张
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对莫言的影响
最初的魔幻现实主义出现在欧洲表现主义画作的相关研究中,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魔幻现实主义才在拉丁美洲被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并逐渐自成一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将理智与荒诞相结合,将现实置放于一种虚无幻象似的环境或气氛中描述,让现实世界穿上魔幻的外衣,使得亦真亦幻、真幻相融的风格贯穿整个文学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年孤独》中文译本的出现,震撼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坛。这部被称为是“继《堂吉诃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1],集荒诞、夸张、虚幻、讽刺、象征等多种描写手法于一身,并融入了神话预言及民间传说,为其作者马尔克斯赢得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中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得到了众多中国作家的喜爱和推崇,莫言便是其中的姣姣者。
莫言所受到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启迪了莫言关于写作观念的转变,正如他自己所言,读了许多相关的作品之后,“感到如梦初醒,我想不到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2]其二则是莫言以此为依托,展开了他此后大胆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之旅,以至于在他之后的作品如《生死疲劳》《酒国》等作品中都带上了《百年孤独》的影子,让人犹如置身于光怪陆离的幻境之中。
正是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之旅,帮助莫言踏上了文学创作的最巅峰。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青睐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莫言也因此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文学大家。正如莫言的颁奖词所提及的,他在作品中“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及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赋予莫言的小说无尽的魅力和久远的生命力。而《蛙》则是莫言于2009年创作的一部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并为莫言赢得了2011年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小说封面勒口的底端写着这样一句话:“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3]。于是,这部小说被评论家们定义为了“一部直面和反思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部展示中国六十年生育史”[4]的作品。然而,莫言所具有的诡异、奇幻、繁杂且无拘无束的创作力和想象力,注定将小说带入更高远的境界,而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赤裸裸地揭露了在特异的历史景况之下,个人的人性、品格、命运、甚至灵魂的畸变,展现出那段历史中戏剧性的幻变事实。
二、亦幻亦实的人物刻画
《蛙》中刻画的形形色色人物,脾气品性各具特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名字都多以身体的部位和器官词命名,诸如陈鼻、万足、王肝、王胆、袁脸、袁腮等等。所有的名字中,除了陈眉和姑姑万心的名字能用“正常”二字修饰之外,其他的人名,总让人有荒诞诡异之感。除此之外,王肝、王胆虽是一卵双生,但王肝身体高大,王胆却是长不大的袖珍侏儒,而这样的王胆,最后却嫁给了高头大马的陈鼻,陈鼻到老年无依无靠,靠着在李手“堂吉诃德”的小酒馆里出卖他的大鼻子,扮演堂吉可德为生。此外,从一开始出场就不同于常人“我”的准姑夫王小倜,那个据说被国民党电台女播音员娇媚的声音所蛊惑的战斗机飞行员,最后被传架着“歼-5”叛逃了台湾。还有秦河,那位曾受过严重刺激的才华横溢的学生,公社书记的弟弟,据说是姑姑的疯狂爱慕者,由最初街上的乞讨者,变为姑姑忠实的计划生育工作专职驾驶员,到最后的民间泥塑大师,以及一心痴恋“小狮子”若干年的王肝,在“小狮子”嫁给“我”之后幡然醒悟,之后一直随秦河左右。天生丽质且洁身自好的姐妹花陈耳、陈眉,一人在火灾中丧生,一人在大火中毁容,成日以黑纱掩面,最后为了替父还债,不得已替人代孕……一个个的人物在作家的笔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但同时亦带有浓重的虚妄色彩。他们的经历让人难以置信,而他们的结局更让人唏嘘不已,让人分不清造成这种“虚妄”的究竟是时代的嬗变,还是现实的无端,亦或是作家的虚幻。
当然,所有的人物当中,人生最跌宕起伏,经历最匪夷所思的,当属姑姑万心。从幼时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到成为受众人尊崇的“送子观音”,再到后来为了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地逼迫孕妇引产的“活阎王”。姑姑的角色,亦神亦魔。接生与引产、救人与杀人、菩萨与魔王,这些极端的反差由姑姑一个人体现出来,难免会让人觉得过于夸张而产生质疑,而对姑姑退休之后的描述,作者的夸张也毫无收敛之意:她“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5]她认定自己罪大恶极,于是终日供奉郝大手捏出来的泥娃娃,祈祷他们能获取灵性,转世投胎,企图以此来洗清并偿还自己的罪孽。作者用夸张荒诞的手法表现出姑姑性格中的矛盾,实则是映射了造成她人性分裂的那个时代的极端矛盾,即当时国家政策意志与民间传统伦理观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这种荒诞夸张的人物刻画手法,体现出作者对那段历史谬妄深入骨髓的批判和反思。
三、虚实结合的叙事方法
小说将三种叙事的文体,即文学素材、书信与话剧融为一体,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叙事方法颠覆性的革新。除此之外,在各类叙述的同时,作者总是或虚幻或讽刺或荒诞地描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人物角色的内心。例如第一章中孩子们在陈鼻、王胆的带动下集体吃煤,竟有如品尝饕餮盛宴般的欢愉,之后还满嘴乌黑地朗诵《乌鸦和狐狸》的描述,看似荒诞不经,实则让人五味杂陈:究竟是怎样的饥肠辘辘,才能逼迫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用煤炭充饥?再如描述“老娘婆”为产妇接生的画面时,作者形容她们“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这俨然是无常的化身,而之后姑姑接生陈鼻时与“老娘婆”田桂花的对比描述,更是极尽夸张讽刺,将那个时代特有的“老娘婆”的愚昧野蛮和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相类似的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还出现在姑姑为了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走火入魔”似的与各个超生孕妇及其家人们“斗智斗勇”的描述。于是,我们读到了姑姑强带张拳媳妇去引产时与其家人搏斗的“壮烈”场面,也目睹了身怀六甲的张拳媳妇为躲避引产,跳进河中用西瓜皮凫水逃走,最终导致早产,一尸两命的悲怆结局。作者将荒诞讽刺的描述穿插到真实历史事件的讲述过程中,更揭示出那个特定历史年代背景下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
当然,《蛙》中最为突出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莫过于描写姑姑受到青蛙的攻击以及对姑姑害怕青蛙缘由的描述。当姑姑醉酒之后路过一片洼地时,受到了蛙的攻击:“无论她跑得多快,那些凄凉而怨恨的哭叫声都从四面八方纠缠着她……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浩荡荡的大军,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有的生着两只金星般的眼睛,有的生着两只红豆般的眼睛,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6]其间,作者还时空倒错地穿插了姑姑内心的联想,那个“青蛙戏人”的传说,使得仿佛原本荒诞无稽的传说,无端的在现实中有了验证,也使整个叙事披上了魔幻的外衣。而关于解释姑姑害怕青蛙原因的叙述,则更像是描述另一个神奇世界的灵异事件:姑姑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吃下了青蛙肉丸子,感到肚子里翻腾不止,“似乎还有嘎嘎咕咕的声音”,于是低头呕吐,那些吐出的绿色小东西,一落到水里,即刻变成了青蛙……作者将这些神奇诡异的叙事发挥到极致,旨在表露出晚年姑姑人性的回归。她开始对自己以往走火入魔地捍卫计划生育工作的行为产生了难以排解的罪恶感。当姑姑想起为此枉死的王仁美、王胆等人,她就会觉得有无数只青蛙在追赶她,让她慌不择路,让她感到凉森森的腥冷,让她的灵魂无法安宁,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惊险而紧张、细腻却惊恐,并满带魔幻色彩的描述,作者成功地表现出了姑姑来自内心最深处的永无止境的罪恶感。
四、魔幻话剧中的癫狂现实
关于最后九幕话剧的深意,莫言先生曾有过如下的评述:“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话剧部分看似说的是假话,但其实里边有很多真话; 而书信体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话,但其实有许多假话”[7]。细细读来,这段话是在给世人传递信息:尽管话剧形式上“彻底的虚构”,但实则旨在讲述那些不可思议的癫狂事实,与书信部分强烈的对比反差不仅暗示了前面内容的貌真实假,还让之前所营造出的现实感几乎荡然无存。最后的整部话剧都充斥着诡异的氛围,阴森、幽黯、凄厉。主人公忽然转变为看似疯癫的代孕女陈眉,而情节亦如梦魇般的吊诡——姑姑以阴暗洞穴为栖身之所,婴儿冤魂般的青蛙频繁向其讨债,陈眉神经质般的控诉,压抑阴郁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最终看似露出正义曙光之后的晴天霹雳,乍看荒诞不经,细想却透露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现实,这或许便是作家想告诉读者的现实:“‘包待制智勘灰阑记’里的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不过是诗意的幻象,‘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般黑白颠倒、是非莫辨,方才是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正是作家笔下闪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逼迫着读者去直视历史现实之中的那些血腥和罪恶,感受那些癫狂事实中彻骨的寒意。
总之,《蛙》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段沉重的历史现实,亦将那段现实中人物的人生经历、命运结局以及人心人性毫无避讳地展现在世人眼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作品中时而夸张荒诞,时而调侃戏谑,时而虚幻讽刺的描写,呈现出的是我们民族历史中的罪恶与惩罚,死亡与生命,善意与恶毒,欢欣与苦痛,是对人性,对命运,对社会深刻的审视和反思。
参考文献
[1]彭彩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专题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2]莫言.恐惧与希望[M].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7: 162-163.
[3]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4]梁振华.虚拟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J].北京:中国图书评论,2012(4):93-98.
[5]孟庆树.莫言《蛙》三题[J].艺术广角,2011(1):54-57.
[6]徐桂萍.从“现实”到“魔幻”的审美视觉变化——莫言《蛙》的写实风格解析与启示[J].语文建设,2013(9):45-46.
[7]赵婉竹.魔幻哈哈镜中的艺术真实[J].戏剧文学,2013(5):9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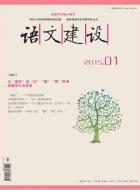
- 从“减负”说“记”“做”“悟”并举的教学行为变革 / 贺义廉 欧阳芬
- 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探讨 / 韩莹 孙福广
-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 顾青 吴魏
- 亦真亦幻 / 周灿美?严丽
- 对大学写作课堂活动有效性评价的分析 / 高惠宁
- 基于存在主义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龙倩彤
- 《远大前程》的课堂教学设计 / 牟英梅
- 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研究 / 张钧
- 高校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策略研究 / 李大鹏
- 高职语文的审美教育探索 / 杨利香
- 高职汉语言教学中的文学鉴赏 / 郑小娜
- 汉字书写教育应贯穿教育始终 / 王艳杰
- 情境作文 / 王宏兴 于桂言
- 基于审美体验的大学文学写作教学探索 / 王建英
- 扩大知识容量,强化情感体验 / 潘亦彤
- 论劳伦斯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 / 梁苑霞
- 论小说《1Q84》中人物的逃避与出路 / 李越
- 土地文化折射出的女性意识差异 / 孔倩云 王静
- 自然主义视角下对《棉被》的解读 / 吴婷
- 《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的孤独感解读 / 樊文琼
- 解读余华小说《兄弟》中的丑陋人性 / 于莹
-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象征意象解读 / 吴林 潘不寒
- 凸显与消解 / 董家丽
- 论《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的探索之路 / 冯建瑞
- 《德伯家的苔丝》叙事空间分析 / 刘芳
- 莫言《红高粱》的语言艺术特色分析 / 左文燕
- 略论《伤逝》的讽刺艺术 / 孙艺铭
- 《孔雀东南飞》婆媳形象的深度解析 / 陈正刚
- 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 艳春
- 空间理论观照下的梅尔维尔小说《比利·巴德》解读 / 杨晓君
- 伍尔芙《邱园记事》中的语言风格研究 / 谭杰
- 清初文人余怀诗词艺术特色探究 / 张晓娟?邢江平
- 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象征元素的生态解读 / 解学林
- 《古书句读释例》辨证 / 尹绪彪
- 诗化的江南古典园林文学 / 张晓辉
- 说“荇菜” / 赵祎缺
- 对惠特曼作品《草叶集》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 张丹
- 网络语言对青少年语言使用影响的研究 / 陈琳
- 构式语法理论下对流行语“今天你X了吗?”的解读 / 陈岩春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李陆萍
- 《红楼梦》“冷香丸”中的语言密码 / 郭孔生
- 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模糊语言的语用分析 / 翁向华
- 现代汉语存现句中“着”与“了”的使用考察分析 / 何大吉
- 概述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研究 / 李慎柱
- 论言语交际误解的语用学分析研究 / 贾萍
- 浅议文学作品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容琴
- 文化图式下文学作品语言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 梁艳红
- 英语写作中的汉语正迁移功能探微 / 张晓梅
- 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下汉语中的标识语翻译研究 / 张莲
- 语言中的文化基因及其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郭宪春?李侠
-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语言风格分析 / 王禄芳
- 语言教学方法策略研究 / 雍瑾
-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 刘娟?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