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19644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19644
论小说《1Q84》中人物的逃避与出路
◇ 李越
摘要: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反映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失去精神依托的人们对于“爱”与“沟通”的渴望。本文旨在运用上世纪四十年代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来解读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通过分析逃避自由的三种途径,指出小说中人物深陷自由困境的原因,由此揭示出追求真正的积极自由的途径,即:只有通过“爱”达到与他人畅快的“沟通”,经过自身积极的思考,重新发现自我,才能消除消极自由带给人的孤独感和无权力感,真正摆脱外在权威的控制,打开自由之门。
关键字:小说创作 逃避自由 爱 沟通
一、小说《1Q84》中的自由困境
在当今文坛,村上春树的地位可谓独树一帜,村上作品的主人公,常被卷入一段冒险经历当中,通过一系列的冒险旅程,从人世间的羁绊、习俗、常识中摆脱出来,达到完全的自由,最后重新发现自我。2009年,村上出版了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崩溃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Q84》,再一次将现代社会中关于自由与孤独的命题展示在读者面前。弗洛姆的“逃离自由”的理论,正是村上要引发读者思考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最好的注释。弗洛姆指出“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与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项不能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就变成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便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可以解脱不安之感,虽然这种屈服或关系会剥夺了他的自由。”
二、《1Q84》中主人公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现代人的自由困境,弗洛姆指出了逃避自由的三种途径,即顺势与随俗、极权主义、攻击与破坏。这些逃避机制,我们也都可以在《1Q84》当中找到。弗洛姆将这种逃避自由的途径称为“机械趋同”,指的是个人放弃了他独有的个性,采取和周围人一致的方式,使自己不再感到孤独和焦虑。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
《1Q84》中天吾的父亲,就是通过机械趋同来逃避自由的典型代表。摆脱了制度与土地束缚的天吾父亲,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思想也仍然深受旧制度的影响。可以说,天吾父亲获得了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他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充满危机的生活与沉重的责任,于是当朋友介绍他进入NHK工作以后,他要立刻逃入新的束缚当中。文章中这样写道:他工作起来十分尽心尽责。……先是干了一年计件支付工资,没有身份保障的委托收款员,由于业绩优秀、工作态度认真,便被录用为正式收款员。这从NHK的惯例来看是破格的提拔。……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幸运了。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图腾柱的最底端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入NHK工作,天吾父亲感觉与外界的差别消失了,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现实中的不安和无能好像没有了,但是在获得了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同时,也消解了他作为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他成为了一个麻木不仁、机械趋同的人,日复一日地奔走在公司设定好的收款路线上。被录用为NHK正式职员之前,父亲虽然感到孤独和不安,但是谈到自己经历的时候,他“父亲很善于讲这样的故事……细节栩栩如生,叙述富有色彩……如果人生可以用逸事和奇遇的多彩程度来计量,他的人生也许称得上相当丰富。”而成为NHK正式职员以后,“不知为何,父亲的故事就陡然失去了色彩和现实感。”
这种逃避现实的心理机构,可以说是大多数正常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行为导致了一种结果,那就是将外界加诸的思想、感觉、希望、乃至于感官的感觉,主观上错认为是自己的,但其实不过是反映了别人对他的期望。这种丧失自我,和由一个虚伪的自我来取代真实的我的现象,使个人被迫要显得和别人一样,想要不断地靠着得到别人的赞许来寻求自己。因此,在天吾父亲已经退休离职,患上老年痴呆症以后,潜意识当中仍然不断地期望别人认同自己,他的灵魂仍然执着的、机械式的继续着收费员的工作。小说第三卷分别出现了NHK收费员在“青豆”“深绘里”“牛河”门前催缴收视费的场景。他强词夺理、咄咄逼人,机械式的说教表面上在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并非是其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而只不过是承袭着NHK,这一公共舆论权威的代表的意见。
小说中“青豆”的好友“大冢环”先是成为受害者,接着自愿踏入了不幸婚姻生活,受到了不间断的家庭暴力。她写给青豆的信如下:“我无论如何难以逃出这个地域,(略)我陷入了无力。我自愿地进入其中,自己锁上门并把钥匙远远地抛开。(略)最深刻的问题不在于丈夫也不在于婚姻生活,而在于我自己心中。我所受到的所有痛苦都是我应该承受的,怨不得任何人”。尽管大冢环家庭生活富裕,可是从小就被父母所忽视,在孤独中长大。同青豆一样,大冢环过早地失去了家庭这一原始关联,自由给予她的只是迷茫、自卑、无能及无意义的感觉。尽管在表面看来,她视野开阔、聪明、博学、乐于助人,口齿伶俐。但是,“就男女关系而言,环真是天生的受害者。”正如大冢环自己所说,她并非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她所受到的伤害常常是自己主动接受的。大冢环的身体里也有“小小人”的因子,这种内在的因子驱使她感到自卑、无能及无意义,使她自己软弱而不愿去主宰一切,期望能够消除自由的负担,期望委诸外力,不断地屈服于他人,因而“一次又一次地卷入麻烦,遭到背叛受到伤害,最终遭到抛弃。”甚至在青豆阻止她走入不幸的婚姻时,她歇斯底里地不听劝告,甚至不惜大吵一架。在意识上受害者会比加害者更为自责的强烈地自我谴责,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彻底腐蚀了她,但是面对想要制裁施暴者的青豆,她只是说“事到如今报警也没有用,我自己也有责任。……看来我只能把这件事忘掉”。环对自己的孤立无法忍受,最后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尽管“精神上都伤痕累累”却“自己锁上门并把钥匙远远地抛开”,任由内心深处的“小小人”搭建禁锢自己身心。
靠自己力量长大后的青豆,朋友很少,只有在同一个垒球队的大冢环曾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在环被人强暴后,青豆将该男子的公寓内部砸得粉碎。表面上看来,青豆是一个主持正义的复仇使者,小说的叙述似乎也给她的行为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但是,“大多数的破坏现象,是不被人们视为破坏的,相反地,人们用各种方法,使这些破坏行为合理化”。从孩提时代开始,青豆就长期受到压抑,孤独、焦虑的折磨一直伴随着她,十岁时的天吾曾经让她感到了爱的力量,长大后与大冢环的交往也曾缓解了她的孤独感。但是大冢环的离去,使她失去了救命稻草,她迫切地需要一种途径去发泄和释放,来逃避自己孤立、无权力的感觉,求生的冲动受阻越大,想要破坏的行动就越强。因而她在毁坏强暴大冢环的男子的公寓时,将房间里的东西破坏得无一遗漏,甚至连牙膏、剃须膏、铅笔都没有放过。可以说,青豆正是用这种方式在发泄自己的愤懑,试图挣脱自己的无权力和孤立的感觉。在小说卷二的结尾处,本该是天吾父亲的病床上,却躺着一只透明的“空气蛹”,三十岁的青豆回到十岁,安眠于“空气蛹”当中。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情节的设置,将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连接在一起。可以说,他们都是深陷于自由困境中的被损毁的孤独的灵魂。
三、克服孤独的唯一方法:实现积极的自由
《1Q84》当中的主人公们,无法克服自身的这种束缚,他们始终处于孤独与彷徨之中,难以在标榜自由民主的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青豆”们曾经逃出了这样那样的外在束缚,但其思想仍未得到完全的解放,缺乏独立思考,自主行为的能力,“自由”的一无所有。在“小小人”的推动下,他们放弃自由的天性,放弃实现自由的权利,逃入 “精神牢笼”之中。
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打破一切束缚和枷锁,而是一个“争取自由,摆脱束缚——陷入孤独、焦虑——走向服从,重新处于不自由境地”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弗洛姆把这种自由看作是“消极自由”。只有对自由的需求和对人类交往的需求同时得到满足,人才能获得自己“与世界、与他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积极的自由。而“爱,是此种自发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小说的结尾也写道,“青豆”与“天吾”终于相见,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之下,他们摆脱了《1Q84》的世界。对于“青豆”来说,对“天吾”的爱,是她克服孤独,解除焦虑,从而不再陷入追求自由的循环往复的矛盾过程。村上希望通过“爱”达到与他人畅快的“沟通”,从而消除消极自由带给人的孤独感和无权力感。但是,对于《1Q84》所反映的这种自发努力,显得非常单薄无力。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是村上小说的一贯特征。而这也正反映出小说的主题所在,即只有经过自身积极的思考,才能真正摆脱外在权威的控制,打开自由之门,实现积极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村上春树《1Q84》(BOOK 1)第8章、第13章[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2]杜晓丽.村上春树对日本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J].语文建设,2013(06).
[3]郭华.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异质空间” [J].语文建设,2014(20).
[4]森达也.相对化的善恶. 村上春树1Q85纵横谈[M].侯为,魏大海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5]张琨.析川端康成在《古都》中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留恋与迷惘 [J].语文建设,2013(08).
[6]余虹.川端康成《花未眠》的审美解读[J].语文建设,2009(03).
[7]弗洛姆.逃避自由.第4章[M].陈明学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8]王荣生.日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取向比较及讨论[J].语文建设,200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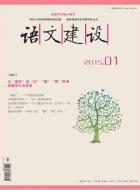
- 从“减负”说“记”“做”“悟”并举的教学行为变革 / 贺义廉 欧阳芬
- 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探讨 / 韩莹 孙福广
-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 顾青 吴魏
- 亦真亦幻 / 周灿美?严丽
- 对大学写作课堂活动有效性评价的分析 / 高惠宁
- 基于存在主义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龙倩彤
- 《远大前程》的课堂教学设计 / 牟英梅
- 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研究 / 张钧
- 高校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策略研究 / 李大鹏
- 高职语文的审美教育探索 / 杨利香
- 高职汉语言教学中的文学鉴赏 / 郑小娜
- 汉字书写教育应贯穿教育始终 / 王艳杰
- 情境作文 / 王宏兴 于桂言
- 基于审美体验的大学文学写作教学探索 / 王建英
- 扩大知识容量,强化情感体验 / 潘亦彤
- 论劳伦斯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 / 梁苑霞
- 论小说《1Q84》中人物的逃避与出路 / 李越
- 土地文化折射出的女性意识差异 / 孔倩云 王静
- 自然主义视角下对《棉被》的解读 / 吴婷
- 《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的孤独感解读 / 樊文琼
- 解读余华小说《兄弟》中的丑陋人性 / 于莹
-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象征意象解读 / 吴林 潘不寒
- 凸显与消解 / 董家丽
- 论《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的探索之路 / 冯建瑞
- 《德伯家的苔丝》叙事空间分析 / 刘芳
- 莫言《红高粱》的语言艺术特色分析 / 左文燕
- 略论《伤逝》的讽刺艺术 / 孙艺铭
- 《孔雀东南飞》婆媳形象的深度解析 / 陈正刚
- 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 艳春
- 空间理论观照下的梅尔维尔小说《比利·巴德》解读 / 杨晓君
- 伍尔芙《邱园记事》中的语言风格研究 / 谭杰
- 清初文人余怀诗词艺术特色探究 / 张晓娟?邢江平
- 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象征元素的生态解读 / 解学林
- 《古书句读释例》辨证 / 尹绪彪
- 诗化的江南古典园林文学 / 张晓辉
- 说“荇菜” / 赵祎缺
- 对惠特曼作品《草叶集》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 张丹
- 网络语言对青少年语言使用影响的研究 / 陈琳
- 构式语法理论下对流行语“今天你X了吗?”的解读 / 陈岩春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李陆萍
- 《红楼梦》“冷香丸”中的语言密码 / 郭孔生
- 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模糊语言的语用分析 / 翁向华
- 现代汉语存现句中“着”与“了”的使用考察分析 / 何大吉
- 概述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研究 / 李慎柱
- 论言语交际误解的语用学分析研究 / 贾萍
- 浅议文学作品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容琴
- 文化图式下文学作品语言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 梁艳红
- 英语写作中的汉语正迁移功能探微 / 张晓梅
- 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下汉语中的标识语翻译研究 / 张莲
- 语言中的文化基因及其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郭宪春?李侠
-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语言风格分析 / 王禄芳
- 语言教学方法策略研究 / 雍瑾
-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 刘娟?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