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20816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
ID: 420816
创伤理论视角下《手》与《杀死一只反舌鸟》的对比分析
◇ 张佳卉
摘要:舍伍德·安德森和哈珀·李虽然是美国文学史上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但在拓展美国文学本土化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创作中他们都塑造了令人唏嘘不已的“畸人”形象,从深层次探讨了人类心理问题。本文主要从创伤理论视角对他们的代表作《手》和《杀死一只反舌鸟》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关键词:创伤理论 《手》 《杀死一只反舌鸟》
引言
在美国文学史上,舍伍德·安德森虽然称不上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但他对美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带来了巨大影响。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很难进行传统化分类,因为其作品中既有敏锐观察的现实主义色彩、冷峻客观的自然主义风格,又有追求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调,更有勾勒简练的印象主义之风。他的创作几乎影响了后世的整个一代作家,福克纳将他称为“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父亲”,强调他“代表了美国文学的传统,我们的子孙将永远继承这个传统”。舍伍德·安德森虽然也创作了《温迪·麦克弗逊的儿子》等长篇小说,但其主要成就体现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以短篇小说集《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镇》为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集中,舍伍德·安德森借助乔治·威拉德这个线索性人物塑造了一个个令人称奇的“畸人”形象,其中开篇之作《手》就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内心经历深度创伤的“畸人”——飞翼比德尔鲍姆,从而洞察了人类微妙的精神世界变化。
无独有偶,深受舍伍德·安德森影响的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在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中也塑造了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畸人”形象——布雷德利。该小说在发表后,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1961年获普利策文学奖。哈珀·李也因她对文学的杰出贡献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章”。布雷德利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作为一个深受心理创伤的人物,他在作品中的行为对情节的推动以及主题的表达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下面就以飞翼比德尔鲍姆和布雷德利这两个“畸人”为关注对象,从创伤理论视角,对《手》与《杀死一只反舌鸟》这两部作品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一、创伤理论概述
创伤是一个心理学术语,主要指某一外在事件或身体伤害引起的对个体内心的影响,主要是创伤性事件带来的巨大影响。而创伤性事件是指那些严重威胁安全或躯体完整性的,引起个体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急骤的威胁性改变,引起灾难性反应的事件。在此事件影响下,心灵在无法期待和恐惧中对一个事件抵抗,先前的知识结构无法为它作好准备,而创伤性事件留下的记忆是深刻而且持久的。荣格认为,对创伤经历的正常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场景中退缩,如果退缩是不可能的,那么自我的一部分就必然退缩。那就意味着自我必须分离,分离是抵制潜在心理损伤的常用防御方式。
在《手》与《杀死一只反舌鸟》中,飞翼比德尔鲍姆和布雷德利这两个原本无比“正常”的人都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了心理重创,形成了弥足持久的创伤性体验,逐渐演变成众人都不愿接近的“畸人”。这种创伤性体验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一生都在影响着其固有的思维模式。
二、飞翼比德尔鲍姆与布雷德利的“创伤”对比
(一)创伤的形成
在《手》中,“畸人”飞翼比德尔鲍姆的形成和他的一双手是分不开的。在瓦恩斯堡镇,飞翼比德尔鲍姆是一个外观非常邋遢的怪人,可谓人见人躲,但是在田地里劳作时,他却能够引起众人的注意,因为依靠灵巧的双手他能够在一天时间内采摘140夸脱的草莓,这是一个常人完不成的任务。不过这 “迅捷”的双手没有为其带来好的声誉,而是使其更加怪诞,只因为在平时他总是把这双手藏匿于众人“眼光”之外。飞翼比德尔鲍姆并非他的真名,他真名叫阿道夫·迈耶斯,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城里的教师。作为一个教师,阿道夫·迈耶斯是非常优秀的,特别是那一双抚摸孩子肩膀和摩弄孩子头发的手,好像充满了魔力一样为孩子们编织着多彩的梦想。通过这双手,阿道夫·迈耶斯不仅表达了对孩子的纯真呵护,而且帮助孩子们去除了心灵的怀疑与眩惑。孩子们就这样在教师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他们也不时做着一些五彩斑斓的美梦。有一天一个迷恋阿道夫·迈耶斯的愚钝学生把一个不可言说的梦境当作事实讲了出来,引来了全城的震惊与愤怒。随之一群人对阿道夫·迈耶斯进行暴打驱逐,甚至要活生生地吊死他。天生温和懦弱的阿道夫·迈耶斯就这样在不明白为何被打、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带着遗憾和恐惧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对阿道夫·迈耶斯来说,这就是一个痛彻心扉的创伤性体验。
与飞翼·比德尔鲍姆的“创伤”相比,布雷德利“创伤”的形成没有那么突然,但是持续的时间却相当长,这足以让“创伤”的影响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少年布雷德利最多是一个叛逆孩子,就像美国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轻狂无知,与一些社会小混混搅合在一起,在一次酒醉后创下祸端并被送到未成年人法庭。布雷德利的父亲出于面子问题,不愿孩子被起诉,保证以后一定严加管教孩子。布雷德利就这样被父亲带回了家中,此后便过上了长达二十几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因为布雷德利家从那之后天天紧闭大门,不与外界来往。即使在父亲死后布雷德利也没有“解禁复出”,而是由哥哥继续看管。整日被“囚禁”在没有阳光的小屋中,正值成长的布雷德利内心一定是遭受了重击,否则不可能如此“逆来顺受”,从善良黑人卡波妮对布雷德利父亲的评价“一个上帝造出的最恶毒的人”就可以猜测他对孩子做了什么事情。常年不露面的布雷德利不仅内心受到了创伤,而且常常受到街坊邻居的无端非议,从而深化了其“畸人”的形象。
(二)创伤的表现
阿道夫·迈耶斯出逃瓦恩斯堡镇只是他“新生活”的开始,也可以说是灾难性生活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与原来的生活以及环境划清界限,首先他把自己的名字换为“比德尔鲍姆”,也许是他觉得“阿道夫·迈耶斯”这个名字有不祥之兆,给自己带来了厄运,但是他换的新名字“比德尔鲍姆”却显得过于随意。这个名字是他受到惊吓后经过一个货运站时在货箱上看到的,对于一个有文化内涵修养的教师来说,这样更换名字未免太过草率,但却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降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投奔到瓦恩斯堡镇的姑妈之后,他竟然大病一场,而且长达一年,足见“受伤”之深重。其实,他的“伤”不只是身体,而更是内心。病愈之后,飞翼比德尔鲍姆陷入了更为深刻的阴影之中,特别是有意识地把双手隐藏起来,因为他觉得除了名字以外,这双手也是其厄运的罪魁祸首。当别人一提到“手”这个字眼,他就像触电一样地藏起双手,并回忆起宾夕法尼亚的一幕幕情形:学生父亲对“手”的不停追问、酒馆老板之言“不许你伸出手来碰别人”等。读者不仅要问,为什么在采摘草莓时,比德尔鲍姆的双手那么灵巧呢?其实,那是受伤更为严重的表现,他是在发泄心中的抑郁情绪,通过“双手”不停的“工作”,似乎这样就能找到想要的答案。他就这样居住在瓦恩斯堡镇的边缘地带,依靠打零工过着一种衣不暖、食不饱的生活。
阿道夫·迈耶斯的“新生活”是经历了创伤之后的一种主动性选择,而《杀死一只反舌鸟》中布雷德利的“新生活”是经历创伤之后的被动接受。作为一个求知欲和好奇心正强的花季少年,布雷德利内心对外面的世界是无比渴望的,但由于父亲的“特殊手段”,他只能湮灭在众人与社会的视线之外。这种“囚禁”对他身心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使他在逐渐失去一些社会人的“特性”沦为“畸人”,与此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理出现了问题。他不仅无法和社会上的同龄人进行正常沟通,就连与自己的家人也难以交流,于是就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一些无谓的治疗。从内心来说,布雷德利没有完全失去常人与外界交流的心理本性,但他只能通过“在门口的树洞放东西”的形式与外界的小伙伴进行难得的交流。由于被“剥夺”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布雷德利只能依靠不灭的童真本性与社会进行简单可笑但却可怜可爱的“对话”,这就是创伤对其带来的伤害,因此他的创伤主要源于父母的武断“囚禁”,而非自身个性所致。
结语
总的来说,尽管飞翼比德尔鲍姆和布雷德利都因为一次特殊事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但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飞翼比德尔鲍姆选择了一种主动逃避,而布雷德利过着一种被动的“囚禁”生活。不过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都没有失去人类最本真的一面,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飞翼比德尔鲍姆除了面对过去的方向彷徨思索之外,也会对乔治·威拉德进行倾诉,而布雷德利除了与孩子进行幼稚可爱的交流之外,他勇敢及时地出手惩治恶人。因此,创伤的确可以给人类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活创伤,但人类灵魂深处的本性是永存的。
参考文献
[1]张强.浓缩人生的一瞬间:舍伍德·安德森及其短篇小说艺术[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罗益民.岸与圈:一个天文学的隐喻——沈从文的《边城》与安德森的《林中之死》[J].文学研究,2005(03).
[3]李莉.《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美国工业时代下小镇生活的一面镜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08(5):58-60.
[4]穆秀丽.美国文学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探邃[J].语文建设,2014(29).
[5]何劲虹. 孤独的世界——评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及其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
[6]姚丽梅.缺失的母爱——《杀死一只反舌鸟》中缺失的母爱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研[J].成功(教育版),2012(01).
[7]叶英.不体面的种族歧视与得体的艺术表现——析《杀死一只知更鸟》[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105-112.
[8]王颖慧.歧视还是接受:析《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文化冲突[J].语文学刊,2011(08):4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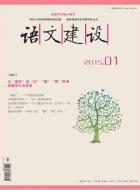
- 从“减负”说“记”“做”“悟”并举的教学行为变革 / 贺义廉 欧阳芬
- 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探讨 / 韩莹 孙福广
-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 顾青 吴魏
- 亦真亦幻 / 周灿美?严丽
- 对大学写作课堂活动有效性评价的分析 / 高惠宁
- 基于存在主义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 龙倩彤
- 《远大前程》的课堂教学设计 / 牟英梅
- 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研究 / 张钧
- 高校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策略研究 / 李大鹏
- 高职语文的审美教育探索 / 杨利香
- 高职汉语言教学中的文学鉴赏 / 郑小娜
- 汉字书写教育应贯穿教育始终 / 王艳杰
- 情境作文 / 王宏兴 于桂言
- 基于审美体验的大学文学写作教学探索 / 王建英
- 扩大知识容量,强化情感体验 / 潘亦彤
- 论劳伦斯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 / 梁苑霞
- 论小说《1Q84》中人物的逃避与出路 / 李越
- 土地文化折射出的女性意识差异 / 孔倩云 王静
- 自然主义视角下对《棉被》的解读 / 吴婷
- 《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的孤独感解读 / 樊文琼
- 解读余华小说《兄弟》中的丑陋人性 / 于莹
-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象征意象解读 / 吴林 潘不寒
- 凸显与消解 / 董家丽
- 论《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的探索之路 / 冯建瑞
- 《德伯家的苔丝》叙事空间分析 / 刘芳
- 莫言《红高粱》的语言艺术特色分析 / 左文燕
- 略论《伤逝》的讽刺艺术 / 孙艺铭
- 《孔雀东南飞》婆媳形象的深度解析 / 陈正刚
- 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 艳春
- 空间理论观照下的梅尔维尔小说《比利·巴德》解读 / 杨晓君
- 伍尔芙《邱园记事》中的语言风格研究 / 谭杰
- 清初文人余怀诗词艺术特色探究 / 张晓娟?邢江平
- 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象征元素的生态解读 / 解学林
- 《古书句读释例》辨证 / 尹绪彪
- 诗化的江南古典园林文学 / 张晓辉
- 说“荇菜” / 赵祎缺
- 对惠特曼作品《草叶集》中隐喻的认知研究 / 张丹
- 网络语言对青少年语言使用影响的研究 / 陈琳
- 构式语法理论下对流行语“今天你X了吗?”的解读 / 陈岩春
- 从英语语言学视角下看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的得失 / 李陆萍
- 《红楼梦》“冷香丸”中的语言密码 / 郭孔生
- 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模糊语言的语用分析 / 翁向华
- 现代汉语存现句中“着”与“了”的使用考察分析 / 何大吉
- 概述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研究 / 李慎柱
- 论言语交际误解的语用学分析研究 / 贾萍
- 浅议文学作品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容琴
- 文化图式下文学作品语言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 梁艳红
- 英语写作中的汉语正迁移功能探微 / 张晓梅
- 语用标记等效原则下汉语中的标识语翻译研究 / 张莲
- 语言中的文化基因及其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郭宪春?李侠
-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语言风格分析 / 王禄芳
- 语言教学方法策略研究 / 雍瑾
-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 刘娟?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