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2年第5期
ID: 139798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2年第5期
ID: 139798
论《白鹿原》关于革命的艺术反思
◇ 吴茜
陈忠实在其代表作《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显然,作者是以“民族秘史”的标准来构架作品的,而《白鹿原》这部反映上世纪五十年间渭北高原风云变幻的史诗性著作也不负所望地达到了作者的要求。《白鹿原》自出版以来一直都是主流评论家研究和批评的热点,其中讨论其“民族秘史”意义的也不少。但以往的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免将小说中隐藏的“革命叙事”作为研究重点,或专论“文化”、“情感”而将革命作为背景,或仅从一两个革命人物的角度泛泛而谈,笔者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斗争史,“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白鹿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部“秘史”数十万字的宏大篇幅是围绕着革命的发展而铺开的,“革命秘史”是“民族秘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宏观的、系统的分析阐释很有必要。
中国当代的革命叙事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但这些作品普遍存在着在政治功利的驱动下将革命神圣化、理想化的现象。以《白鹿原》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主题和单一叙事,而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广,打破了单一的革命叙事而置入了作家的文化审视,因而展现的革命图景不仅更加真实动人,也因文化视野的投现而令人深思。《白鹿原》这部“民族秘史”中的革命叙事不论是在人物和情节的塑造上,还是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都具有反传统、复杂化、多元化的特性,其中流露出的对革命的反思更是难能可贵。革命和文化在这部巨著中相激相荡、互为映现,革命摧古拉朽地冲击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静观默察地审视着革命,革命和文化的这种互为映现的关系使《白鹿原》在切入“民族秘史”的同时,完成了对革命的艺术反思。对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革命来说,无论对革命的反思还是艺术地表现对革命的反思,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而《白鹿原》中的革命叙事正因为浸透了文化的底蕴和人性的光辉才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下文将从革命与传统文化、革命与人两方面入手,集中揭示这部作品中表现的“革命反思”,探求“秘史”下的别一重意味。
一.革命与传统文化
白鹿村是“以儒学观念为主导,以封建宗法制为主体”的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在鹿兆鹏等革命者眼中被视为“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原上的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儒家传统、三纲五常为基础形成,白嘉轩既是封建家族族长,也是乡约族规的捍卫者。作者不遗余力地细致描写他翻修祠堂、修补乡约、率众祈雨、惩戒族人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极力渲染宗族仪式的神圣庄严与族长的恪尽职守,目的就是将族长白嘉轩的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与革命中良莠不齐、走马灯般的各类党政机关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以“铁打的族长,流水的地方官”之感。而宗族仪式的原始和繁琐也增强了这部民间“秘史”的真实性。每当白鹿原经历了一次天灾或人祸,白嘉轩总是挺身而出,将族人聚集到祠堂中来,仿佛是要用强大的宗族力量将族人的心凝聚在一起。此举虽然不一定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对安抚民众、稳定人心却有着莫大的作用。不论是残暴旧军阀杨排长、人面兽心的国民党田福贤还是莽撞的农协头领鹿黑娃,他们出于好意或恶意的举措只给白鹿原带来了灾难和伤害,而宗族的力量却能让人们得到片刻心灵的安宁。白嘉轩对原上的斗争并不感兴趣,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观的,他都持褒扬态度,即使对改过自新、回归正统的土匪鹿黑娃也不例外;反之则一律贬斥。他最喜爱的女儿白灵投身国民革命,想用先进的革命理念“冲一冲他那封建脑瓜子”,他在劝导无效后也果断将白灵逐出家门。白灵遇害那晚他坐立不安,冒险在黑天雪地里跑了半夜找朱先生解梦,可见他并非对女儿无情。但是,根植于他脑海中的传统思想使他不能接受女儿参加革命的事实,他狠心逐出白灵的举动向族人宣告了他对革命的态度。
然而,祠堂只能暂时掩盖星星之火却不能阻挡革命的燎原之势,当驻扎在原上的保安团用大征丁大征捐的方式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时,白嘉轩看到原上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终于也发出了“无力回天”的悲叹。他将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宣布“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这实际上是白嘉轩在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困境下无奈地放弃了他捍卫一生的宗族权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道:“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白嘉轩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一生信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古训,在处理家族事务上一丝不苟、事无巨细,以严格的族规来要求自己和族人。虽然乡约的内容在今天看来有诸多封建古旧之处,但它作为一项约束族人行为的道德规范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当白嘉轩看到革命的洪流冲散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宗族纽带,族规和乡约再也无法约束族人时,内心的悲凉和无奈是不言而喻的。
封建宗族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则是构建封建宗族的精神纽带。所以,固若金汤的封建家族在革命的催生下分崩离析也就预兆了儒家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如果说白鹿原上美丽神秘的“白鹿精魂”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那么博学多才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关中大儒朱先生就是白鹿精神的化身。白嘉轩是一个严格执行族规乡约的“凡人”,而制定族规乡约的朱先生则是“圣人”。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朱先生这一人物,对其乐善好施、安贫乐道的品质和学富五车却不问政事的清高大加赞赏,甚至将其镀上了一层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神圣色彩。无论是人品道德、胆识谋略还是运筹帷幄,他都堪称完美。但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完人”却与革命无缘甚至屡屡对立,这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朱先生将白鹿原喻为国民党、共产党、土匪三家相争的“鏊子”,并说出了“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不过是‘公婆之争’”的惊人之语。他能笃定而准确地判断“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
这些看似大逆不道、荒诞不经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能治国兴邦的领袖人物,“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也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论哪方得到天下都是苍生百姓之幸。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却复杂残酷,尤其是这样伟大的民族理想、社会理想,即使是在革命胜利后也未必能实现。当革命的激情减退后,革命者们能否坚持以执着的信念为神圣理想而奋斗?朱先生目睹了这鸡飞狗跳的世道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很自然的对不甚熟悉的共产主义也产生了几分疑虑。革命所固有的血腥、暴力与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宽容、中庸、隐忍等成分是相悖的。所以朱先生及其追随者白嘉轩对革命始终抱有一种由不信任而导致的排斥态度,他们只能从延续了上千年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和立身纲纪中找到精神慰藉。今天的人们已经明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已经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某个人而是由整个历史决定的。但我们也必须理性而清醒的认识到,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企图通过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白鹿原》中流露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和缅怀并没有任何否定社会革命之意,任何人都无法割裂自己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白嘉轩、朱先生等人身上残余的“封建思想”,反而应该尊重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依附,并呼唤受到革命冲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
二.革命与人
革命离不开“人”,如果说革命的主潮是“正史”,那革命中的每一个个体就构成了这部“秘史”。在那个形势复杂、斗争残酷的特殊年代,无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工具,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则大相径庭。有的人并没有相应的革命觉悟,甚至不能算是革命者,但其行为实际上已经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有的人热血满怀地投身革命,却在命运的捉弄下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也有人虽然身处革命阵营,其所作所为却是反革命的。《白鹿原》中的革命人物不再是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的理想英雄,而是一个个真实平凡、有血有肉的“人”。
鹿兆谦(黑娃)是革命者中最不寻常的一个,他从闹农协开始踏上革命的道路,参加过共产党武装部队,失败后沦落为土匪,后招安进了国民党保安团,在关键时刻起义投诚,促成了滋水县的解放,而最终却被同党白孝文诬陷冤杀。他是全书唯一一个在国、共、匪三个利益集团都游刃有余的人,他几经风浪都化险为夷,却在革命胜利后死于同伙的黑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黑娃与鹿兆鹏、鹿兆海之类的革命党不同,他并没有固定的革命信仰和政治倾向;他更与白孝文之类的投机分子也不同,他重义轻利、侠肝义胆。他虽然辗转于不同的阵营,但读者却不认为他两面三刀,反而多对他持同情态度,就是因为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从不负人”时顶天立地的豪气。黑娃是一个天生的反抗者,他从小就畏惧白嘉轩“挺得太直”的腰,后又因为娶了田小娥而为祠堂所不容,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破坏力,是各个阶层公认的“冷家伙”。可以说,他既有强烈的革命需求也有较高的革命能力,他的反抗和暴烈使他天然地靠拢革命。但遗憾的是他对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分不清国共革命性质的差别,他的革命举动更多的是出于兄弟之义而缺乏理性的思考。在朱先生和传统文化的熏染下,黑娃开始皈依仁学、“学为好人”,并出人意料地成为朱先生最后也是最好的弟子。被誉为“中国式人道主义者”的汪曾祺曾援用古训“仁者为人”为古代的人道主义,“仁”即凝聚了儒家文化精华的仁爱和仁义。对于黑娃而言,不论是他的革命还是他的仁义,最后都使他成为革命的牺牲品。黑娃的悲剧就是对革命的人性质疑和人道追问。
另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来自白灵。白灵是《白鹿原》中除朱先生外唯一一个化身“白鹿精魂”的人,也是作者最为偏爱的女性角色。从她出生时啼叫的百灵鸟到她被害时出现在亲人梦中的白鹿,从她读书写字的潇洒聪慧到投身革命的坚定果敢,作者不吝溢美之词,在白灵身上寄托了白鹿原上人们追求的种种美好品质:善良、美丽、纯洁、坚韧、自尊自信等等。但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独一无二奇女子却屈死于根据地清党肃反的屠杀中。自小说出版以来,白灵的悲剧让无数读者不解甚至不满,她这只“百灵”理应奔向更宽广光明的未来而不是掉入自我倾轧的黑洞。其实,作者对白灵命运的安排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即白鹿原上一位名叫张景文的革命女性。当作者读到共产党员张景文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而活埋时,他顿时感到一种“捶拳吁叹的失控”,作者的痛心遗憾比读者读到白灵被害时的心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白灵这个白鹿原上新女性的形象也就应运而生了。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作者将本不该发生的悲剧艺术地再现了出来,是对革命中内部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与诘问;而将悲剧的命运加在了白灵身上,无疑又加强了表达效果。在白灵心中,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奶奶口中那只神奇的“白鹿”,其实品行高洁的白灵也是作者心中的“白鹿”。当这只象征着美好人性的“白鹿”掉进革命的“黑洞”时,读者不得不对在革命中破碎的人性美而深思。
此外,《白鹿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革命的真实态度。白鹿村是中国大地上最普通、最典型的一个村子,绝大部分民众对革命既不了解也不关注,他们宁可安分守己地困苦度日,也不愿“掺和”到去旧迎新革命中去。当军阀残部疯狂征粮,农民不堪重负时,他们也只是通过传鸡毛信、拒绝交农的举动来反抗,并没有想过彻底推翻一个政权。其中鹿三是这次交农事件的中流砥柱,其不畏强权、敢于献身的勇气是白嘉轩都自叹不如的。鹿三和大多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一样有革命需求,而且他在实际上已经充当了革命者的角色,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坚持反对革命。他对主人白嘉轩忠心耿耿、感恩戴德,因为他并不认为以“仁义”待人持家的白嘉轩是压迫者。反而在听说儿子鹿黑娃闹农协、砸乡约碑文后暴跳如雷,甚至要挥刀相向。虽然农协在今天看来存在着偏激、不成熟、把问题简单化等诸多问题,但它毕竟是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与白嘉轩所在的地主阶级有本质区别。鹿三身上体现了白鹿原上绝大部分普通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不了解并本能地排斥“革命”。更有甚者如白嘉轩,在大势所趋、原上“暗里进共产党的人多着哩”之时依然执迷不悟,不理解亲戚的革命行为。作者真实地将原上百姓对革命的态度展现了出来,既赞扬了共产党员白灵、鹿兆鹏的优秀品质,亦不回避国民党军官鹿兆海渴望战胜日本收复河山的爱国之心,更从多方面表现了广大群众对革命的或畏惧、或洒脱、或不了解、或不关心的心理。这对于读者正确认识革命的启蒙作用是极有帮助的。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让革命的精神真正深入人心依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话题。作家并不以为革命不合理,但是当革命已经成为过去,而且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时,也许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反思革命,能够带给人民更多的启示。
文学永远是一个向历史和时代敞开的话语空间,而如何书写革命历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文学话题。[4]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家可以用新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方法来描写在不同环境下革命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包括对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反思、对革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以及对革命理想的坚持等等。白鹿原上的革命既与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革命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更融入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人性的闪耀光辉。它必然有落后、保守、不彻底的一面,但这也未尝不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写照。《白鹿原》既表达了对儒家传统的推崇和缅怀,也直言不讳地描写了革命与“人”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流露出的反思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作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艺术的手段抒写革命给中国带来的震动,并融入文化、家族、人性、情感等多重色彩,使这部“民族秘史”有了更深层的意味。《白鹿原》中体现的对革命历史的理性思考、对革命经验的辩证吸收和对历史问题的全面反思对广大读者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吴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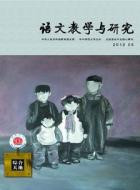
- 无法被规训的另一面 / 王海燕
- 研究性学习的三个层次 / 李涛
- 适性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叶萍
- 语文教学设计的制定原则 / 徐以才
- 信息技术给语文课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 戴新翠
- 我们的会场 / 范小青
- 语文教学要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 王军
- 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 张略
- 初中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 陈芙玮
- 语文教学的诗意探寻 / 张厚萍
- 语文教学要讲究艺术性 / 刘素君
- 如何实现语文教学的返璞归真 / 王云飞
- 古诗词教学中材料解诗的几种类型 / 张林
- 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 龙莲明
- 初中生自主性阅读能力的培养 / 滕宏江
- 中学生课外阅读再思考 / 徐红梅
- 读是语文教学之本 / 周启德
- 在朗读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 洪孝添
- 作文批语与学生心理 / 胡世荣
- 提高初中生写作水平的方法 / 王道平
- 如何引导小学生写作文 / 章梅香
- 文采飞扬 妙笔为文 / 孙金兰
- 学生随笔写作的策略与实践研究 / 杨裕华
- 作文训练的四大法宝 / 苏多山
- 高中议论文教学中教的艺术 / 孙蔷华
- 论语文教师的课堂语言 / 吴小燕
- 语文教师应如何锤炼课堂教学语言 / 蔡栋
-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有效方法 / 方杰
- 珍视课堂教学中的无心插柳现象 / 任泽寿
- 开发成语资源 提高课堂效率 / 郝君
- 语文课堂教学情怀生成 / 王文芸
- 践行“四实”打造高效语文课堂 / 朱亚红
- 如何组织课堂教学 / 杨丽
- 初中语文教学如何加强文学性 / 高群
- 体态语是语文课堂中师生沟通的桥梁 / 陈晓霞
- 对语文课堂教学优质高效的反思 / 任波
- 小学写字教学摭谈 / 杨东
- 自主学习课堂模式初探 / 冯卫东
- 巧用信息技术优化语文教学 / 宋忠东
- 《项羽之死》中的六个“三” / 王敏
- 让学生感受文言之美 / 王霭秀
-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的艺术手法 / 张分化
- 语文教学评价的艺术 / 王优
- 语文教材插图中的信息 / 向磊 哑禅
- 语文教学中学生思想的培养 / 兰海燕
- 阅读教学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 李忠桥
- 有效性阅读教学探究 / 陈波
- 注重文章的内在美 / 余慧敏
- 品读《南州六月荔枝丹》 / 张法欣
- 试论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和谐 / 石风
- 依托文本丰富语言积累 / 谢晓艳
- 立足课堂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 曹红梅
- 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识字 / 王开美
- 突破课堂识字的关键 / 谢超
- 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会识字 / 于建华
- 论《白鹿原》关于革命的艺术反思 / 吴茜
- 浅谈韩愈诗歌的诙谐幽默 / 孔倩倩 胡文文
- 《小狗包弟》中的环境描写 / 曹碧荣
- 晏殊《浣溪沙》中的生命意蕴 / 刘有斌
- 苏轼《定风波》阅读体会 / 胡欢节
- 把微博引进作文课堂 / 沈浙瑛
- “语言—思维”写作训练单元教学设计 / 曹阳
- 入题.入格.入言 / 孟华
- 《将进酒》朗读教学课堂实录 / 郝龙
- 关于中考作文命题的探讨 / 黄英平
- 飘洒着诗意的雨 / 丁宏兵
- 古诗词鉴赏关系类题型答题技巧 / 肖立俊
- 让流行歌曲在作文中飘荡 / 鲁红军
- 2011广东高考语文实用类阅读题浅析 / 万志
- 《好嘴杨巴》教学片段与反思 / 陈霞
- “活动单导学模式”下作文的批改方法 / 洪春燕
- 《咏雪》教学设计 / 李振昌
- 个性化作文的基本特征 / 邢惠梅
- 诗歌鉴赏类题型的解题探微 / 练治华
- 在实践中反思 在反思中收获 / 杨白平
- 坐堂号脉 精通题理 / 董钰
- 对语文综合性活动有效性的几点思考 / 李雪飞
- 如何写就中考作文 / 卢兴治
- 据材料写议论文三步法训练初探 / 覃东雷
- 探究集体备课的新方向 / 熊雷
- 以书为镜的魅力教师 / 李小平
- 孩子到底怎么了 / 向仕勇 朱德娥
- 教育贮满情爱 / 黄书琴
- 寿礼 / 吴生舟
- 忆师生情 如沐春风 / 叶晶晶
- 关于自我教育的基本构想 / 李后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