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47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47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真正和《中学语文教学》亲密接触,是1994年。
那年,《中学语文教学》和开明出版社等单位联合组织了中华首届“圣陶杯”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似乎此前还没有过这样高规格的论文比赛。我将早就酝酿好的一篇论文《语文课堂教学的和谐原则》寄到大赛组委会。说真的。我想不到自己会得一等奖,更想不到还名列第一。接到通知,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不仅我自己很激动,我们的校长也高兴坏了,特许我双飞前往北京。那个年代,坐过飞机的人不是很多,这让许多同事既羡慕又妒忌。
会议期间,和《中学语文教学》的几位编辑老师都认识了,陈金明老师,史有为老师,还有一位姓苗的老师,已经记不得名字了。也就是在那次颁奖会上,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程翔老师,他那时好像刚在全国课堂比赛中得了什么奖,正红得很。颁奖大会上是他代表大家发的言。他们几位还就着这个活动,开了一个成立“全国青语会”的预备会。
那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每当看到自己在人民大会堂穿着短裤的留影,尽管样子土气得掉渣,但我还是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那次活动,我见到了当时语文界三老中唯一健在的张志公先生。他当时精神已很不好,讲话已经中气不足。短短的会议中间还被服务人员扶出去休息了一次,但他呼吁大家致力于语文教学改革和研究的恳切希望给予了大家强烈的震撼,也激发了我终身献身于语文教育的决心。给我颁奖的是雷洁琼先生。她年岁已高,但精神明显比张老好。很荣幸的是,我和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先生,还有一个短暂的聊天。叶先生先问我是哪里人,听说是江苏来的,他显出不同寻常的亲切,说自己也是江苏的,苏州人。可惜后来有一次见到他,他已经记不起我了。我当然也不好冒失地认他,更不能浅薄地说出当初领奖的事。
不久,《中学语文教学》又和某个单位合作在青岛召开了全国优秀青年语文教师座谈会。江苏的代表是我和严华银。座谈会上,我发言的内容是从语言习得的特点看语文教育的科学化。也许溢美的话总是难忘,记得陈金明先生对我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叮嘱我把发言整理好寄给《中学语文教学》,寄稿时我同时又参加了中华第二届“圣陶杯”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后来文章又获得了一等奖,并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连同第四届,我在《中学语文教学》组织的“圣陶杯”论文大赛中三次获得一等奖。家乡的《盐阜大众报》以“连中三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回想起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这三次获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然不是说自己因此有了一点虚名,而是坚定了我用心于语文教学及研究的决心和信心,使我有了进行语文学科研究的自觉意识。
可以说,《中学语文教学》始终在关注着我的成长。她不仅及时推出我的成果,哪怕是一点不成熟的体会(粗略统计,先后在该刊发表论文达30篇左右),而且不断推出新的栏目,激励我们这一批人的成长,增添我们求索的动力。1998年,张蕾来函约我写一篇谈读书的文章,这正戳到了我的短处。写那篇文章我真是“羞愧”得不行。但正因此,也极大地激发了自己读一点书的决心。我觉得自己在读书方面不应安于落后,便针对自己的情况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些年来。虽然不敢说读了多少书,但始终按计划坚持在读,得益自然也很多。
后来《中学语文教学》又推出了“成长之路”栏目,并约我写稿。完成《平凡人生寻常事》一稿的过程,是我第一次系统进行教学反思的过程。回顾自己走过的语文教学之路。甘苦得失虽然并没有都写到文章中,但感受是极其强烈的,前面的路也看得更清楚,目标也更明确。去年,《中学语文教学》又开辟了“名师工作室”。兼着苏州市名师名校长班六位语文学员导师的我,正为没有合适的课题引导他们研究而犯难。在张营主编的引发之下,我们几个人多次碰头,对“选修课课堂教学的特征”这个话题,有了一些想法。凑成的一组稿反响似乎还不错。近来,张蕾主编拟策划一个“语文名家新生代”的栏目,又把栏目写作的任务交给我。尽管到现在稿子还没有通过她的法眼,但这又是一次促使我进行思考、总结和提升自己的难得的好机会,也使我感到肩头上承先启后的沉重责任。回首走过的路,登上每一个台阶,背后都有无数双手推着,而《中学语文教学》便是其中有力的一双。
也因为《中学语文教学》,我结识了许多语文圈子中的好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我在语文教学研究方面有所心得的重要因素。1999年,我去天津参加全国中语会第七届年会,一天正在房间里和几个朋友聊天。一个个子不高、但长得比较敦实的人敲门进来:“请问黄厚江老师在不在?”一问,才知道进来的是如今名气很大的李镇西。原来他看到我和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同一期上发表的文章。感到我们的许多看法有相通之处,便趁这次会议的机会想找我聊一聊。现在,在全国各地常常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对我比较熟悉的朋友。这些朋友总是说:“我们在《中学语文教学》上经常读到你的文章。”现在,和主编张蕾兄,早已成了好哥们儿。只要有机会,就往一起凑。没有机会见面,便常常电话里聊上几句,东长西短,油盐酱醋。天下大事,无所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仍是语文教学,课程改革的前景,现状中的问题,杂志的方向,栏目的设计,活动的组织等。有什么想法,坦言相陈,从不掩饰;有什么困难,尽力帮助,毫不含糊。记得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我向张蕾致谢,她说:“黄厚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哥们儿之间,说什么感谢呢。”真的让我很感动。当然,我对他们的刊物和编辑有什么意见,她对我的习作有什么不满,也都是直言指陈,毫不隐讳。本来,说《中学语文教学》是我的老师,才更为准确;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把她作为我的一个朋友,把她的关怀当做朋友的情意。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许多良师益友,使我心存感激,难以忘怀。有几家语文刊物,伴我一路走来,始终关心着我的进步。《中学语文教学》便是其中感情特别的一家。
在她30岁生日之际,权以此篇短文作为菲薄的贺仪。
(江苏省苏州中学 215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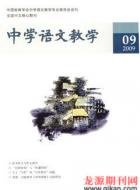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