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7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7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题解】
锦瑟,装饰华美的瑟。瑟:拨弦乐器。通常二十五弦。“琴瑟”连言,喻朋友合和融洽:“琴瑟不调”则言夫妻不和,“琴断朱弦”比喻丈夫死亡。“瑟”,象征女子,或象征爱情,并非泛泛联想。诗人在《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中也说:“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弦危中妇瑟,甲冷想夫筝。”明言“妇瑟”“夫筝”。宋词人贺铸说:“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元诗人元好问说:“佳人锦瑟怨华年!”(《论诗三十首》)“锦瑟”都与佳人、华年相关。
【句解】
锦瑟无端五十弦,
[五十弦,言其声之悲,从而引出华年之思。无端,有怨望口气,痴情语。传说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阐而悲。]
一弦一柱思华年。
[“一弦一柱”,每弦每柱,代指瑟之音响。“思华年”的并不是“弦柱”,而是闻弦柱之音的诗人。闻瑟而思华年,明言主旨,并无含糊。“华年”,青春年华——青春年华的情事。]
庄生晓梦迷蝴蝶
[倒装比喻句:我之晓梦(如)庄生梦蝶一样迷幻——那梦中的蝴蝶,是我?是她?美丽而又虚幻。重在“迷”字,这一典故基本含义为沉迷,痴迷,虚幻无常;而“晓梦”又喻示其凄迷而不可久长。]
望帝春心托杜鹃。
[同上:她(一指情人)之春心(如)望帝托鹃一样执著——我从杜鹃的啼鸣中听到了她的心声。重在“春心”,这一典故的基本意义为爱情的“悲苦孤凄”。春心,情爱之心。杜鹃啼血,执著也。此联写心心相印,刻骨相思。]
沧海月明珠有泪,
[同上:月明之夜,我以沧海蛟人的诚意,泪下成珠——献给她!有:为也,作为;实是泪为珠之倒辞。泣珠:传说鲛人水居如鱼,泣泪为珠。月满则珠圆,月亏则珠缺。《广释词》:有——是。《孔雀东南飞》:“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杜甫《腊日》:“漏泄春光有柳条”。]
蓝田日暖玉生烟。
[同上:日暖之时,她似蓝田美玉,化为轻烟,可望而不可即。生,亦当解作“为”。《汉语大词典》有此义项,又有“升起”“转世”等义项。紫玉化烟:《搜神记》:夫差女紫玉和韩重相爱未果。紫玉死,韩吊于墓,紫玉形现,韩欲拥之,紫玉如烟而逝。《广释词》:生——成。何逊《送沈助教》:“未觉爱生憎,何见双成只。”“生”“成”互文。杜甫《遣闷奉承严公二十韵》:“藩篱生野径,斧斤任樵童。”谓藩篱成野径。此两句合读意为:我徒然哭泣,对方却如烟般消逝,泪亦空流也。此联写两相阻隔,相思而无缘相聚。]
此情可待成追忆
[省略句:岂待追忆时才感到惘然。扣住“华年”之思,进而点明“惘然”之态。“情”字透出全篇核心。照应首联之“思”。可待,岂待。]
只是当时已惘然。
[当时即已惘然,今思之忆之,更有痛定思痛之深悲也。只是,就是。当时,指某一段时间内的情事,不能指“一生”。]
【章解】
这是一首“感旧怀人”诗。首联由“锦瑟”起兴,引发对“华年”的思忆。中间两联具体写“华年”情事,写刻骨的相思与血泪的悲苦。颔联重在写“心”,写夜思梦想之炽烈;颈联重在写“身”,写花前月下之不得见:心相通而身相隔也。且对句分写,两两对称,一句写自己,一句写情人;上下又可以互解——我之迷亦彼之迷,彼之心亦我之心;我之泪亦彼之泪,彼之姿亦我之姿也。如此,四句写足“华年”情事之“惘然”。尾联跳出“追忆”,回到现实,以深长的感叹作结。点明“情”字、点明“追忆”,以与“思华年”照应,清晰而严谨。由于用典,诗意丰富而含蓄,特作今译如下:
锦瑟无情不相怜,
无端多到五十弦。
瑟曲悲切一声声。
引我魂飞忆华年。
我,长夜难眠,梦中寻她到五更天,
犹如庄周梦蝶心迷乱,
是她飞入我的梦境,
还是我飞进她的心田?
她,锦心微澜,难销春情一片,
就像望帝化杜鹃,
一声声啼,一声声唤,
直啼得鲜血淋漓口舌残。
我,泪眼望欲穿,就像沧海鲛人,
在月明之夜,泪作珍珠捧到她面前。
她,身影恍惚间,就像蓝田美玉,
在阳光中,缥缥缈缈化作一缕烟。
此情此爱随流水,
岁月无穷恨绵绵。
岂是今日空追忆,
当初何曾不惘然!
【异解】
对本篇主旨的理解
1 黄世中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D05年)题解:
自宋至清笺释者“不下百家”,大别有十四种解读:以锦瑟为令狐楚家青衣,义山爱恋之未遂,是为“令狐青衣”说:以中二联分咏瑟曲之适、怨、清、和,是为“咏瑟”说;以为锦瑟乃亡妻王氏生前喜弹之物,诗以锦瑟起兴,睹瑟恩人,是为“悼亡”说;以为诗“忆华年”,回叙一生沉沦苦痛,是为“自伤身世”说;又有“诗序”说,“伤唐祚”说,“令狐恩怨”说,“情场忏悔”说,“寄托君臣朋友”说,“无解”说,以及数种调和、折中,合二、三说为一说,等等。余意《锦瑟》当为“悼亡”之作,然身世之感在焉。
2 《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我觉得如谓锦瑟之诗中有生离死别之恨,恐怕也不能说是全出臆断。(周汝昌语)
3 韩兆琦编著《唐诗选评集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说明:
以锦瑟起兴。追述了哀婉凄楚的一生,抒发了诗人怀才见弃、壮志难酬、岁月虚度的悲伤,表现了诗人回顾往事时无限沉痛、怅恨的心情,也反映了诗人理想破灭后对社会、人生的清醒认识。
4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57年)
作意:大概近于悼亡为是。
作法:首二句,隐指亡妇之年龄五十弦折半为二十五岁,故曰“华年”。颔联上句又兼用庄子妻死,骨盆而歌的意义。下句隐说身在蜀中,效子规的啼血……颈联,上句是说哭泣,下句是记姿容。换言之,三句是写遇合,四句是写分散,五句是写悲思,六句是写欢情……末联则意义较明,“此情”即指上面悲欢离合之情,是说生前情爱,往往漫不经心,一经死后追忆,觉得当时爱情已惘然若失了。
5 陈增杰《唐人律诗笺注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笺注:
锦瑟:作者睹物起兴,“无端”二字,有自怨自怜意。庄生:“晓梦”,言梦之短暂。迷,状梦境迷离,叹人生变幻无常。下句写听鹃啼鸣,自伤迟暮。珠有泪:二句言失去的美好生活,不能再来,徒然令人向往。此情:当日迷惘之况,令时追忆,情更迫切,益为伤感。附论:在众多释解中,我们认为“闺情”和“自伤”说较合诗意,朱鹤龄的“感旧怀人”一语(见《玉谿生诗说》引,纪昀称“此说是也”),甚得要领……
【余论】
诗,也是有逻辑的
读诗,我们强调语言“通解”,就是要认认真真地研读诗的语句,不可离开语句本身作无谓的联想与猜度。此诗首尾两联,将其要抒写的“事”与“情”已然交待明白:“追忆”“华年”往事,抒发“惘然”之情。其“事”限于“华年”,限于“当时”:其“情”限于“惘然”。所以,凡说“一生”等等,都显然不合诗意。至于“咏瑟”说、“诗序”说等,不仅与“华年”“当时”之时间限制不合,与“惘然”之情也难以对应。是否“悼亡”呢?似乎也不是。因为诗人与亡妻生时(当时)的关系并无龃龉,更难说令人“惘然”。
所以我取“感旧怀人”说。从诗的整体情调看,这所怀之“人”,当是一位与他心心相通、情深意笃而又无缘聚首的人。这样看来,“令狐青衣”说也许靠谱。
这首诗还有一个特点,也是难点,就是中两联的解读。历来的论者,都把它看做诗人一面的独白。而这样的解读,很难讲清楚四句诗之间的逻辑。喻守真说“三句是写遇合,四句是写分散,五句是写悲思,六句是写欢情”。“庄生晓梦”怎么是“遇合”呢?为什么五句写了“悲思”,到六句反过来写“欢情”呢?陈增杰先生的“笺注”也是如此,一句一句看,都可通;连起来看,就完全没有逻辑。所以我把这两联看做“对举分说”:一句说自己,一句说情人。如果单说自己,是单相思,悲剧是一人之悲剧;现在分说双方,则悲剧是两人之悲剧,有增一倍之悲的效果。这样解读,在逻辑上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北京第十二中学高中部 100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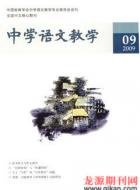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