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26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26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让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读书成为每个人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否可以这样说,教学的终极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培养学生持续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从而让阅读陪伴其一生,使其进入永远追求阅读快感的人生境界,从而不断优化他人生的情意结构,优化人生。优化他的道德评判标准,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人力基础。为实现这样的目的,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必须摆脱过于功利性的读书。而追求快乐的有兴趣的读书,让有兴趣的读书成为师生共同追求的教学目标,从而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增强阅读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不断地去自主开拓阅读的广泛价值,不断地去体验全新的阅读快感。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阅读教学中追求阅读的陌生感,要围绕阅读陌生感的激活和处置走出新的路子。
一、阅读陌生感的元形态来自于作品创作的陌生感。
1 任何作品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化的背景和条件。
首先是作者的生活体验非同一般,具有陌生价值。著名作家邓友梅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自己创作方向的把握、创作风格的历练和创作素材的提炼的事。他说,文革一结束,他琢磨最多的就是如何使作品与众不同。他看到肖复兴写新疆农垦生活,张贤亮写大墙内的生活,都成功了,成功原因就是写了别人不熟悉也不能写的内容。而自己与他们不同的是年龄虽差不多,但工作得比他们早,且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就有了得天独厚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积累。另外,他在天津时的左邻右舍,三教九流都有,包括满清时的落魄的王爷公子,这就有了特殊的社会环境素材。这些“陌生”的东西促成他写出了《话说陶然亭》《烟壶》等作品,且轰动一时。
其次是作者观察生活的视角非同一般。生活在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环境里,由于观察生活的视角不一样,写出的东西就各具面貌,各有情态,在常人眼里就很“陌生”,就觉得它不是什么类型化的东西,没有复制痕迹。朱自清和俞平伯在同一时期,乘同一条船游览秦淮河,写出了都让人叫绝的有自家面孔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根本原因就是两人观察生活的视角不一样,有不同的感悟和抒情寄托。
再其次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非同一般。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和鲁迅笔下的人力车夫。虽都是旧中国拉车的,但作者创作的目的不一样:前者要写出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拉车夫苦难的生活,以及被黑暗社会逼上绝境的生活现状;后者却要写出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拉车夫善良豁达的本性。表现底层劳动者高尚的人格。同样写母亲,胡适的《我的母亲》是要写出一个忍让大度、严格宽厚的母亲形象,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深切怀念;而邹韬奋的《我的母亲》则写出了母亲是一个慈爱、望子成龙、善解人意的旧式妇女,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怀念和愧疚之情。这样创作的结果,就使人物形象处在似又不似的境界,彼此之间就具备了互相排斥的陌生距离。
2 任何作品在叙述方式和语言运用上都与众不同,不以常人方式展示,语言的陌生感越强烈,作品的个性也越鲜明。
音乐评论家徐冰曾这样评价谭盾的音乐:“今天听谭盾的音乐,你就觉得说不出它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作品才是有意思的。”而这种“有意思”就是植根于音乐语言的原始性和非理性。同样画《富春山居图》,古代的黄公望和现代的叶浅予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所用绘画语言不一样,虽对象一致,但画面迥然。前者浩渺浑厚,后者新彩华丽。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同理。很多作品就因了叙述方式的陌生和语言运用的陌生,最终使作品呈现强烈的陌生感而独步时代。鲁迅作品风格的冷峻与深刻,朱自清作品风格的华丽与深细,余秋雨作品风格的繁富与厚重,贾平凹作品风格的典雅与朴茂,都是令人击节称赏的。而启迪人追逐他们的根本原因,正是叙述方式和语言运用的陌生感激发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
正是由于这样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不断地锻造创作性格及表现形态,使作品呈现的色彩、风格、思考、摄人心魄的力量都不一样,形成了作品鲜明的陌生感,并沉淀为阅读兴趣源。
二、阅读陌生感的再造和强化得力于对作品陌生感的精细梳理和创新利用,也得力于教师对作品处置的陌生化。
对于学生来说,对每一件作品的初始接触都是陌生的,这种陌生感可以说是先天具备的,故而学生的初期兴趣是强悍而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学生先行阅读,这种陌生感又会随着阅读的完成而变得淡化、退潮、消失。随着陌生感的强悍逐渐走向消失,心理满足后的倦怠也就产生了,阅读的兴趣就会荡然无存。而课堂每一篇作品的教学一开始就处于这样的阅读兴趣的颓势阶段,如果不关注学生阅读的心理变化,不去有意地破坏学生初始阅读后形成的认知架构及兴趣屏障,就有可能使我们的一切设计付之东流。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研究学生的阅读心理,就必须用方法轰击学生已然麻木的兴趣屏障。通过我们教学行为的改变,重新让阅读陌生感回到学生中来,从而让课堂充满好奇、惊讶、感叹、顿首、拍案,使学生的内心因陌生而兴趣盎然,因陌生而情意鼓涨,因陌生而愈益渴望。正是在这无数次的阅读陌生感的培养中,奠定每一位学生产生让阅读伴随终身的愿望的基础。
结合教学实践,我们不妨探索阅读陌生感再造和强化的方法,让教师对作品的陌生化处置成为可能,让学生的阅读兴趣潮水般地涌入我们的课堂教学中。
1 理解切入点选择的移位,能让学生因匪夷所思而陌生感顿生。
对一篇作品的理解往往是从整体阅读开始的,而整体阅读又常常遵循着作者的行文思路展开。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循着这样的阅读思路进行文本研读的话,就会与学生的先期阅读不谋而合,使学生感觉到教学不过是在重复着昔日的故事,而学生的阅读兴趣迅速退潮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将文本理解的切入点来个另辟蹊径,让学生感到本已读懂的作品突然间变得“陌生”,不那么“懂”了,他们阅读的情绪就会回复到初始接触阶段,重又进入亢奋状态。阅读兴趣的重新出现,正是教学成功的预约期待,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的模型暗示。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仅收到当下课堂教学效果良好的反馈,而且还强化文本常读常新的秘诀就在于切换不同的阅读视角这样一种阅读理念。
鲁迅的《故乡》是被咀嚼了无数遍的传统课文,我们自己都已熟悉到产生阅读疲惫感了。这样一篇远离学生生活的传统名篇还能否唤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关键就在于寻找新的切入点,使课文的陌生感放大,让学生和我们一起感到像没有读过的一样又有了阅读理解的冲动。
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切入点:当二十年后
闰土重新和“我”见面时,课文里有这样一句话写水生:“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作者用一个“拖”字,一个“黄瘦”的描写将水生第一次介绍给我们,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作者这样的描写草率吗?写闰土时那样的华彩,写水生时这样的吝啬,其中包含着作者怎样的沉痛之感呢?我们不从闰土说起。而改换一个角度,从配角水生说起,目的正是要通过这样的理解切入点的移位,来增强作品学习的陌生感,来燃烧起学生“重新”阅读的激情。
当然,选择水生说起不是没有意义的单纯求“新”,而是可以通过对水生的分析带起与闰土的对比,带起对二十年后故乡愈益贫困化的思考,这又和对课文主题的理解是一致的。
2 人物形象意义分析的与时俱进,解读的不落窠臼,能使学生感到新鲜,陌生感油然而生,阅读兴趣的复位水到渠成。
课文中一些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似乎已成为文学画廊中的老照片,早有历史定论,岂容后辈多嘴。如果仅仅满足于将历史定论传达给学生,那么,我们想要看到学生交头接耳热议的场面将是南辕北辙。所以,我们不妨与时俱进地阅读这些作品,从中读出点新意来,读出点人物的崭新光彩来,然后引发学生逆向思维的兴趣,让这种新的阅读带给学生新的认识,带给学生陌生的沉思和结论,来个老树发新芽,让清新的画面促使学生兴奋点的生长。
《老王》(人教版八上)是杨绛女士描写底层人生活及表达自己悲悯情绪的一篇力作。对于老王的评价都停留在“老实厚道”“有良知”“知恩图报”上,学生自主阅读对老王的认识也基本与此相同。如果我们教学这篇课文也仅仅沿着文章的顺序了解老王的职业、生理缺陷、居住条件和老王给“我”家送冰、送病人、送香油鸡蛋的事,以及得出老王是老实厚道的好人的结论。要让学生激发出更多的阅读兴趣是困难的。我们不妨在人物评价上挖掘更多的深层的信息,提出一些让学生颇感意外的“陌生”问题,然后给人物以新的价值定位,就必定会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并教会学生一定的与作品人物对话的途径与方法。问题可以这样设计:文中作者写道。文革时丈夫生病了“烦老王送他上医院”,但自己却不敢乘老王的三轮,这是为什么?而老王却敢送病人,这又是为什么?当老王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却坚决不肯拿钱”,还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些细节的描写反映了老王是个怎样的人?结合文革这一特殊年代的历史背景,老王就不仅仅是一个大众性的泛化的厚道人、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正直的人,正义与正直,恰恰是千百年来底层百姓的共同追求,并可以说是渗透血髓、与生俱来的人格高标,也是道德底线。这样的人物评价不是凭空塑造,而是立足在作品的细读基础上。正是由于这样的设计,人物评价的盲点赫然摆放在学生面前,学生因“陌生”而惊讶,因惊讶而陡生弄通他的兴趣。这样的教学才能真正让学生“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3 语言赏析注意寻找新的生长点,让学生沉浸在陌生感的氛围中,内心充溢着好奇与惊叹。
语言是载体,它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诸多元素。阅读作品不仅仅理解作品,解读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欣赏作品、审美作品。而欣赏和审美又离不开语言的欣赏和审美。正是通过对语言的品味欣赏和审美理解,才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眼光,才能永葆他们对文本的阅读兴趣,因为语言本身的美感是最本真、最原始、最纯粹的审美客体。也是最具魅力、最经得起时间洗刷的审美客体。
温庭筠的《望江南》和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同在人教版九(上)教材,且前后编排,其中“悠悠”一词两首词都有,但意味不同,学生一般很容易忽视。我们不妨设计这样一个欣赏题:“温词中‘斜晖脉脉水悠悠’中的‘悠悠’和范词中‘羌管悠悠霜满地’中的‘悠悠’意思一样吗?为什么?”这样一问,学生显然没有准备,从阅读的角度看他们会感到很“陌生”。从词汇意义看,“悠悠”一词均作“长久”“遥远”解。但结合两首词的情境欣赏,这“悠悠”一词却负载着不同的审美信息,具有不同的审美意义。温词中的“悠悠”寄托着女主人公的相思、哀怨、无奈如水般悠长,绵绵不断的江水带走的正是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之泪,我们透过“悠悠”一词可以想见的是女主人公哀怨的神情和凄迷的眼神。而范词中的“悠悠”寄托的却是戍边将士思念亲人渴望归乡的情感,“悠悠”的羌笛之声既是胡声,很苍凉空寂,又是思乡之音,很悠长遥远,将军征夫应秋而起的悲凉与为国长年戍边的慨然之气,被“悠悠”的羌管送得很远很远。
这样寻找语言赏析点既是文本研读的需要,也是阅读陌生感产生的优质基点。
总而言之,既然阅读陌生感能有利于我们的课堂教学和文本阅读,能真正让学生在富有兴趣的阅读中去体验阅读的快乐与增长阅读的能力,能使自己审美的目光敏锐,能砥砺自己评价的思想,我们不妨充分利用它来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并达到培养学生终身有兴趣阅读的目的。
(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研究中心 214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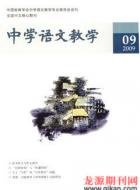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