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1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1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张超老师在与管然荣老师“对话”时说,“我欣赏孙绍振教授的‘还原法’——还文本本来面目、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解读法”。张老师在《(项链)教学实录》(《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7期)中引导学生发现鉴赏精彩传神的细节描写就是例证。他能从文本细微处出发,引导学生把握主人公的形象,探究其悲剧根源,如从向贵族靠拢的工具“猎枪”上、用来炫耀的“请柬”上,感受罗瓦塞尔先生的虚伪;从自惭形秽的马车、装假项链的真盒子等细节,感受巴黎社会崇尚虚荣。这种尊重文本的探究,读出了语言节点的丰富内涵,很有价值。
然而。孙教授的“还原法”中还包括“历史的‘还原’”。即把作品放到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去,特别是还原到产生的艺术背景中去。《项链》作为外国文学作品,不应看做独立存在的实体,割断它与西方文化的联系,而应结合西方文化背景分析,才能深入把握人物形象,开掘文本深刻内涵,使罗瓦塞尔夫人的悲剧上升到人类的悲剧,深化小说的主题。
西方的文化著作,始终贯穿着“原罪”文化,“原罪”指《圣经》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犯的罪,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流放人间。于是人“在罪孽里生”,必定在人间忏悔、赎罪。“原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底色,是西方文化的根,因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项链》也根植于此。“原罪”文化中最鲜明的一点便是人间非天堂(伊甸园),世界是荒诞的、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不合理。人生是悲剧,是不可捉摸、没有意义的。人本身是有缺陷的,不是万物灵长,只有通过劳动、创造来实现自身价值。
懂得“原罪”说,读《项链》,我们才可理解“生活是多么的奇怪!多么变化无常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把你断送,也可以把你拯救出来”的含义,张老师理解为“这段文字多么像玛蒂尔德的内心感慨和独自”,可谓浅尝辄止。这句话反映了人生的荒诞感,这种荒诞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所说的“人生如梦”,因梦有喜有忧,有噩梦、思梦、惧梦等区别,且中国古代文人对人生的虚幻感与瞬息变化感多产生于人生不遂意之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把你断送,也可以把你拯救出来”,则体现了人面对命运时的无能为力,人对命运的不可把握,人生充满了变数这样的悲剧性。结尾玛蒂尔德为之辛苦十年的项链竟是假货,这令人对奋斗的人生也产生虚幻感,冥冥中命运之神似乎又一次戏弄了苦苦奋斗的人们,给作品涂抹上更浓郁的荒谬感和悲剧色彩。成也项链,败也项链。玛蒂尔德用十年时间对项链牢笼的突围,也是对无序无常的命运的一次突围,具有终极性的关怀性质,因而这种突围不仅是个体的行为心理,还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张超老师引导学生认识到“虚荣心并非玛蒂尔德独有”,但分析依旧围绕着个体的“玛蒂尔德”转。我们仔细阅读文本,运用“还原法”,将作者省略的、回避的等内容,进行推理、想象和还原,就会发现小说展现的不仅是玛蒂尔德对命运的抗争,它还是“玛蒂尔德们”,包括“佛来思节夫人”对命运的抗争。“玛蒂尔德”和“佛来思节夫人”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是一类人的代码。
因而笔者认为,只有结合西方“原罪”文化探究文本,才能更真实地还原文本,认识到玛蒂尔德对命运的抗争,关乎人类对人生的终极性命运的叩问和关注,充满了哲理和悲剧色彩,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而小说的“豹尾”,也不再拘囿于构思的精巧,而是展现西方原罪文化包括基督教所弘扬的人性美,即玛蒂尔德诚实、勤劳、勇敢,维护人类的尊严;而贵妇人佛来思节夫人,听到朋友的叙说后,感动得几乎脱口道出假项链的真相,诚恳单纯,对朋友充满悲悯情怀。
(江苏省江阴市长泾中学 214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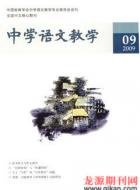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