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48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48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语文老师永远不要忘记《学习的革命》一书中的两句话:第一,我们确信,最伟大的真理是最简单的,最伟大的训诫是最易明白的;第二。大多数好的学习方法都是常规,但每个孩子都通过许多这样的方法学习。今天,我想用这两句话作为标准,来研究、思考、品味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
说到王尚文先生,首先就要提起他的“语感论”。王尚文认为,言语形式是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之“纲”,并以茅盾《风景谈》中的一段话为例阐述:不能简单地把“三五月明之夜”翻译成“农历每月十五月色明亮的夜晚”、“宛如”就是“好像”等等,因为重要的不是作者描写的对象而是他用以描写的语言,在语言中作者按照美的法则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创见澄清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语文应该教什么的问题。朱熹曾说过,大凡物事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如昔人赋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得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朱熹所说的“如何形容得好”即指“言语形式”,而只有通过“言语形式”这条途径,才能品味出文学作品的“言外之意”。因此,只有以“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才能保证语文课的“语文性”和“语文味”。“涵泳”,是传统语文教育观的教学方式。我国古代的语文教学从来注意对文章的整体把握,主张反复讽诵,潜心涵泳,以明达文意。“涵泳”之说前身是“意会”,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庄子。《庄子·无道》说:“语有贵也。语之所随者,意也。意有所随,不可以言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观点,对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朱熹独辟蹊径采用了“涵泳”两字,他说,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有自见。清朝曾国藩极为推崇朱熹“涵泳”之说,称它为“最精当”的“读书之法”。他说,“涵泳”二字,最不易识……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以涵泳为主要方式的教学模式体现了伦理型文化朴素的整体观念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它把综合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归宿,避免人为分割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孕育着现代系统的雏形。如果我们把涵泳也作为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是带有综合性的。它是一个人思想品格、审美情趣、文学修养、语言功底以及生活基础等诸因素综合的体现。我国古代的语文教学十分重视涵泳,重视在涵泳中培养学生对言语形式的感受。这无疑是正确的;在阅读教学中重视语感的培养,并以此作为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基础,是符合语文这门学科规律的。
其次,新时代语文学科“课程标准”提出了两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概念”——“素养”和“养成”:明确指出了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过程、方法——“基础”“习惯”和“兴趣”。从“语感教学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王尚文先生非常重视“诵读”的作用,认为书面语的阅读只有还文字以声音,才能在倾听中找回生命的气息,找到心灵的感觉。语文素养的养成,最主要的还是要多读,熟读能将言语对象内化为语感图式。我国古代的文言跟口语基本上是脱节的。但我国古代的语言教学硬是在不太长的几年时间里,基本上能让大部分学生得心应手地运用文字表情达意,这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因此王尚文先生把“熟读、背诵课文的习惯”作为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时必须养成的“十大习惯”之首。对于诵读在课堂教学中的指导,可谓十分具体,如“可以先由教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自己练习着读,有时还得背诵”,“每讲完一遍,还该由教师吟诵一两遍,并该让学生跟着吟诵”等等。而至于诵读的作用,首先当然是对文本深层意蕴的领会和把握——“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知道它们的味儿”,“吟诵是诗的兴味的发端,也是诗学的第一步”,“只有在吟诵里,骈文和所谓八大家,以及近体诗,才能发挥充足的意味”。但是朱自清对诵读的价值,则有着更为深入而精微的思考。他说过,一般人讨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都只从写作方面着眼;诵读方面,很少人提及。大约因为写作常用,问题的迫切,显而易见:诵读只关系文化,用实用的眼光看去,不免就是不急之需了。但从教育的立场说,国文科若只知养成学生写作的技能,那就太偏枯了。了解和欣赏是诵读的大部分目的,诵读的另一部分目的是当做写作的榜样或标准。朱自清认为诵读不但有实用的功能(为写作提供榜样或标准),更有文化的功能,而文化的功能才是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技能训练的偏枯需要诵读来补救。当前语文教学出现严重的“泛语文化”倾向,表面热热闹闹,实则空空洞洞,带着“人文”的初衷。却走向了“人文”的反面,朱自清、王尚文等人对于诵读的高度重视,能否给我们以启示,以便尽快找到“疗救”之道呢?
此外,王尚文先生认为学生还要有“推敲语言文字的习惯”。同样地,“辨词析句”的能力也是我们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整体阅读”无疑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闪亮的理念,但很容易被浅化、俗化、泛化。对文章主旨的简单把握不能算“整体阅读”,对文章作者思路作一般性的清理不能算“整体阅读”,对文章思想情感的肤浅概括更不能算“整体阅读”。如此等等。“整体阅读”决不应导致语文教师抛弃“辨词析句”这个看家本领。周汝昌先生在北大一次演说时说:“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整体阅读”这个概念,既非常现代,又非常传统;既是非常人文,又是非常工具的。“整体阅读”,一靠基础。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具有夯实基础的功用。二靠习惯,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叶老多次指出,语文教育,归根结底是习惯的教育。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里的“义”现,就是指“整体阅读”。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决不是“整体阅读”。三靠积累。“课程标准”中重复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积累”,这道出了语文教学的本质。如果在长期语文学习中没有积累。包括汉字的积累,经典篇目的积累,以及极为重要的文化与生活的积累,那么,就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因为文化的积累构建底蕴,而生活的积累产生灵性。教李密的《陈情表》,语文教师不能不关注全文475个字中一共用了29个“臣”字。其中除了两个“臣”字指朝臣外,其余27个“臣”字均为李密自称。这是旧汉之臣与新晋之帝间的对话。一口一个“臣”字,心意切切,诚惶诚恐,卑微谦恭,使“听话者”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既感谢皇恩之浩荡,又感谢武帝之宠幸,可见李密用心之良苦。一个有经验的语文老师不会不懂得:辨词析句自然是从小处着手,但又需从大处着眼,离不开文本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依托,特别是作者的人生态度、思想情感的倾向。
从以上三点我们是否能够发现,以“语感论”为重要标志的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通过“涵泳”“诵读”“辨词析句”等词语来落实,显得十分简单朴素。其实,真理往往就是简单而朴素的。语文教育需要提升其科学性,而科学性恰恰蕴含在王尚文所说的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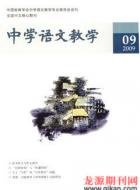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