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29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29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很多老师都说,现在每看到学生的“文化历史大散文”就有些厌倦,这些文章往往形式一律,似曾相识,没有什么生命活力,总像是从哪儿抄来的,坊间称之为“秋雨体”。说句公道话,这件事也不能全归罪余氏,虽然他自我炒作,不能说没有责任,但推波助澜起而效颦者也太多。我曾翻看过一套40卷的散文大集。有一半作者也能娴熟地用那样的“体”,足见出版时是有市场的。令一些教师喜欢的是。“秋雨体”的高考作文曾得过高分,“秋雨体”的大赛作文曾得过奖,于是大行其道。
学生模仿,“本钱”往往不够,因而雷同之作极多,遂成鸡肋。常用到的人物有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李清照和曹雪芹;人物活动的特定季节多数是秋天,时间一般是夜里。场景一般在江边、高楼或后院,人物一般仅一人(因为人多了他就没法子写),人物情绪基本是遭遇不幸、贬谪、迁徙、离散后的失意和孤独……当然,人物可以互换,如岳飞可以换成辛弃疾,李清照也可以换成曹雪芹……像个魔方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位这样写的学生都以为自己独一无二,他却不去想读者会感到腻味。
我因孤陋寡闻,也上过当。大约是十年前,每看到学生作文说起屈原司马迁的境遇,说起嵇康苏轼的命运。总以为学生还有点书卷气,有点读书的“底子”,这样的作文,放在大部分不读文学的学生群中,一下子就显现出来。2000年江苏省作文大赛,有位学生写竹林七贤,借《世说新语》中的小故事,连缀加工后搬进作文,两千多字,行云流水,入选时评委都拍案称奇,委托我找作者谈话,了解是否抄袭。谁知不过两三年,能写这种“文化历史大散文”的高中生越来越多。平时作文中并不多见,也许是没有什么好处,不值得下饵,一到作文比赛或是高考,就冒出一大群!而一些中学生作文刊物的编辑则见怪不怪,说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文风。我和同事们曾归纳其特征,日:“滥抒情,口吐白沫;假叹息,无病呻吟。沾文化,满地打滚;伪斯文,道貌岸然。”
每年的作文大赛。都会有一些选手乐此不疲。不管大赛命的什么题目。他都能强行把那准备好的从屈原司马迁到林则徐谭嗣同全塞进去,乃至让命题评审组全体目瞪口呆!有一年作家叶兆言以“禁止鸣笛”的交通标志命题,看图作文,竟然有十多个学生照样玩“文化历史大散文”,记得有位同学从秦始皇的“禁止鸣笛”一直说到岳飞的“吹笛”。莫名其妙。
2008年,为了纠偏,我们在省高中作文大赛中规定学生写议论文,题目是“没有问题的问题”。题目有点难度。但我们想的是:这两百多写手是全省几十万高中生中挑出来的。总不至于束手无策吧。可是我们失望了。赛后一些同学叹息“准备好的材料用不上”,“套不上”,他们准备了什么材料来“套”呢?我想知道。听学生自述,我们发现,他们仍然认为“文化历史大散文”可以“通吃天下”,因而一如既往地“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而不知这一套早已过时。面对题目。他们想强行套作。发现有困难。有位选手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当你今天走进考场时,是否在想:今天要唤醒地下的哪几位古人来客串你的‘文化历史大散文’?……五千年厚重的文化以滑稽的方式活生生地被功利化了。当这些‘文化历史大散文’刚刚出现在中学课堂时,曾让我们欣喜,而当它疾速泛滥之时,它已经掩饰不了华丽外衣下残破的洞……”作为评委,看到这里我们松了一口气:学生总算醒过来了!
“屈原悲壮地向我们走来……”“司马迁抬头仰望满天星斗……”“易安女士的心。像碎了的涟漪……”——如果连中学生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蒙人的拼装术,是“装修”“粉饰”“忽悠”,教师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传授这种毫无价值的套路呢?
生活很重要,阅读积累也很重要。一些同学读书比较单一,“吃偏食”,因而下笔总是一个路数。加上教师错误的指导,“写记叙文靠余秋雨,写议论文靠周国平”,已经是一些同学的写作金箴,也成了教学圈内不言自明的“高考作文潜规则”。
“文化历史散文”不是不可以写,对历史文化阅读多,善于思考的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发现,在思维上有突破,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在表达形式上也会有创造,但绝不是简单地演绎,投机取巧的拼装。王立根老师曾借用马克思严厉谴责法国诗人沙多勃里盎(一译夏多布里昂)时的经典话语来批判这种糟糕的文风——“虚伪的深刻、谄媚的夸张、感情的卖俏、杂色的光彩、语言的修饰、戏剧式的表演、壮丽的形态来哗众取宠,媚悦于世”。
从写作学习的发展规律看,学生丢弃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懂得理性地分析问题,只会模仿或是演绎历史人物生平故事,那他今后的学习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是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如果高中时代沾上了这种不良文风,可能好多年也纠正不过来。这是足以让我们警惕的。
(江苏省南京师大附中 210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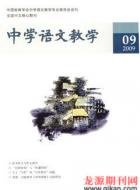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