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9年第7期
ID: 138336
语文建设 2009年第7期
ID: 138336
让我们走出两极思维的怪圈
◇ 黄厚江
检讨六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的语文教学改革,我们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改革的总体轨迹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对立的两极思维严重阻碍了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
这种对立的两极思维首先表现在对语文学科自身的认识上。对“语文是什么”这样一个原初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会儿是“工具”,一会儿是“文化”。而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摇摆,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语文和“思想”两者关系的理解上。之所以给思想加上引号,是因为在不同时期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和表达也不完全相同。传统的说法是“道”,较长的一段时间称之为“思想教育”,目前的主要表达为“人文”。到底称之为什么,倒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对它和语文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它所表达的内涵的理解。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典型的是十年动乱期间),语文完全成了“思想政治”的附庸,最严重的时候,连语文教材也由毛泽东语录替代。自从应试教育成为各个学校的唯一追求,语文的狭隘工具论便大行其道。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主要就是围绕工具和人文两个概念展开的。从语文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当然不能否定这场讨论的意义,但讨论双方都是各执一端,讨论成了“两极”对话,不了了之的结果在意料之中。表面看来,目前两种声音都小了。但这不是说明矛盾解决了,而是表明双方对对方的放弃,同时也表明这样的两极思维更加隐秘化。
这种对立的两极思维,更多地体现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知识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段时间的语文教学,把语文知识作为教学内容的主体或全部,什么文体知识、语法知识、修辞知识、写作知识、文学常识、逻辑知识,无论备课还是教学都围绕知识点转圈,阅读教学、写作教学也都高度知识化。新课程改革之后,又出现了对知识的极端淡化。语法没有了,修辞不见了,更没有人再谈文体知识了(至少公开课是如此的)o最近讨论语文课程知识的人又多起来了,稍作分析不难看出,还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在讨论:一种是狭隘的知识观,一种是广义的知识观。其他如目标问题、训练问题、文体问题等都存在着这样的两极思维。
在具体的教学行为上,这样的对立思维也很突出。以前是以教师为中心,一切教师说了算;现在以学生为主体,一切跟着学生转。以前是完全局限于文本的封闭的课堂教学,现在强调课堂的开放性,抓住一个话题,便信马由缰,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以前是句句讲解,段段分析,现在则浮光掠影,不着边际。以前是钻在课文里不出来,现在是课文根本没有读,忙着开展各种活动。以前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现在合作学习了,什么问题都先小组讨论一番。以前是一切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现在是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当然,这里的“以前”和“现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其实,就是今天,从教师群体的整体情况看,我们还会发现,一方面是部分人仍然高举着人文大旗,把语文课上成人文教育课、思想教育课,甚至是道德教化课;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埋头苦干的仍是只有知识点的应试课,语文教学理科化、语文教学习题化的情况并不鲜见。
种种现象,不一而足。毫无疑问,这样的两极思维对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是极为有害的。两极之间的摇摆,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不说,更可怕的是混淆了视线,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信心。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两极思维怪圈,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治气候的影响。语文学科很难摆脱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如果对不同时期的语文教材和高考作文题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影响的明显。而六十年来的政治路线则表现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摇摆曲线。
二是浮躁的改革心态。我们的语文人大都有着很高的改革热情,更不缺少为语文教学改革呐喊奔走的先驱,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在热情的背后,有时潜藏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一次课程改革启动初期,不少人就把改革理解为“革命”。似乎所有旧的都是坏的,一切都必须推倒重来。不少人以为,这将是一场颠覆一切的革命;不少人希望,一夜之间语文教学就面目全新。再加上一些行政改革者的推波助澜,于是失去应有的科学冷静和理性克制,就在所难免。
三是现实利益的驱动。这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利益的驱动。比如长期以来,简单化的应试教学,就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屈从。二是绝大多数教师的惯性心理和惰性,因为一旦放弃以前的做法,就要在精神上和精力上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即使认识到新的做法是正确的、好的,也有人不愿接受,更不用说主动探求最科学合理的做法了。三是少数改革者,为追求改革的轰动效应,为显示自己改革的决心和胆识,把很多本来应该是折中和留有余地的做法推到了一种极端。
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1995年接受国家教委任务,新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时提出了“守正出新”的编写方针。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科学冷静的态度。我们理解,“守正”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不走极端,不搞全盘否定,不为改而改,更不刻意地标新立异。在此基础上追求“出新”,才是可行的、科学的。为改而改、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做法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始终以为,语文课程的许多看似对立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找到平衡点加以解决的,包括所谓工具和人文的问题、课程知识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教学行为上的种种问题。关键是大家要走出两极思维的怪圈,关键是要有科学冷静的改革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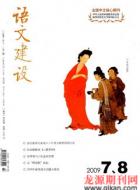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 “语文”课程名称亟须规正 / 潘 涌
- 敬畏母语 / 史绍典
- 素质教育视野中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 李 节
- 让我们走出两极思维的怪圈 / 黄厚江
- 看母语教学地位的升沉 / 于漪
- 论点摘编 /
- 两个答 / 王尚文
- 谈《鲁滨孙漂流记》的后殖民语境 / 龙剑明
- 回望六十年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轨迹 / 顾振彪
- 语文定名六十年,名实相副何其难 / 王松泉
- 语文教学的去知识化和技能化倾向 / 倪文锦
- 主题组元潜藏的危机 / 施 平
- 生活本位与伪科学化 / 潘新和
- 浅析小作文训练的类型、特点与价值 / 钟家莲 邓小珠
- 对比阅读: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 钱理群
- 抒情景观中的悲剧氛围 / 孙绍振
- 学生主体与语文知识内容的缺失 / 徐林祥
- “刘姥姥进大观园”喜剧效应的心理分析 / 翟应增
- 好嘴“好”在哪里? / 章国华
-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叶利清
- 一利化干戈 / 叶茂樟
- 论语文教学中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 / 李福灼
- 浅析苏轼的“以文为诗” / 曾 姝
- 斥天与誓天 / 杨小曼
- 评出“真”味,品出“悲”情 / 孙建高
- 此“民”非彼“民” / 杨仕威
- 《雨霖铃》 / 梅培军
- 《采薇》教学设计 / 徐德琳
- 追求课堂训练设计的有效性 / 王 君
- 根据现实阅读需要创生合宜的教学内容 / 叶黎明
- 优化语文教学的提问策略 / 刘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