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2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2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张永庆老师在与李震老师“对话”时。曾明确说道:“语文课堂对话不能脱离文本,要从文本出发,从词语出发,从句子出发。”(《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6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登高)教学实录》中,有一处“对话”与此说似乎并不相合。为呈现“本真”,兹谨录原文如下:
师:诗人不仅没有排遣愁绪,反而增添更多新愁。大家说一般如何消愁?
生:喝酒。
师:但是诗人有没有喝呢?
生:没有。
师:诗人为什么酒杯已到唇边又轻轻放下?
生:因为他心事重重。
师:说得很对,诗人欲罢不能啊!所以当我们读到最后一句时。应该读出悲咽之声。哪位同学再把最后一句读一下。
(学生读,教师范读)
从“学生读”后“教师(仍)范读”之中,我们似不难看出,教师对学生的朗读并不满意(想必是学生并没有“读出悲咽之声”)。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是这段“对话”脱离了文本,以致学生根本不曾体味出“潦倒新停浊酒杯”一语中所蕴含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苦之情!
苏教版必修四注“潦倒新停浊酒杯”为:“指诗人因疾病困顿。刚刚戒酒,故而登高时不能饮酒尽兴。新停,刚刚停止。”(2006年12月第3版,第61页)“对话”时,张老师即使不“对外联系”(李老师语),似乎也应该“从词语人手,从句子人手”来把握语句含义;虽然,注释中的“(饮酒)尽兴”说与李老师的“消愁”说不甚相合(若将此作为课程资源加以讨论,或有助于将对话引向深入!),但“新停”之“因病不能喝酒”之义却已为所有注家所采信,可谓不争之事实。“因疾病困顿而不能喝酒”与“因心事重重而不想(无心?)喝酒”,这二者之间是不是多有差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也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诗人为什么酒杯已到唇边又轻轻放下”云云。是一段偏离乃至误解文本的伪“对话”!
细读文本,我们自能看出,尾联两句,上句写自己艰苦备尝,自发弥添;下旬写自己潦倒日甚,愁苦难排。此中的“艰难苦恨”,不仅指诗人自己万里作客、衰年多病的艰辛境况和身世遭遇,同时也含有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天下苍生的辛酸痛苦:“不眼犹战伐”,“无力正乾坤”,正是这“艰难苦恨”,才使诗人的白发越来越多,而现在又衰年多病,独自登台,心情自然是更加凄苦。“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在诗人迫切需要借酒消愁的时候,却又因疾病困顿而不得不暂停饮酒——且还是刚刚停止,如此这般,诗人的内心能不愁深似海?此中,诗人仍是用惯常的层层递进的顿挫笔法,来揭示其内心那沉郁不舒的悲苦之情;如果我们的对话不深人至此,学生又怎能“读出悲咽之声”?
笔者甚至还认为,这一段的对话还可以“对外联系”,以引领学生深入理解文本。我们知道,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杜甫的内心盛载了太多太多,这便注定了他的痛苦;因之,诗人也就经常求助于酒,祈求以酒消愁。但生活的困顿却并不能保证他“烂醉是生涯”。于是。他便因“耽酒需微禄”而曾接受过一个与他理想落差很大的管理兵器的“贱职”,甚至还曾“厚着脸皮”向人借酒——“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向人乞钱——“时时乞酒钱”。由此可见诗人对酒的依赖已到了“不可一目无此君”的地步!(详见李志玲《喝不醉的诗人》,《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5期)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引入对话之中,对加深理解“新停浊酒杯”给诗人造成的悲苦,无疑能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果真如此,学生“读出悲咽之声”想必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李震老师说:“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笔者的上述文字。或能为之佐证吧!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实验中学 213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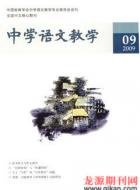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