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0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0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荣维东:我国把写作看做是学生“个人的事”,看成是“文本的制作”,这就使写作损失了它的内在动机和交流功能,成为一桩苦差事。为何很多人讨厌作文,却喜欢发短信、用网络聊天或者诸如此类活动?二者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真实交流的机制和功能。
我认为,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机械的“文本的制作”的作文教学观,是目前写作教学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角度看待写作,那么写作实质上就是一种运用书面语言,针对明确或假想的读者进行的有目的有意义的建构和交流活动。这样的写作,既是一种“问题解决”,一种“思维过程”,一种“信息处理”,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建构和交流”,这显然要深刻和有趣得多。
下面是一个基于交流取向的写作发生模型。
写作的本质在于交流。交流和对话是人与社会存在的本质体现。写作是交流,这是国外作文教学和我国作文教学理念的一大不同。国外是基于社会交流语境进行作文课程设计的,其课标、教材、教学都具有一种鲜明的真实交流或模拟环境下交流的特性。
如下图所示:一旦话题(写什么)、角色(我是谁)、对象(写给谁)、目的(为什么写)这些问题确定下来,写作就变得相对轻松了。写作时,之所以容易出现障碍,是因为“写之前”的一些潜在问题没有解决。
试想,为什么大多数人几乎都可以自如流畅地说话,却不能自如流畅地写作?为什么有的孩子写不好,说起来却头头是道,网上聊天轻松自如呢?是因为:说话的时候,交流要素是相对明确的。它有明确的话题、听众、目的等语境,交谈时还能够基于上述要素不断生成新的信息、念头,并随时进行调整。如果我们的写作也建立在这样一个模拟对话的交流情境和机制中,那么写作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就有可能解决。建立基于“交流”取向的作文教学观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真正解决学生的写作欲望缺失,写作内容缺乏,以及文章体式语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写作应是一种问题解决,不是文本制作。文本制作只是问题解决的副产品。而写作面对的是一大堆“未知”。即“问题空间”,需要填补这些问题空间。思考或构思,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解决过程。想清楚了,也就有东西写了,也就容易写清楚了!至于为什么能说的人却不能写?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即表达方面的问题——书面语言的熟练运用问题。掌握一定的字、词和句式,把构想出来的念头表达出来的“文本的制作”过程,显然是第二位的,是从属性的。
写作是人生活的一种方式。人的写作生活,涉及有外在的生活世界和内在的生活世界两种。写作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内心生活世界,它是建构自我内在世界的一种手段。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写,靠说或者其他方式生活,但那样生活无疑是一种残缺。他可以靠说话传播他的情感,思想,与人分享他的发现和感悟,但他的交流、思维、他的影响力却很有限。述而不作的哲人传播思想必须靠“语录”等文本。
作文课程应回归本源,回到真实。这样的作文不仅仅是“写文章”,也是学习、生活和生命的方式。让学生的作文过程,成为他的一个个“生活事件”。成为融入其生命冲动体验的真实的“成长历程”。这应该是作文或写作的本质所在。中国的写作教学设计完全可以在回归真实生活的哲学理念下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将基于“文本制作”的技能训练的作文教学,向“基于真实或模拟真实”情形下的内在和外在生活世界全面回归,这是一种生命和言语技能的双重建构。写作课程和教师的责任就在于要设法营造学生走人生活世界的机会、动机、策略和手段。
李海林:其实,往大里看,写作只是生活流中的一节。在写之前,写作者在生活着,生活到某一步,需要写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之前生活的继续,之后生活的前奏。果然,他写完了,生活又继续往前走。只不过这个时候,生活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写作的动作,会有些变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写作的动作,也可能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会变成另外的样子。这样的写作,是生活中的一个动作,是生活本身。
这样来理解写作。写作这个动作发生之前的生活,就是十分重要了。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不是“写作要有生活的积累”意义上的重要,生活不是为了“积累”写作素材所以才重要的。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活需要写作”。生活到了这儿,需要我写一点什么才更有意义。生活中的每一次写作,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们为什么写?不就是需要写吗!不就是如果不写。生活会变得不好,生活会停顿吗!当然,也有的人终生不写作,但那不正是生活没有意义的表现吗?不正是生活层次不高、内涵不丰富的表现吗?我们现在教学生学会写作,不正是要让他们层次高一点、内涵丰富一点吗?也就是说,生活对写作的意义,是在“解决为什么写”这一点上,并不是(至少不全是)在解决“写什么”即写作内容这一点上。
写作教学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是解决生活问题,不是解决“要让学生有生活”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学生对生活的意识”。他生活着,但没有体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活。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生活着呢?我们不是一般地“教生活”,而是在“教写作”的问题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是从“写作”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是教学生“如何把生活与写作联系起来”。这里的可联系性就在写作动机:为什么写作,因为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因为要生活。或者说因为要让生活更有意义。
这里面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你现在为什么非要写不可呀?你写给谁看呀?他看了会怎么样呀?你想要让他怎么样呀?你写的时候,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这些境况,会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写完后你会有什么变化?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等等。好像与写作没有什么关系吧?实际上关系大着呢!这些问题,决定作者写什么、怎么写,都由这些“预期”决定着。作者写这个东西,这样地写着,就是为了在这些方面达到他的“预想”。一句话:我想怎么生活,我就会写什么、怎么写。因为写作就置于生活流中。生活在影响着写作,写作也在影响着生活。
荣维东:李老师,我理解,您的“把写作当做生活流的一部分”的观点。是您的“论真实的写作”的深化,这样写作就可以“融入生活”了。可是,细细一想,是否也有漏洞——是不是有必要区分“学生学校写作”和“一般人的生活写作”以及“专业作家的创作”呢?
如果我们把学生的写作看成是“生活中的写作”,是不是会混淆“学生写作”和“作家创作”的区别。学生也确有“习作”的成分在,可是目前把这一点放大了,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哈哈镜中,变形了,异化了。我们看到的大都是那些可以换取高分或者老师赞许的“小文人语篇”(王荣生语),学生在作文时,是用了一副别样的心态,别样的话语,和苦苦练就的“文本制作”的技巧去骗取“高分”。如果取消掉这种“虚情假意”的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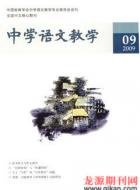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