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6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6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重要最后影响的德语诗人。生于东欧一个犹太血统家庭,1942年父母相继惨死于纳粹集中营。1952年,流亡、定居在巴黎的策兰在西德出版诗集,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引起广泛反响。在这之后,策兰的创作日趋深化、发展,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甚至被称为“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内莉,萨克斯语)。1970年,策兰因无法克服精神创伤而投塞纳河自尽,死后他的诗歌及其悲剧性命运引起了更广泛关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他已被公认为是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
《死亡赋格》为策兰的成名作。无论谈论策兰本人还是谈论战后欧洲诗歌,这都是不可绕过的一首诗。诗中对纳粹邪恶本质的强力控诉。它那经历了至深苦难的人才有的在神面前的悲苦无告,它那强烈、悲怆而持久的艺术力量,至今也仍在感动着无数读者。的确,正如有人所说。它是“二十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自问世后,它被上演,被谱曲,被选人各种诗选和西德的中学课本,现在,它也被选人语文出版社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
《死亡赋格》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这和二战后西方的思想处境、和西方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密不可分。1949年,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多诺这样写道:“奥斯维辛后仍然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无论这个断言在后来是怎样引起争议,它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仅提出了战后西方诗歌、艺术的可能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把“奥斯维辛”作为一个西方心灵无法逾越的重大“障碍”提了出来。
奥斯维辛本来是波兰的一个小地方,纳粹德国曾在那里建立集中营,有上百万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在那里被杀害,所以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不仅大规模的屠杀令人难以置信,其技术手段的“先进”和工业化管理程度都属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身为人类却又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类暴行,产生过巴赫、歌德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却又干出如此疯狂野蛮的事,这一切,都超出了人类理性所能解答的范围。它成为现代人类历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个谜。可以说,对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心灵,它都是一个“深度撞击”。它动摇了文明和信仰的基础。
正因此,“奥斯维辛”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经由人们从哲学、神学、历史、政治、伦理、艺术和美学等方面所做出的重新审视和追问,它不仅成为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象征,而且伴随着人们对一切集权主义、对专制程序、对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对工业文明和种族、信仰问题的思索和批判。可以说,正是伴随着这种追问,“奥斯维辛”照亮了人们长久以来所盲目忍受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策兰的作品在世界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来看策兰的这首诗: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正午喝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蛇他写
他写道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他写着步出门外而群星照耀着他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狼狗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犹太人在地上让他们掘个坟墓
他命令我们开始表演跳舞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喝正午喝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蛇他写
他写道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我们在风中掘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他叫道朝地里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你们另一些唱呀表演呀
他抓起腰带上的枪他挥舞着它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用你们的铁锹你们
另一些继续给我跳舞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正午喝早上喝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你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他玩着蛇
他叫道把死亡演奏得更甜蜜些死亡是从德国来的大师
他叫道更低沉一些拉你们的琴然后你们就会化为烟雾升向空中
然后在云彩里你们就有一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正午喝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我们在傍晚喝我们在早上喝我们喝你
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他用子弹射你他射得很准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
他派出他的狼狗扑向我们他赠给我们一个空中的坟墓
他玩着蛇做着美梦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王家新译)
据传记材料,策兰这首诗写于1945年前后,最初发表时为《死亡探戈》,后被定为《死亡赋格》。这一改动意义重大,它不仅把纳粹集中营里的屠杀与赋格音乐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与赋格艺术的大师、德国文化的象征巴赫联系了起来(“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因而对读者首先就产生了一种惊骇作用。
“死亡赋格”(“Todeduge”)为策兰自造的复合词,即把“死亡”(“todes”)和“赋格”(“fuge”)拼在一起,其间不加任何语法关系。诗人使这两个词相互对抗,又相互属于,从而再也不可分割。和这种词语的并置相关,《死亡赋格》整首诗在语言形式上也比较特别,即不“断句”,虽然这给阅读带来了难度,却有了一种音乐般的层层递进的冲击力。
诗的第一句就震动人心:“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这一句在后来反复出现,有规则地变化,成为诗中的叠句。令人惊异的是“黑色牛奶”这个隐喻。说别的事物是黑色的人们不会吃惊(策兰早期就写有《黑色雪片》一诗),但说奶是黑色的,这就成大问题了。这不仅因为奶是洁白的,更重要的是奶是生命之源的象征。但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它却变成了黑色的毒汁!这真是令人惊骇。它所引起的,不仅是对纳粹的控诉,还从更深处动摇了人们对生存基础、对文明的信念。因而“黑色牛奶”具有了更深广的生存本体论的意味。从策兰的一生来看,他都生活在“黑色牛奶”的诅咒之下。
“牛奶”是怎样变成“黑色”的,或者说文明是怎样反过来成为生命的敌人?这一切都让人不能不去追问。
回到“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这句诗上,它不仅是一个悖论,而且在后来反复出现时奇特的时间顺序也值得留意:“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在正午喝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这里不仅有时问的颠倒,按照有的研究者的提示,这里面还有着《旧约·创世纪》的反响:“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那里还有傍晚,还有早
上:第一日”。而策兰对之的模仿可谓意味深长。这种模仿使“奥斯维辛”与一个神示的世界相对照,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震撼力。这“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正午喝,在夜里喝,“我们喝呀我们喝”!这就是神的惩罚吗?
我们再来看诗中对赋格艺术手段的运用。赋格音乐一般由数个音组成的小动机胚胎成主题,朝各个方向发展、转化,直到内容充足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它运用对位技法,使各部分并列呈示,相应发展。巴赫的赋格音乐具有卓越非凡的结构技巧,并充溢着神性的光辉。它构成了欧洲古典音乐的一个高峰。而策兰的《死亡赋格》第一、二、四、六段都以“清晨的黑色牛奶……”开头,不断重新展开母题,并进行变奏,形成了富有冲击力的音乐节奏;此外,诗中还运用了“地上”与“空中”、“金色头发”与“灰色头发”的多种对位,到后来“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也一再地插入进来。一并形成了一个艺术整体,层层递进而又充满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读《死亡赋格》,真感到像叶芝所说的“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说《死亡赋格》有一种“可怕的美”,一是指死亡集中营里那超乎一切语言表达的痛苦和恐怖居然被转化成了音乐和诗!一是指它在文明批判上的“杀伤力”:它以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对已被纳粹所毒化了的德国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质询和“颠覆”!巴赫的音乐美妙吗?当然。但在纳粹集中营里。它居然成了死亡和种族灭绝的“甜蜜”的伴奏!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惊的么?
赋格音乐最主要的技法是对位法,《死亡赋格》中最重要的对位即是“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与“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玛格丽特,这不是一般的名字,是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歌德《浮士德》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苏拉米斯,在《圣经》和希伯莱歌曲中多次出现,她成为犹太民族的某种象征。需要注意的是,在原诗中,策兰不是用“grau”(灰色)来形容苏拉米斯的头发,而是用“aschen”(灰,灰烬,遗骸,英文为“aschenes”)。这一下子使人们想到纳粹集中营那冒着滚滚浓烟的焚尸炉,也使人想到格林童话中那位被继母驱使,终日与煤灰为伴的“aschens”即“灰姑娘”!
“aschen”这个词的运用,本身就含着极大的悲痛。诗的重点也在于玛格丽特与苏拉米斯的“头发”,策兰要强调要呈现的,正是这两种头发的对位。诗人着意要把两种头发作为两个种族、两种命运的象征。与此相对应,诗中的“他”和“我们”也都是在对这种头发进行“抒情”和感叹,“他写到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这里的“抒情主体”是集中营里的纳粹看管,“他”拥有一双可怕的蓝色眼睛和一个种族迫害狂的全部邪恶本性。但这并不妨碍他像一个诗人那样“抒情”,他抒的是什么情呢——“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这里不仅有令人肉麻的罗曼谛克,在对“金色头发”的咏叹里,还有着一种纳粹式的种族自我膜拜。他们所干的一切,就是要建立这个神话!
正因为如此,两种头发的对位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我们在风中掘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这里的“抒情主体”变成了“我们”——被迫喝着致命的黑色牛奶,被迫自己为自己掘墓,承受着暴虐和戏耍而为自身命运心酸、悲痛的“我们”!从这里开始的“对位”一下子拓展了诗的空间,呈现了诗的主题,使两种头发即两种命运相映衬,读来令人心碎。策兰就这样通过赋格音乐的对位手法,不仅艺术地再现了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也不仅对纳粹的邪恶本质进行了控诉和暴露,而且将上帝也无法回答的种族问题提到了上帝面前,因而具有了更深刻悲怆的震撼力。诗的最后,又回到了赋格艺术的对位性呈示: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在诗中交替贯串出现的,到最后并行呈现了。这种并列句法,这种金色头发与灰色头发的相互映照,使人似乎感到了某种“共存”甚或“重归言好”的可能,但也将这两者的界线和对峙更尖锐地呈现了出来。这种并置,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策兰诗歌的译者和研究者费尔斯蒂纳用一种悖论的方式所表述,是“一个不调和的和弦”。它的艺术表现到了它的极限。所以说诗的最后将上帝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提到了上帝面前。
但全诗最后的重心却落在了“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这一句上,诗人以此意犹未尽地结束了全诗。苏拉米斯,带着一头灰烬色头发的苏拉米斯,象征着被德国的死亡大师不可抹掉的一切,在沉默中永远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策兰在其据说是与阿多诺进行想象性对话的散文《山中话语》中有这样的句子:“拐杖沉默,石头沉默,然而,那沉默不是沉默”。(见王家新、芮虎译《保罗·策兰诗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的确,那沉默不是沉默。策兰这首诗的最后,或者说他一生的写作,就写作于这种如他自己所说的“回答的沉默”(the silence of an-swers)里。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的来信。她的信使我看到了策兰诗背后那么深远的犹太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背景和神秘的精神基因。她在信中谈到《旧约》中这样的记载: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被迫在河边唱起《锡安之歌》给征服者作乐,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因此她说她在读《死亡赋格》的时候,“巴比伦之辱”就在起一种“同声作用”,“甚至那把挂在柳树上的琴也返回了德国的上空……”
的确,那把“琴”神秘地返回了德国的天空——这就是策兰的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100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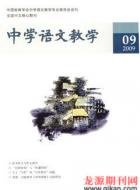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