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5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5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张岱号陶庵,晚明“小品圣手”。别样的人生经历,倜傥不羁的叛逆个性,使其小品文一扫传统散文“微言大义”的沉郁,转而张扬个性解放,参悟生命终极。其文体自由,抒写性灵。《湖心亭赏雪》就宛如一幅空灵简雅、冰雪剔透的文人画。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先从听觉渲染了造化的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又从视觉渲染了造化的纯。一个万籁俱寂、白茫茫的纯粹世界,天高地迥,“上下一白”,借造化之手,将尘世的喧嚣、尘世的华彩乃至尘世的念想化为洁白的纯粹。于是,宇宙骤然空阔,“余”的精魂寄托于一叶小舟,在这个静止、纯粹的世界上飘荡。大自然是一幅画,而这幅画契合了文人情怀。叫人想到了讲求“简”“雅”的明清文人画:物我为一,心手相忘,入画景致似乎毫不在意,偶然得之,随心赋形,自然而然。你看,这“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超越自然,赋为心象,视角高远,随心移换。这个静止、纯粹的世界里仅存的几点痕迹。全被我飘移于天际的精魂俯瞰得这样渺小,渺小到几乎微不足道!于是,这世界空空洞洞,杳杳冥冥,一念没有,一丝不沾。好一个空灵澄澈、天长水远的阔达境界!
“长堤一痕”,痕是名词,有轻渺、疏淡的特点,如同宣纸上一抹轻微的飞白。这可是横贯西湖的大堤啊,怎么就变成了一抹轻微的飞白了呢?怎样才能把充盈视野的庞然大物微缩?那只有拉高视角到高空俯瞰。而作者明明在舟中啊。那只能把心放飞到高空,让自己的精魂在冥冥青空俯瞰。是什么让作者“魂不守舍”?或许是一种繁华过后的过眼皆空,或许是一种掩藏极深不忍思虑的深深的痛。
“亭为一点”。点也是名词,像画纸上不入眼的一滴遗墨。亭子本应是立体三维的,却微缩成了画纸上的一点。这种视觉效果,是雪野空阔的写实,更是一种虚幻的心象。对景致的这种微缩处理突出了造化的“空”,这个“空”字正是作者内在精神的外化。
“舟为一芥”,芥也是名词。随心赋形,将人智能的工具幻化为造化最卑微的存在。在造化的阔达无垠里,人的智能所造就的一切,都如草芥一般微不足道。
“人为两三粒”,超越了人类自傲的认知标准,视人与造化万物无异。这心灵需要距离尘世多远才能把人拟物微缩到这般?而此刻作者明明在舟中啊,显然,此时的作者不是用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而是灵魂飘举,精骛八极,绝尘脱俗了。
这些数量摹状,好似一个空灵的心里仅存的几点“杂尘”,是对尘世仅存的几缕惦念;或者正是用这几点微小的“杂尘”来反衬了宇宙的阔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陶庵公着力营造的这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境界是否回响着作者灵魂最深处的某种声音?如果杜甫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还飘飞在世俗的天空,那么陶庵公是绝尘脱俗了:这里没有“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尘世之乐,也没有“雁落平沙,霞铺江上”的人烟鼎盛,人世的踪影几乎被这三天大雪遮蔽得无影无踪。那么,这种绝尘脱俗是一种繁华过后的过眼皆空,还是灵魂里一种掩藏极深不忍思虑的深深的痛?这一切只有陶庵公自己知道了。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陶庵公是一个不爱表白的人,他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新鲜生动的摹状,我们从这些生动的摹状中快乐地体验其中的况味。美国诗人史蒂文森说:“诗毕竟不是思想概念。它必得是自然的启示。概念是人为的,直觉是本质的。”我们从陶庵公对自然个性化的直觉中。个性化地体验着直觉背后的本质。
我们再体会一下亭中饮酒与这段数量词摹状的关系。雪地铺毡而坐,烧酒对饮,有此逸志者必雅士。然而,却不一定人得陶庵公的法眼,这人间的烟火对于陶庵公清净的心境甚至是一种叨扰和污染。有动作摹状词为证:面对二人的“大喜”,沉浸于神游之中的陶庵公却不是亦大喜。欣然入座。注意“拉余同饮”的“拉”字和“强饮三大白”的“强”字,这两个动作摹状与二人“大喜”之情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扫兴、勉强之态跃然纸上。一厢是没心没肺故弄风雅的世俗之乐。一厢是深沉蕴藉超凡脱俗的精神漫游。舟子说“更有痴似相公者”,其实他永远不可能知道相公的“真痴”!
整篇小品就是陶庵公绘就的一幅简雅的文人画,取义禅宗,空灵澄澈。大雪是画的主体:让造化简单、纯粹,让人的心简单、纯粹。于是这一组数量词摹状就是画家飘逸的勾勒、点染。这种高远微缩的处理,是一种心象的写照。这就是文人画的简和雅。文人画大多以造化为主体。人的活动只是点缀。至于这幅画的“亭中对饮”,虽是雅士风流,却至多是对陶庵公心象的一个反衬。
张岱这篇洋溢着冰雪之气的小品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庄子,灵魂的大鹏飘举九天,空灵自由。在今天这个心灵的翅膀难以承载物质之重的时代,个性化地体验张岱这篇山水小品,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提升。
(山东省青岛开发区一中 266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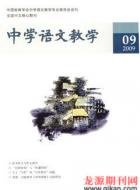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