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40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40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杨宝生《“植杖”释义勘正》(《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7期,以下简称《勘正》)认为此“杖”不是“手杖”而是“犁杖”。这一“勘正”其实是以正为误,不能成立。
首先,释“杖”为“犁杖”,违背语言规律。
《归去来兮辞》“或植杖而耘耔”是用典,唐代李善《文选》注早已指明出处:“《论语》曰:‘植其杖而耘。’《毛诗》曰:‘或耘或耔。’”《勘正》所引“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此据四部丛刊本),是苏轼针对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而发。“耦耕”也是用典。也出自《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植杖”源出《论语》。《论语》中“杖”共见4次,不外乎汉代崔瑗《杖铭》所说的“杖”(“乘危履险,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强”):《乡党》“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而《微子》中“以杖荷蓧”的丈人继而“植其杖而芸”,“杖”当然不会由“手杖”变成“犁杖”。
“犁杖”不见于《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标示“<方>”,表明这是个方言词。根据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5525页,中华书局1999年),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称“犁”为“犁杖”。从李准《黄河东流去》到陈忠实《白鹿原》,都可见这一称呼:刘绍棠发表于《河北文艺》1951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标题就叫《新式犁杖》。《勘正》说“犁杖在犁地之时”“犁杖耕耘禾垄”“用犁杖于禾垄中耕耘”“用犁杖为青苗除草培土”,显然也是指称犁。请注意,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固然称“犁”为“犁杖”,但是任何方言都没有把“杖”称作“犁”或把“犁”称作“杖”的。也就是说:犁杖:犁≠杖。可是《勘正》给出的等式却是:杖:犁杖:犁,竟然把从《论语》到《归去来兮辞》的“杖”用一个方言词“犁杖”偷换为“犁”了!因此。所谓“‘杖’在古文中……也可指‘犁杖’”,完全不能成立。
“杖”指“犁杖”的原因,《勘正》认为:“犁杖在犁地之时,其下端犁铧须着地入土,其上端犁把儿须以一手持之,故曰‘杖’。正如段玉裁所言:“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如果这是说“杖”由手持的犁把儿进而代指全体,那也只可能是在某些方言区,而不是古汉语中。因为犁的部位古代有专名,唐陆龟蒙《耒耜经》:“前如捏而樱者日辕,后如柄而乔者曰梢。……辕之后末曰梢。中在手,所以执耕者也。”犁把儿手握的部位,叫做“中”;“中”往下的是“犁梢”,都不叫做“杖”。
其次,所说古人关于“耘”与“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更为重要的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违背古汉语实际。
《勘正》说:“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用犁杖于禾垄中耕耘之时,其犁铧在土壤中行进过程中,既犁翻掉其中的杂草,又将翻拥起的土壤,拥培在禾苗的根部。为了增强培土的效果,还常常在犁铧上部增装拥土之物。正所谓一功二得。”然而,《归去来兮辞》“植杖”来自《论语》“植其杖”,这种“在犁铧上部增装拥土之物”——“犁壁(犁镜)”,《论语》成书的战国时期尚未出现。据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西汉时发明了犁壁(犁镜),由犁壁和犁铧构成的弯曲面能将耕起的土垡破碎和翻转过去。汉代犁壁的形制有向一侧翻土的鞍形壁和向两侧翻土的菱形壁两类。不过犁壁出土的地区有限,而且在汉画像石中没有见过它,说明其使用尚未普及”,而战国铁犁“只能在地面划开一道沟,不能翻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11页)。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也指出战国铁犁“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作垄”(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古人如何训释“耘”与“耔”的?《诗经·小雅·甫田》“或耘或耔”,毛亨传:“耘,除草也。耔,雝本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耘,音芸,本又作芸。耔,壅禾根也。”《勘正》所引述的古人“耘”“耔”训释与此相同:《诗经》朱熹注“耘,去田间草也”,《玉篇·耒部》“耔,壅禾本也”。《荀子·王制》《墨子·三辩》都说“春耕夏耘”,播下的种籽出苗后,杂草亦生,除草成为急务。除草(耘)和培土(耔)往往结合进行,完成这两项农作的主要工具是“便于在庄稼地的行垄间除草、中耕、培土”的铁锄,“春秋战国时代中耕用的锄类工具,不但材料改用铁质,品种也显著增加,这反映当时劳动人民已十分注意到中耕、除草、间苗等项工作的技术要求,因而创制出多种不同性质的锄具,以适应精耕细作提高田间管理水平的需要”(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除草(耘)和培土(耔)这个精细活,“能将耕起的土垡破碎和翻转过去”的西汉铁犁尚且完成不了。说古人关于“耘”与“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耘耔’一词准确全面地描述了‘犁杖’耕耘的双重作用”,这就不仅把原本不同的“耕”和“耘”“耔”混为一谈,而且用前者取代了后者。
再看人教社高中《语文》第二册(必修本)课本注释,其实不误:“有时在田里除草培苗。植杖,把手杖立在一边,一说倚着手杖。耘,除草。耔,培苗。”《勘正》认为无论将“植杖”释为“把手杖立在一边”,还是“倚着手杖”,与除草培苗的行为放在一起。都是难以讲通的。为消除这种疑虑,我们认为有必要再补充说明:之所以解释为“有时把手杖立在一边在田里除草培苗”,是因为除草、培土的农具是铁锄,锄又作鉏,装有长柄,是一种站着除草的农具;耨是一种短柄锄,是蹲着用一只手执柄操作的。(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站着双手握锄(钮),无法再倚手杖;蹲着一手执耨,重心下移,相对稳定,则不必倚手杖,所以要把手杖立在一边。况且汉石经《论语》作“置其杖而耘”,“置”就是放置。《尚书·金縢》:“植璧秉圭。”郑玄注:“植,古置字。”之所以有“一说”解释为“有时倚着手杖在田里除草培苗”,是因为水稻的中耕方式与旱田作物有所不同。据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水田耘耔,农夫拄杖支撑身体,双脚交替着将杂草踩进泥内。此法在汉代名鹭,《说文·癶部》:“癹,以足蹋夷草。”用脚(足)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则植杖正所以耘”(江永《群经补义》卷四)。从《论语·微子》丈人“杀鸡为黍而食之”——用自产的“黍”招待子路,可推测旱田耕作的可能性较大。许倬云《两周农作技术》:“由于黍的耐旱能力强,而味道也较佳。因此在商代以来成为中国普遍的作物……稻大约在古代北方的食粮供应比重上不及黍稷普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4页)齐思和《毛诗谷名考》:“自古以来长江流域是产稻的中心。不过古代华北产稻的区域,远较现今为广。现在不产稻子的地方,在古代是以宜稻著名的,这是很可注意的事。但是华北区域究竟是以吃黍、稷为主的,稻、粱即在贵族侯王也是特别的珍品。”(《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联系《微子》中丈人还说到“五谷”(从郑玄、赵岐、高诱、王逸到金鹗均以为“五谷”包括稻)、《阳货》中孔子说过“食夫稻”,因而不能完全排除“植其杖而芸”在稻田的可能,所以从《论语》“植其杖而芸”到《归去来兮辞》“或植杖而耘耔”,“一说”仍以不取消为宜。“植”的本义是“户植”(《说文·木部》),“户植”是直立之木(段注),引申为树立、竖立。所以朱熹注:“植,立也。”立杖,从不使用角度说是置之,从使用角度说则犹云拄杖、倚杖。
(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310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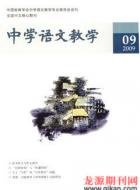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