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3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9期
ID: 353733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诗歌是用“愁”堆砌起来的,离别之愁,相思之愁,怀乡之愁,亡国之愁,还有说不清其实说得清的“闲愁”。翻开书卷,它会绵延而来,弥漫天地,哀伤处令人心悸,深沉处让人回味。这样的诗句。从《诗经》到唐宋诗词,我们可以信手拈来,“出自北门,忧心殷殷”(《邶风·北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王昌龄的《闺怨》),“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之十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横塘路》)然而,每位诗人的愁与如何表现这份愁是“不一样”的。在集中学习古代诗词的时候,我们会每天面对这么多愁,如果读不出“不一样”,就会走向疲惫甚至麻木;同时,课程学习目标中也有个“说好处”的要求(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参考书》第1页),这个“好处”应该包括一首诗的“不一样”。
就一首诗而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有生命的,有自己的灵魂,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留下的诗词必定有它的特别之处。同题材的诗词,不同作者寄寓的具体情感与采用的表现方式自然不同,而同一个作者表现同一题材或同一对象也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语言、手法,意象、意境,思想、情感,都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有时可能是一个句子,有些诗中的多数句子都很平庸,但其中一个句子就能点铁成金,使整首诗熠熠生辉。韩愈《左迁至蓝关》、柳宗元《登柳州城楼》,都是贬谪诗,编在一个专题里,可是,不仅情感有别,单是抒情方式上就有很大差异。柳诗完全借山水景物委婉曲折地抒情,韩诗既即景抒情,也直叙其事,直抒胸臆。柳宗元的永州诗和柳州诗同为贬谪诗,意象特征与情感也有明显不同。永州诗山水优美,意象清静,表现了心理上的不平静与政治上毫不畏惧的执著。柳州诗中的山水却是奇崛险怪,情感上则凄婉哀绝。
冯延巳的《鹊踏枝》(在第七专题)与辛弃疾的《丑奴儿》(在第十二专题)都写“闲愁”,怎样让学生读出它们的不同呢?
师:冯延巳《鹊踏枝》的显著特点是写出了闲愁的“连续性”。同学们认为“连续性”表现在哪里呢?
生1:老师,什么是“闲愁”?
生2:“闲愁”就是“闲情”,是一种无端涌起的愁思。
师:说得对,作者在“闲情”后点出了“惆怅”,下片又明确点出“闲情”就是“愁”。它是一种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迷惘情意。
生3:“连续”就是绵延不断,我认为末尾一句是最能体现的。“独立”写寂寞,“小桥”更突出了形单影只。“风满袖”写凄凉,“满”字突出了寒风的强烈。“人归后”写“独立”时间之长,“平林新月”写夜色渐起,渲染了寂静的氛围;同时,“月”本身就是思念的意象,对月越久,愁就越难以排遣。这样一层层地写出了“闲情”的苦、深、久。(生掌声)
师:评点得好。词句意境优美,小桥寒风,平林新月。寂静、凄迷、清冷。人物也有雕塑造型之美,主人公独立小桥,一任晚风吹拂,似在翘首等待,又仿佛在俯首沉思,韵味无穷。这份愁被写得回环萦绕,拂之不去。但是,这更多的是体味愁的程度,而不是“连续”呀!
生4:老师,这愁是从白天来的,从白天到夜晚一直在愁,还不“连续”吗?(师:何以见得?)“河畔青芜堤上柳”的颜色鲜明,应该是白天。
生5:这一句本身就有“连续”。“青芜”写绿遍天涯的无穷草色。“柳”更是万丝飘拂,隐含了愁的绵远纤柔,况且这草色又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年年河畔草青,年年堤边柳绿,愁情也就年年无尽无穷!紧接着又用“何事”疑问,更强烈了。
师:既然是“年年有”的“愁”,为什么又说是“新”呢?
生6:词开端已经说过“闲情抛弃久”的话,经过一段“抛弃”的挣扎又重新复苏起来,并且不能自解。
两首词放在一起学习是一种比较,从方式上看并无新意,但它体现了教师处理教学文本的思路:重组。这种重组意味着专题之间可以也应该打通,因为专题只是以时序编排的。虽然一个专题体现了一个阶段的时代风貌。然而机械地按时序教学,只是让学生对一个阶段建立整体认识,结果很可能会造成单篇的累加。回到必修的老路,诗歌本身的元素也无法体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篇教学就不能体现诗词本身的元素,只是文本重组会突出这种鉴赏角度,进而突出选修学习重角度的特性。重组是有难度的,需要教师对选修教材的内容有一个整体把握,找出最佳的组合角度。《鹊踏枝》与《丑奴儿》都写“闲愁”,《鹊踏枝》有明显的“连续性”,《丑奴儿》上下两片一气用了三个“愁”字,足见愁之多之密。它们分属两个专题,两个时代,作家的风格也不同,并且一篇是必读,一篇是自读。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比较容易看出各自的个性特征。本节课是从单篇学习开始的,这一做法还启示我们,对于难度较大的诗词,组合学习也应从单篇开始,不宜直接进入统整性的研习。
课堂第一个问题指向《鹊踏枝》的整体感知,要求说出“连续性”的表现,思维难度较大,隐含了理清情感脉络的要求。这是个“真”问题,有质量的问题,基于课前的学习基础,学生应该可以回答,但课堂肯定会出现意外,这里就出现了两次。当意外出现的时候,教师巧妙地将它转化成了有利的学习因素。面对“连续性”的问题,学生问出了什么是“闲情”,这表明他不明白字面的意义,不理解情感的内涵。教师点拨了词义,同时借此机会指出了“闲情”“惆怅”“新愁”在词中的位置,这就初步暗示了情感的脉络。为进一步讨论作了铺垫。按照常理,“连续性”应该是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过程,可学生就从最后一句开始,这又是个意外。这说明他喜欢这一句并且理解较深,自我学习的时候就是评点的此旬,但他没有扣住课堂问题。教师的两问顺势而为,极为巧妙,既充分品味了这个重点句子,又使问题回到“连续性”上,极为自然地引导学生逐步向上文反推。
师:看来,主人公前面就在“闲愁”中挣扎了,她是如何挣扎的呢?
生7:“抛弃”是有意寻求摆脱,“久”字既是时间长,更是努力的表现,“谁道”是反问语气,原以为可以做到,谁知竟然未能做到。说明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全落空了。
生8:糟糕的是,这种情况年年、天天都在重复,后面的“每”“还”“依旧”“日日”字字沉重。无奈之下只好借酒浇愁,听之任之。
师:其实,这份无奈中有一意承担负荷的意思。看来,词的“连续性”是层层加深的,上片说“日日”,下片说“年年”,层层推进又回环往复。那么,《丑奴儿》也是如此吗?(一生再读)
生9:不一样,上片说少年“不知愁”。下片写现在知愁。而且两个“愁”也不同,上片是“闲愁”,下片是关心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而且这个“闲”好像和《鹊踏枝》的“闲”有些不一样。
师:是有些不一样,我们后面继续讨论。既然
情感的内涵与表现不同。写法是不是也不同呢?课本就要求我们思考《鹊踏枝》是如何高明地写出来的。
生10:《丑奴儿》用对比,以昔衬今,以无写有;运用叠句,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有回环之美;情景描述少,主要是直抒胸臆。
生11:《鹊踏枝》描述情景多。情和景相交融,而且虚虚实实的;还有就是层进手法。(师:层进是显著特点,但重视意境的营造使得词意韵味悠远。)
生12:其实也是比兴,情景相生,景又有象征意味。
组合学习是要有主次先后的。《鹊踏枝》被明显放置在主要位置,第一阶段的学习完全是一种细读,不仅对每个句子的情感内涵进行了玩味。还突出重点句子,理清了各个句子与上下片之间的关系。《丑奴儿》则一带而过,不作停留。这样的处理符合各自在专题中的位置,《鹊踏枝》是必读课文、重点文本,《丑奴儿》是自读课文、辅助文本。两者难度也不一样,《丑奴儿》虽说有“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态,但议论的色彩浓,外显的语言平易浅显,表现的方式一眼就能判断;《鹊踏枝》则是不同情境的结合,有跳跃性,意象的内蕴丰富,存在多义理解,表现方式更是它独特性的体现,是难点所在。如果我们在研习中采用其他组合方式,比如难度都比较大的诗词组合在一起,比如同专题并且都是必读的诗词组合在一起,也应分出主次。这不是因为课堂时间的限制,而是为了突出课堂研习的重点角度。
与情感的连续性一样,课堂也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为由浅入深的层次。课本要求思考的问题是怎样高明地写出连续性的,课堂先读出的则是连续性而不是“怎样写”。这个定位是恰当的,理清了情感脉络也就读懂了词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讨论写法的高明是尊重学生认知规律的做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铺垫。教师还始终注意为连续的推进埋下伏笔。学生认为“敢辞”是“听之任之”的时候,教师突然插进一句:其实是“一意承担负荷”,但又不作解释。学生提出两个“闲”有些不一样是很敏锐的,教师也没有马上展开。一方面因为与当前的主要任务有冲突,为使课堂主线清楚,应不枝不蔓;另一方面问题的难度较大,需要集中探讨,所以教师只是交待“后面继续”。事实上,所有这些铺垫完成后,后面的课堂便进入到深度品味的阶段,感受情感的复杂,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挖掘造成不一样的多重原因。
师:两个“闲”有些不一样,谁能说说清楚呢?
生13:辛弃疾的“闲”就是少年人的多愁善感,其实没什么愁,把自己想得很寂寞,模仿前人。无愁找愁。后面的哀愁是削职闲居报国无门的悲凉,当然还有怨愤。
生14:冯延巳失恋了吧!(生全体笑。师:有道理的,爱情的苦闷往往让人欲罢不能,虽然无奈却也决意担当。但这人不一定是冯延巳,可以说成抒情主人公。)
生15:可能是对国势衰微的忧虑,或是追求理想的深挚情怀。以美人香草、闺中愁情表现忧患意识是文人诗歌中的传统。从屈原就开始了。
师:冯延巳生活在中主李璟时期,这个时期南唐较为繁盛安定,冯延巳也仕途亨通。没理由忧虑呀!
生16:我觉得是春天怀念亲人,闺怨诗中很多的。
生17:说成闺怨也太简单了。这份“闲情”好像有点没来由,每到春天自然来了。其实怀人倒也未必在春天,秋天不行吗?
生18:我读过不少冯延巳的词,好像他是不愿说明白。比如,“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采桑子》)主人公是男是女很难判别。“旧愁新恨知多少。目断遥天。”(《采桑子》)哪些旧愁新恨?说不清。
师:我比较赞同你的看法。这份愁其实没有具体所指,缥缈朦胧,还让人感到一丝寒意,所以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不确定的。会唱《最近比较烦》这首歌吗?
(生兴奋,有的轻声唱,有的轻声说歌词。)
师:看来,现代人与古人一样,日日年年也有新的人生郁闷的,虽然郁闷愁苦的原因不一样,但郁闷忧虑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不招自来。
生19:我明白了,他所写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事,而是一种人生中常有的、说不清的忧愁苦闷。一种若即若离的人生忧患意识。
(师:请自由诵读,《鹊踏枝》要读出孤单苦闷,《丑奴儿》要读出悲凉怨愤)
真正的不一样其实是在不一样的背后,只找出显性的不一样不是真正找出了不一样,或者说学生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不一样。这个“真正的不一样”就是时世与作者的人生。如果是情感有不同,时世的影响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尤为重要,这样我们就必须知人论世。本课的设计者是非常明白个中三昧的。课前学习时已经布置了相应的学习任务,课堂上抓住前一阶段学生的问题进行生发,实际就是要借助课前的知识积累引导学生向深处开掘,在弄清愁产生的原因之后,准确理解它的具体内涵。当然,不经意地结合前面的问题引起讨论。体现了课堂结构的严谨与教学的机智。学生对辛弃疾是熟悉的。初中阶段学过他的作品,高中又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因而很快就能判断哀愁的实质是报国无门,写少年愁只是反衬而已。对冯延巳,学生要生疏些,理解词意原本是可以结合作者人生的,但是冯氏的人生与词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能用于否定,不能用于肯定,所以教师直接插进去介绍只是为了否定学生的某个看法,把学生带出误区,逐步逼近词的真意。
冯延巳闲愁的深沉内涵已经超过了学生人生经验的积累,超过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因为学生正处在“不识愁滋味”的年龄,不可能一下子悟到这种与生俱来的人生忧患,即使是成年人也未必就能马上理解。于是,教师另辟蹊径,迂回接近,使学生渐渐走了进去。一是让学生尽情表达自己的领悟。失恋的说法引起了哄笑。说明多数学生朦胧感觉到词里别有寄托。即使只读到这个层面,也没有什么错,爱的哀婉缠绵也是一种美。忧虑国事、闺怨怀人,也都是可能的合理解读。一步步的多角度理解让学生进入到“愤悱”状态,自然出现了深度追问的契机,文本的真意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二是流行歌曲的引入。表面看有些另类。恰恰是教师的匠心所在,因为联系学生熟悉并喜爱的事物,就化深为浅了。这其实也是借助学生已有的人生经验,即使不是他亲历的。歌词明白道出了人生的无奈,比如,“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人生总有远的近的麻烦”,当学生口诵这些歌词的时候,就会恍然大悟,至少与冯延巳不再隔膜了。
从诗词的元素上说,本节课是从情感切入的,在读出情感不一样的同时,读出了表现形式的不一样与背景的不一样,并且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较之必修,选修的诗词鉴赏显然不需要面面俱到,从某一个角度深度研习即可。教学文本是以专题呈现的,12个专题各自有它的共同特征,或内容,或风格。比如中唐诗是“创新求变”,北宋词是“格高韵远”。研习深度固然体现在知晓它的总体特征,但总体特征建立在具体诗词的独特性基础上,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个研习角度。这个角度可以是具体的“这一个”有什么不一样,还可以是共性的特征,这取决于教材尤其是教师的意图。比如《鹊踏枝》的独特在于闲愁的“连续性”,同时它的意境又极为优美,如果设计了深度品味意境之美的任务。未必就从情感切入。
本课采用了高低搭配的方式重组文本,是不同作家的跨专题组合。其实文本重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要有联系的意识,读出“不一样”的意识。不同时段的作家作品可以组合,同一作家可以组合,而且更有价值,更易于读出具体诗词的个性。如果与同时代(同专题)的其他词作组合同样可以读出不一样。比如,同为写愁,温庭筠词表现的是爱情的苦闷,是一种人类共通的心绪,具有普泛化的特征,但苦闷是确定的、明白的:李煜词则由个人的痛苦进而感悟到人生痛苦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痛苦的内涵性质也是确定的。而冯延巳“闲愁”的不确定性与连续性是其词作的基本特征。他把忧愁表现得更深更广,写出了命运的神秘和不可捉摸,人生愁苦的持久性,这给他的词增添了几分苍凉。这一特征使得他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为独特的一个,也凭借这一点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将三者组合。各自的个性同样会得到凸显。
(江苏省南京市第五中学 21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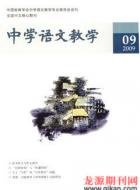
- 及早知道笔调事 / 韩石山
- “描述”与“论说”辨 / 刘占泉
- 从高考作文命题改革看中学作文教学思想转变 / 张伟明
- 阅读陌生感的再造有利于阅读终身感的培养 / 周仁良
- 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与思考 / 蒋 华
- “同课异构”与“异课同构” / 李 蕾 宋 悦 李卫东 王彤彦 仇 强
- 学生何以“故纸堆里讨生活”? / 王栋生
- 关于“写作”和“写作教学”问题 / 李海林 荣维东
- 一次对命运的突围 / 张 兰
- 与文本对话,是实现教学对话的前提 / 宋桂奇
- 不一样的“闲愁” / 蔡建明
- 从意象间的关系看《乡愁》的主题 / 何元俭 陶 健
- 一幅空灵简雅的文人画 / 张存平
-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 王家新
- 李商隐《锦瑟》通解 / 王俊鸣
-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 彭 献
- 《兰亭集序》教学设计 / 占淑红
- 再论《论语》和《归去来兮辞》的“植杖” / 颜春峰 汪少华
- 《孔雀东南飞》札记二则 / 郑丽萍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王大绩
- 作文,每个选手的奥运 / 周京昱
- 夯实基础 强化应用 / 安徽省初中语文学业考试评价组
- 平实素朴,回归根本 / 苏盛葵
- 语文课要上得“实”一些 / 郑晓龙 任海霞 谢政满 李朝晖 张怀民
- 一路走来的朋友 / 黄厚江
- 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 / 陈钟樑
- 香港、大陆教材《苏州园林》比较研究 / 倪 岗
- 别具一格 另辟蹊径 / 秦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