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78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78
探析《一把尘土》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黄玉梅
摘要:我们在《一把尘土》中能够感受到作家伊夫林·沃笔下那满满的“恶意”,小说从局部到整体,在每个细微之处都散发着反讽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通过男主人公托尼的悲剧人生,经由轻描淡写的故事叙述,从女主人公布伦达背叛家庭开始,到男主人公托尼落入野蛮人的手中,作者藉由反讽这种表现手法表达了他对当时文明最深刻的控诉。
关键词:《一把尘土》 伊夫林·沃 反讽
引言
“反讽”的起源要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文学中,取“佯装的无知,虚假的谦虚”之意。而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经由各种文学理论的建立和拓展,反讽的概念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流派的创作表达形式,其内涵在不断加深,并且越来越复杂。发展至今,反讽在原本修辞学的概念基础上又获得了哲学审美层面上的扩展,同时也开始被普遍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不过作为艺术领域的一种固有属性,反讽对于作家的运用也是具有极高的要求的,它不仅要求写作者能够轻松驾驭其所选择的题材,并且要在视角上做到客观、超然和冷静。
伊夫林·沃作为英国著名的现代三大讽刺小说家之一,《一把尘土》可以说是其巅峰之作。作者在情节设置上将人性的虚伪面具撕开,裸露出当时英国社会人性的卑鄙与丑陋,我们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溢出的作者的讽刺与不屑。而且作者在小说中还建立了哥特时代的人类落入野蛮人手中的主题,展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于现代文明压迫的控诉与谴责。在语言上,伊夫林·沃将反讽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意境融入到小说创作中,通过超然的叙述,不添加任何的私人感情和主观意象,给读者留出了更多的客观思考空间,让读者从小说人物荒唐而滑稽的行为中领会极富张力的反讽语言艺术。
一、《一把尘土》中语言文字的形变
在《一把尘土》的开篇,“他干了错事又不受惩罚,这真是太荒谬了”这句话是女主角布伦达对丈夫,即小说的男主角托尼的控诉。在字面上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对于这种控诉所扮演的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似乎是在简单陈述一个已知的客观事实一样不添加任何的主观思想。但事实上,女主角的所有控诉都是其为自己的背叛而找的借口,纵观全文,我们看不到男主角托尼做了任何与表述相关的事情,而作者通过这种看似在为布伦达打抱不平,并通过叙述语言的表象和真实内涵之间的深度对比,形成语言上的反差效应,真正地将反讽的幽默语言艺术效果充分地展现出来了。
作者通过这样的反讽表现出文字的形变。也就是通过词语的精心堆砌,将实际的情景与文字自身表现出来的意思进行刻意的翻转和明显的改变。这就使得上下文的语言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荒谬,而作者就是要通过这种带有清晰痕迹的反常来使得客观事实成为笔下文字的注解,并凭借态度模糊的人物语言叙述来实现反讽的目的。[1]我们看到,事实上在上述的语言中我们是看不到作者的明确实际意图,也可以说作者在有意地隐藏他的真实想法。但是通过叙述语言文字与叙事内容之间存在的不合理,又很明显地带出了作者想表达其对小说内容的实际看法。作者以自身的思考态度作“诱饵”,促使读者依靠小说语境去实现对小说内容的寻思,并在对小说语言破译的过程中,实现作者和读者之间思维的共通。而作者也依靠这种文字的变形,使得小说从多维度呈现出形式多样的特色,进而达到别出心裁的反讽效果。
二、《一把尘土》语言中的叙事张力
在《一把尘土》的反讽叙事语言中,展现的是反讽领域内极富表现力的一种审美艺术,即为叙事张力。善与恶的对比,真与伪的互照等都是反讽形成的正反两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能够有效帮助作者建立小说世界的双维空间,文字意义形成的表象世界和真实含义形成的客观世界之间构成特殊的矛盾,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层次地去品味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结构中所隐含的深刻意义,并通过反讽的手法使两个世界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可以说,这种叙事张力不仅是反讽艺术风格的本质,更主要的是通过反讽也同时形成了语言张力的表现基础。“那时候我开始怀疑我丈夫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变。”这是布伦达的律师在布伦达的授权下捏造的对于布伦达的丈夫托尼的无情控诉。而作者在字面上通过讼词痛斥了托尼堕落的种种罪行,如果有细心的读者通读全文后,会发现其实作者在极尽恶劣的控诉中嘲讽的却是背叛了家庭的布伦达。[2]如果我们单独截取出这一段控诉的话语,在文字构筑的表象世界中,我们只会对布伦达产生同情和认可,而对托尼产生厌恶和鄙视。但是作者在进行情节设置时,将反讽的艺术表现融入到全文中,并通过某段情节与小说整体的节奏形成对比,产生巨大的张力,在既知的小说背景下,让我们看透了布伦达自私而丑陋的本质,转而对托尼产生更深刻的同情与怜惜。这种表面上指责托尼的不忠实则讽刺布伦达的堕落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的思维在多维层次上形成立体的艺术结构。
以上通过完整的情节设计和独立的场景情况,完整展现的反讽意味在文学领域被称为情景反讽。情景反讽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要考虑如何能够通过小说的整体构思与小说中独立的情景之间形成反讽效果,而不是要思考如何将反讽的语言植入小说中。所以《一把尘土》的整体反讽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伊夫林·沃在反讽思维上的超高造诣,以及在反讽手法上的高超的驾驭能力。事实上,作者并没有对小说内容给予深刻的评价,更多的是站在超然的角色领域内,实现一个作者对小说的情节的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的叙述。所以无论是好是坏,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读者去进行自我价值观的衡量,尽管我们可能会在某个节点上有了与作者相似的观点,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作者,无法准确地描述作者在下笔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三、《一把尘土》中的反差
反讽的最低层次是直接通过反向的语言陈述对客观现实进行讽刺,而在《一把尘土》中形成的反差则要更有艺术性。首先作者将情景反讽作为小说的整体结构,并将具体的细致的小说情节作为节点,打开反讽的大门,让读者能够脱离故事之外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去品味小说整体形成反差的讽刺意味。此外,小说中形成的美好幻想和残酷的客观现实之间形成了反差的沟壑,让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急剧旋转,而从中体现出的反讽意义也就一目了然。
在小说中,布伦达为了实现自己的解放,想尽一切方式促成珍妮与丈夫在一起。而可笑的是,珍妮费劲心思去引诱托尼却最终换来托尼的极度厌恶。期望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在作者幽默的语言中却发现其中的深意,让我们无法释怀地笑。布伦达与比弗这对所谓的恋人之间的爱情游戏,在布伦达渴望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去追逐现代时尚的潮流时,却发现原来比弗爱的不是她,而是她丈夫手中握着的闪烁金币。贪婪的布伦达向托尼索取高额的赡养费无果,也就意味着布伦达与比弗之间的爱情将失去唯一的纽带,布伦达一切的爱情幻想都将破灭。其中,向来对她百依百顺的托尼第一次强烈地拒绝了她的要求,也出乎布伦达的预料之外。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出乎我们意料的反差形成了整部小说的反讽基础。小说《一把尘土》的情节发展是与许多读者的想象大相径庭的,尤其是作者会将小说的情节通过并置、对比、撞击等手段实现产生矛盾的目的,更有效地将小说的反讽推向更高境地。[3]
《一把尘土》自身形成的反差造就了反讽的效果。在反讽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必须站在一正一反两个角度上对小说的结构、情节、情境等方面进行设计。而作者在小说全篇所表现出冷漠和超脱的态度,与创作时内心的炽热感性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篇优秀的反讽小说是作者能够在创作中严格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思维,在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既不让自己的内心现实冷漠,同时也不在笔下添加任何主观情感,这样的融合产生的反讽效果,能够更加全面和丰富地展现作者两种层次上的思考,使反讽更具客观性和公平性。所以在《一把尘土》的反讽语言中,反差是实现反讽的最主要的基础,也是作者在小说篇章设置中最具特色的文学思想。[4]
结语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上看,反讽小说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将会在表达形式和艺术内涵上有更深层次的展现。而伊夫林·沃笔下的《一把尘土》虽不能简单地称为是反讽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是绝对称得上是巅峰之作。[5]作者通过反讽的手法来观察社会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期盼与现实的反差为后世读者具化了一个战后破败不堪的英国社会。[4]尽管我们未曾经历,但读后却如身临其境,文中未曾有一笔一墨的批判与嘲讽,却能够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最深处的那份由来已久的对社会现状的思索。同时作者借由小说整体的情节背景设置与某个节点的情境之间的对比,深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的某些人性的丑陋面容,表达了作者对这种情况的憎恶和无奈。伊夫林·沃对反讽这门艺术的驾驭是举重若轻的,他可以站在一旁客观地看着自己的憎恶滋生,却不显现任何的主观评价,我们说写小说就像是在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随心而动、随意而生的。[6]但是作为一个反讽的小说家,作者必须能够像一个医生一样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工作,不能妄加评断,所以笔者认为世界文坛对于作者伊夫林·沃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担得起如此高度的赞誉。而通过对小说中反讽语言的分析,我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感情以及对作者所描述的社会感同身受。并且笔者认为伊夫林·沃《一把尘土》的创作思路对我国反讽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也有着深刻的探索意义和借鉴价值。语
参考文献
[1]胡春华,涂靖.情景反讽的类别及语用特征[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01).
[2]周祖亮.“反讽”的流行与误用[J].语文建设,2005(05).
[3]苗学华.讽刺在《一捧尘土》中的体现[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05).
[4]曹鸿娟.认知诗学理论下的外国文学阅读[J].语文建设,2015(23).
[5]杨静.奈保尔与伊夫林·沃的文化异同论[J].枣庄学院学报,2005(06).
[6]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J].小说评论,200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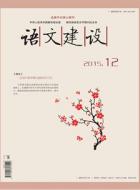
- 论写作教学模式建构的方法 / 彭小明 刘亭玉
- 语文课堂情感教学的再思考 / 赵爽 王相文
- 错位的教育何时能归位? / 张春梅
-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的概念图阅读策略培训设计 / 李艾平 王欣春
-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价值特性分析 / 刘品端
- 将情感注入学生 / 心田 牛永刚
- 浅论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渗透问题 / 叶敏
- 语文教学目标的价值诉求及有效生成 / 程颖
- 论ZHC测试与广西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结合 / 冯海英
-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目的观演变及启示 / 李文华
- 农村语文教师朗读教学能力亟待提升 / 苏洁梅
- 写作教学还可以这样教 / 王伟
- 语文学科性质观之争及滥觞追溯 / 赵东阳 王春梅
- 刍议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 张毅蕾
- 经典诵读的语文阅读教学实践性研究 / 程乔夏
- 以《平凡的世界》为视角看现状文学教育 / 雷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融合策略 / 张立英 朱敏
- 关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探讨 / 南君
- 语用课堂:为言语生命的发展奠基 / 欧加刚
- 高校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进路 / 王玲玲
- 《草原日出》生态主义叙事声音研究 / 冯平
- 论作家曼斯菲尔德小说体裁的文本创新 / 高向晔
- 海明威《老人与海》空间与叙事探析 / 郭菲 李晶
- 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叙事艺术探微 / 胡文涓
- 毕淑敏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评析 / 李艳云 李彩霞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刘翠萍
- 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虹》中的厄秀拉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形象分析 / 马义
- 哥特小说传统下的《哈利·波特》创作研究 / 蒙静
-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解析 / 王凡
- 川端康成小说中“女性救赎”主题解读 / 吴小梅
- 简·奥斯汀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比较 / 闫俊玲
- 黑色幽默与身份构建 / 杨坤 马永良
- 霍桑《红字》中的象征主义解读 / 张科
- 真实的世界:《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 / 徐晓芳
- 论《爱的牺牲》中的悲观主义爱情 / 刘俊丽
- 凯鲁亚克《孤独旅者》的文化记忆述略 / 杨昕璐
- 解读《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苦难意识的书写 / 孙艳红
- 简论《约瑟夫·安德鲁传》的艺术特色 / 潘秋阳
- 从林黛玉的“哭”探究其人生的四重悲剧 / 杨彦科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伊莉莎的心路历程解析 / 王书艳
- 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比较研究 / 毛三艳
-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学理论研究 / 辛魁鹏
- 粤语童谣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传承与发展 / 徐艳贞 何志慧
- 探析《一把尘土》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黄玉梅
- 网络媒体标题语言特点与新用词研究 / 李婧
- 华兹华斯《水仙》的诗歌语言评析 / 李丽英
- 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意象与语言隐喻 / 李月圆
- 钱钟书《围城》文学修辞语言研究 / 梁造禄
- 近十年网络语言及其使用现状分析 / 娄博 李改婷
- 认知语言学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 宋新克
-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评析 / 孙远
- 先秦汉语时间词汇系统研究 / 滕华英
- 论爱德华·萨丕尔语言与文学关系理论研究 / 王惠欣
-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评析 / 王晶
- 认知转喻视域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 邢大红
- 海明威《一天的等待》语言特色与表现手法 / 张明梅
- 雷蒙德·卡佛的文学语言观念之解读 / 胡海青
- 语言规范的预测性问题 / 杜兰兰
- 语文教学下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素养的优化路径 / 谢晓信 梁汉平
- 语文教育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研究 / 项丽娜
- 试论英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 / 马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