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69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69
凯鲁亚克《孤独旅者》的文化记忆述略
◇ 杨昕璐
摘要:《孤独旅者》是凯鲁亚克记录特殊文化记忆的自传作品,这部作品将多元的文体汇集于短篇故事之中,以立体而连续的画面形式对作者的文化记忆进行呈现。本文从作者选取的记载体裁入手,分别阐述了不同故事场景中蕴含的多元文化记忆,进而分析了文化记忆背后的文化立场。
关键词:凯鲁亚克 《孤独旅者》 文化记忆
引言
《孤独旅者》是凯鲁亚克一些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小说片段的合集,这些文字均以作者的旅行为背景展开。在小说中,凯鲁亚克的行迹遍及美国,从南部到东部海岸、西部海岸乃至遥远的西北部,甚至覆盖了墨西哥、摩洛哥、巴黎、伦敦等域外国家,他用浓墨重彩的文字将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五彩斑斓的城市一一记录下来。虽然这部作品所涵盖的内容与其名作《在路上》较为近似,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并非是在单纯地重复记录作者所经历的旅程与所见的各色自然景观,而是更多地蕴含了凯鲁亚克对多样文化的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讲,《孤独旅者》并不仅仅是凯鲁亚克的个人旅行日记,而是一本混杂的地域文化素描。从表面看,这部作品展现的是一种由一个独立的受过教育的一无所有的随意流浪的放荡者所过的生活的大杂烩,并且以旅行为主题,但其更深层的思想意韵则是作者对文化记忆这一主题的关注与反思。
一、 以自传为载体刻录的特殊文化记忆
从形式上来看,《孤独旅者》属于回忆录,从体裁来看,这部作品带有典型的自传体特征。在作品中,凯鲁亚克甚至直接使用了自己的姓名,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回忆并反思了旅行以及思考的意义。
与其代表作《在路上》有所不同,正是因为《孤独旅者》具有浓重的自传色彩,其中记录的经历与回忆便更显得真实而客观。同时,通过以自传为载体,小说也更好地反映出作者独特的思想个性变化过程,更充分并形象地呈现出作者对于传统文学精神的转变,也增强了特殊文化记忆的强大表现力,使原本生硬的文字在承载多元文学题材方面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在这部自传回忆录当中,凯鲁亚克融合了手记、日记、游记以及自省自辩等多种形式烘托自传文本的历史化和时代化及可变性、文化性特征,并在这些文化记忆当中巧妙而自然地融合了复杂而有争议的“垮掉派”的反文化议题,并用自己的实际旅行情节来提供自我解释。
虽然以旅行自传为载体,但这部作品并不单纯为生态与自然写作,其目的在于通过描绘异国形象来反观和折射美国文化和社会。毋庸置疑,对文化的记忆是凯鲁亚克旅行日记中始终不变的旨归。行走在旅途中,凯鲁亚克发现,无论路途延伸到哪里,作家的心中总会带着关乎文化的种种问题。他在反复的自我对话和回顾评价中讲述自己的现时写作、文化回忆和自我反思,得到评论界和大众的理解,进而肯定自己对传统文学的追求。而丰富的旅行游记和有着哲学意义的见解则成为证实凯鲁亚克传统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有力证据。通过在自传中将特殊的文化回忆进行对比,自传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性,大大超越了之前的小说中的印象派风格和反叛形象。因此,诸如詹姆斯·琼斯等人虽然讽刺了这部小说的垮掉派书写,却也极大地认同这部作品当中所要表达的文化记忆主题。
二、不同故事场景中蕴含的多元文化记忆
《孤独旅者》共包含五个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记录了凯鲁亚克的行迹以及他对文化景象的反思。在小说中,凯鲁亚克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寻找希望的流浪汉,将自己在现实和回忆中的不同形象进行糅合,在不同文化场景中感受不同的文化记忆。
在《码头上的无家之夜》中,凯鲁亚克进行了疯狂的“历史回转”。他先是以圣·彼得罗湾为中心描述了真切的现实生活,之后则将记忆拉回到从西向东的美国大陆中去。那些过往的简短历史片段在他的记忆中穿插着织成了希望与绝望、现实与虚幻并存的网络。在洛杉矶,及时行乐、不醉不休的加州文化令凯鲁亚克印象深刻,野蛮而叛逆的爵士乐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早已沉睡的细胞,使其血脉贲张。此外,在这个故事中,他还通过对好友丹尼在面对世界时表现出的麻木与无奈以及他从热情到愤怒的转变,向我们呈现了20世纪中叶美国机械文明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抹杀。
在《墨西哥农民》和《欧洲快意行》中,凯鲁亚克向读者呈现了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异国风情。他将墨西哥形容为一片“净土”,在这片净土之上,自然的乡村、淳朴的印第安民族纯净安详,与世无争;在法国,惊心动魄的斗牛场、虔诚与寂静的教堂、别致的自然景观、浓厚的艺术氛围令他痴迷向往。在这两个故事中,文化的对比成为记述的重心——轻松惬意、浓厚艺术气息与美国“痛苦消沉”的文化氛围形成鲜明对比。从墨西哥平和且美好的社会氛围以及法国的浪漫文化气息中,凯鲁亚克意识到:“每件事物都是完美的,世界始终弥漫着幸福的玫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幸福就在于意识到一切是一个巨大的奇异的梦。”从这一意义层面来看,凯鲁亚克所要追求的并不是故事中描绘的清晰文艺的画面,更非旅行本身,而是一种理想的、具体的美国文化形态。
从第三个故事《铁路大地》开始,凯鲁亚克又将视线转移到旧金山、船上和纽约,这些地方斗争都浓缩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具体记忆。在故事中,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表达了他对处于“钢铁文明”之下的普通民众的关注以及对各种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与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凯鲁亚克将社会文化聚焦于美国社会最底层群体并非随意而为,正是因为这类群体代表了美国最低层次的文化阶层,因此这类群体在反映美国文化时当然也最为真实。在小说中,凯鲁亚克通过散文诗般的语言对自然景观进行描述,而这恰恰与其在文中反复提及的“悲哀”劳苦的工作生活形成强烈对比,这种自然与文明的反差正代表着作者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极大差距。
在《纽约场景》中,凯鲁亚克描述了在“高楼林立,城里众声喧哗,飞短流长”的纽约的文化感受。通过对纽约的聚焦,他着重反思了美国的文化生活、知识、文学影射等等。在纽约,生活、文化都更加自由而具有活力,自由的文化氛围也给予了“垮掉派”足够的艺术空间、机会和自由来发挥自我、实现自我,在这里,他们的激情得到释放。行走于纽约,那里的酒吧、地铁、街道、报刊亭、餐厅、广场、俱乐部、美术馆等等各个角落都被凯鲁亚克用类似于影像的形式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饱含着他对纽约文化的真切情感认知,也带着他对“垮掉派”自由、放纵的向往。
三、 文化记忆背后的文化立场
虽然从表面上看,凯鲁亚克在这本旅行自传中描写了大量的自然生态景观,但与世界文化对比,在文化记忆当中阐述自己的文化立场,才是凯鲁亚克所要实现的真正意图。在《孤独旅者》中,凯鲁亚克认为多数人对“垮掉派”以及他们所追求“另类文化”存有相当的误解,而这部作品的目的正在于以旅行为切入点,深入解读“垮掉派”,从而厘清“垮掉派”文学与美国文学传统之间看似复杂的关系,解决如何澄清人们的误解,处理美国文化与他们的艺术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
在旅行札记式的《孤独旅者》中,凯鲁亚克通过横跨美国大陆,向读者呈现了美国社会下层文化的粗俗、残酷、压抑和绝望,通过跨越国境走上异国土地,客观地记录下墨西哥与法国的轻松文化氛围,在强烈的画面感与时空对比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种种文化形态形成的昏沉幻觉和沉重压抑。这种压抑其实代表了美国新生艺术家生存、创作的艰辛境地与苦难现实,当然更是对美国传统文化对新生文化进行抑制的客观体现。在作品中,凯鲁亚克花费大量篇幅展现美国文化现实的目的是揭示传统的丑陋与垮掉派艺术家所处文化空间的狭小和被泯灭的艺术希望。这种传统与新生文化的矛盾反映在自传里作家的个人流浪经历和路上生活的苦难,不断地逃离和寻找的过程。在故事当中,那个不断出现的流浪汉,正是无数“垮掉派”艺术家的象征和缩影,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挤压之下无从发挥文化灵感,但又不得不在社会、文化以及大众的误解与轻视当中,艰难缓慢地寻找突破,在传统文化的黑暗之中挣扎着寻找并捕捉艺术生命的希望之光。在挣扎、彷徨、痛苦当中,凯鲁亚克在小说中这样描述了美国传统文化:啊,美国,如此强大,如此悲伤,如此黑暗,你就像干燥夏季里的树叶,在八月之前就开始卷皱,看到了尽头。你是无望的,每一个人都在旁观你,那里只有枯燥乏味的绝望,对将死的认知,当下生活的痛苦。通过这充满苦涩意味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凯鲁亚克对于美国传统文化强大却枯竭的深刻认知,以及那对于新生文化希望的强烈渴求。
虽然一直以来,外界都将凯鲁亚克看作是反叛象征以及反文化运动的代表,未关注到他在《孤独旅者》中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美国传统文化的细微态度转变。但是,从凯鲁亚克在旅途中感受孤独以及思考人生的态度上,我们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对于美国社会以及美国传统文化,他的态度实际上并非是一味地反叛和逃离,而是存在认同,并且他认为“垮掉派”同样需要更好地接受和构建文化,而这种贡献完全可以体现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正如他所讲到的“热爱生活本来的样子吧,不要在你的头脑里建立任何先入之见……”“我意识到不必把自己隐藏在孤寂当中,而可以接受社会,不论其好坏”“有一天我在文学上的努力将从社会保护中得到回报”。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与“垮掉派”文化的关系来讲,凯鲁亚克并不认为两者是水火不相容,反而“垮掉派”文化能够以传统文化的土壤为生存依托,并在其基础上构建更好的文化。语
参考文献
[1]杰克·凯鲁亚克.孤独旅者[M].赵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李杰.消失在路上的流浪汉——读凯鲁亚克的《孤独旅者》[J].语文世界,2006.
[3]徐翠波.《孤独旅者》与凯鲁亚克的文化记忆[J].外国语文,2011(08).
[4]夏学花.嬉皮士:美国主流社会的叛逆一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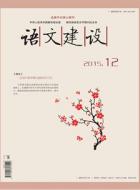
- 论写作教学模式建构的方法 / 彭小明 刘亭玉
- 语文课堂情感教学的再思考 / 赵爽 王相文
- 错位的教育何时能归位? / 张春梅
-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的概念图阅读策略培训设计 / 李艾平 王欣春
-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价值特性分析 / 刘品端
- 将情感注入学生 / 心田 牛永刚
- 浅论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渗透问题 / 叶敏
- 语文教学目标的价值诉求及有效生成 / 程颖
- 论ZHC测试与广西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结合 / 冯海英
-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目的观演变及启示 / 李文华
- 农村语文教师朗读教学能力亟待提升 / 苏洁梅
- 写作教学还可以这样教 / 王伟
- 语文学科性质观之争及滥觞追溯 / 赵东阳 王春梅
- 刍议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 张毅蕾
- 经典诵读的语文阅读教学实践性研究 / 程乔夏
- 以《平凡的世界》为视角看现状文学教育 / 雷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融合策略 / 张立英 朱敏
- 关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探讨 / 南君
- 语用课堂:为言语生命的发展奠基 / 欧加刚
- 高校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进路 / 王玲玲
- 《草原日出》生态主义叙事声音研究 / 冯平
- 论作家曼斯菲尔德小说体裁的文本创新 / 高向晔
- 海明威《老人与海》空间与叙事探析 / 郭菲 李晶
- 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叙事艺术探微 / 胡文涓
- 毕淑敏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评析 / 李艳云 李彩霞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刘翠萍
- 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虹》中的厄秀拉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形象分析 / 马义
- 哥特小说传统下的《哈利·波特》创作研究 / 蒙静
-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解析 / 王凡
- 川端康成小说中“女性救赎”主题解读 / 吴小梅
- 简·奥斯汀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比较 / 闫俊玲
- 黑色幽默与身份构建 / 杨坤 马永良
- 霍桑《红字》中的象征主义解读 / 张科
- 真实的世界:《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 / 徐晓芳
- 论《爱的牺牲》中的悲观主义爱情 / 刘俊丽
- 凯鲁亚克《孤独旅者》的文化记忆述略 / 杨昕璐
- 解读《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苦难意识的书写 / 孙艳红
- 简论《约瑟夫·安德鲁传》的艺术特色 / 潘秋阳
- 从林黛玉的“哭”探究其人生的四重悲剧 / 杨彦科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伊莉莎的心路历程解析 / 王书艳
- 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比较研究 / 毛三艳
-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学理论研究 / 辛魁鹏
- 粤语童谣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传承与发展 / 徐艳贞 何志慧
- 探析《一把尘土》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黄玉梅
- 网络媒体标题语言特点与新用词研究 / 李婧
- 华兹华斯《水仙》的诗歌语言评析 / 李丽英
- 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意象与语言隐喻 / 李月圆
- 钱钟书《围城》文学修辞语言研究 / 梁造禄
- 近十年网络语言及其使用现状分析 / 娄博 李改婷
- 认知语言学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 宋新克
-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评析 / 孙远
- 先秦汉语时间词汇系统研究 / 滕华英
- 论爱德华·萨丕尔语言与文学关系理论研究 / 王惠欣
-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评析 / 王晶
- 认知转喻视域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 邢大红
- 海明威《一天的等待》语言特色与表现手法 / 张明梅
- 雷蒙德·卡佛的文学语言观念之解读 / 胡海青
- 语言规范的预测性问题 / 杜兰兰
- 语文教学下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素养的优化路径 / 谢晓信 梁汉平
- 语文教育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研究 / 项丽娜
- 试论英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 / 马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