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74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74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伊莉莎的心路历程解析
◇ 王书艳
摘要:本文拟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详细分析《卖花女》中伊莉莎从追寻到迷失,再到觉醒的心路历程,揭示其“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启发现代女性如何实现自身价值。
关键词:伊莉莎 本我 自我 超我
引言
英国现代最伟大的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1856-1950),一生共创作了52部剧本、5部小说和数量巨大的其他著作。其喜剧《卖花女》自问世以来,多次被拍成电影、改编成音乐剧,并成为深受全球读者青睐的经典之作。该剧通过生动的心理刻画和幽默讽刺的语言描写,讲述了出身贫寒的卖花姑娘伊莉莎拜著名语言学家息金斯教授为师后,如何变身为举止优雅、端庄大方的上层贵妇,并最终离开上层社会的故事。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可知,学者和专家已从哲学、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文体学、语用学、接受美学等角度对该剧的创造进化论、神话原型、女性意识、语言特色、戏剧效果等进行分析,然而对伊莉莎的心理研究尚未涉及。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概述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又称心理分析)主要包括“人格理论、本能论、焦虑论、性欲论和梦的理论”。[1]其中,早期的“地形观”人格理论将人格分为:最外层的意识、中间层的前意识和最里层的潜意识。意识是人对外界现实环境和刺激的直接感知。前意识是调节意识和无意识的中介机制。潜意识则是在意识和前意识之下,受到压抑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心理活动。
晚期的“结构观”人格理论则将人格分为:最底层的本我、中间层的自我和最高层的超我。本我是“一团混沌,云集了各种沸腾的兴奋”,在本能的驱使下遵循“享乐原则”,努力满足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对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熟视无睹。[2]超我代表着良心和自我理想,依靠“道德原则”而成为“本我的压制者”。[2]自我深受“本我、超我、外部世界的规范”的三重压力而遵循“现实原则”。[2]弗洛伊德指出:本我、自我和超我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只有保持三者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人的心理才能处于正常状态,人格才能健康发展。
二、伊莉莎的心路发展历程
《卖花女》不仅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等级意识的腐朽保守,还真实展现了伊莉莎的心路发展历程。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伊莉莎萌发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念头。于是,她鼓起勇气,登门向息金斯求教,并在语音训练中,对他渐生情愫,一度迷失自我,但最终觉醒,选择离开。
(一)直面现实,敢于追寻梦想
首次出场时,头发“像灰老鼠似的”伊莉莎戴着“沾满伦敦的尘土和煤烟”的黑色小草帽,穿着“又粗又旧的黑大衣”“深黄色的裙子”和破靴子,“罩着粗布围裙”,日夜奔波于伦敦街头,遭人白眼、受人歧视。[3]然而,在“超我”的作用下,她显得异常坚强和乐观,怀揣自食其力的“自我理想”,还常用辛苦挣来的钱接济嗜酒如命的父亲,这正是她报答养育之恩的“良心”所在。
同时,伊莉莎的“自我”时刻遵循着“超我所要求的行为准则”。[2]虽衣服破旧,她出门前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因为“自我”不断提醒她:若要卖掉手中的花,外在形象很重要。虽住着“连猪圈也够不上”的房子,她并没怨天尤人,却勇敢维护自身权利和尊严:当觉得息金斯记录的话可能对自己不利时,她竭力辩护:“咱卖花也不犯法,……咱可是个正经人家的女孩子”;当息金斯嘲笑她口音难听时,她发出微弱的抵抗声:“咱愿意待在这儿嘛,你管不着”。[3]
然而,伊莉莎的“自我”也要“满足本我的欲望冲动”。[3]作为普通人,她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欲望和需求。首先,她想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一幕结束时,拿到息金斯扔下的一大把钞票,她立刻有了打车回家的欲望。为了满足“本我”的虚荣,她拿出钱来向车夫炫耀:“瞧,车钱对咱不算啥。”[3]其次,她不想安于现状。当得知只要三个月的工夫,息金斯就能让她参加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甚至可为她找个上等人家的保姆或店员的工作时,她有了不能只在大街上卖花的想法。
但是,伊莉莎并没异想天开,奢想成为上流社会的公爵夫人。相反,她能认清现实,树立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在花铺里做个店员”[3]。这正是“自我”“本我”和“超我”相互协调的结果。从此,伊莉莎开始了追寻梦想的漫漫长路。
(二)历经艰辛,偏又迷失方向
诚然,对伊莉莎来说,要实现梦想谈何容易?拜师前,她刻意打扮一番,戴上插了“三根驼鸟毛”的帽子,围上“不算脏的围裙”,穿上“弄得整齐了一些”的粗布外衣。[3]遭到断然拒绝后,她并没立即离开,因为“本我”告诉她:如果离开,一切将成为南柯一梦。同时,“自我”要求她及时调整策略,运用激将法迫使息金斯考虑收她为徒。然而,息金斯要烧掉她的衣服、用去污粉给她洗澡的建议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她决定放弃求学。甚至,息金斯的物质诱惑—“有整盒、整桶的糖”可“一天到晚吃”、可每天“坐汽车游遍全城”和“想着巧克力糖、汽车、金子和钻石”—也没让她的“本我”占据上风。伊莉莎坦言:自己是个正派人,不会无缘无故要别人的东西,也从未想过“坐着很漂亮的马车到白金汉宫去”,但为了实现梦想,她愿意留下[3]。
在六个月的魔鬼训练中,聪明、勤奋的伊莉莎彻底改观了语音面貌、掌握了各种方言、学会了搭配衣服、弹好了钢琴。在朝夕相伴中,她对息金斯渐生爱意,主动照顾他的衣食住行,这正是其“本我”情欲的自然流露。为博得心上人的欢心,她在大使馆舞会上竭尽全力,凭借完美的语音、优雅的仪容和维多利亚女王似的神气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和夸赞。
晚会结束后,回到现实中的伊莉莎深陷困惑:命运能眷顾她,让她成为息金斯太太吗?然而,沉醉于胜利喜悦中的息金斯非但没察觉到其情感变化,更不理解她为何情绪低落。息金斯如释重负地“谢天谢地,总算完了”让她不禁质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到哪里去?我做什么好?我将来怎么办?”[3]的确,她在街头卖花时,虽收入不多,却心情愉快;虽口音不纯,却无人在意。如今,标准的发音、优雅的举止并没改善其经济状况、提高其社会地位,却让她在亲身经历了“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之后,无视刚刚接触的文明而退回到曾经的无知状态”。 [4]此时,伊莉莎像一艘迷失方向的小船,独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却求助无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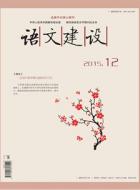
- 论写作教学模式建构的方法 / 彭小明 刘亭玉
- 语文课堂情感教学的再思考 / 赵爽 王相文
- 错位的教育何时能归位? / 张春梅
-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的概念图阅读策略培训设计 / 李艾平 王欣春
-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价值特性分析 / 刘品端
- 将情感注入学生 / 心田 牛永刚
- 浅论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渗透问题 / 叶敏
- 语文教学目标的价值诉求及有效生成 / 程颖
- 论ZHC测试与广西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结合 / 冯海英
-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目的观演变及启示 / 李文华
- 农村语文教师朗读教学能力亟待提升 / 苏洁梅
- 写作教学还可以这样教 / 王伟
- 语文学科性质观之争及滥觞追溯 / 赵东阳 王春梅
- 刍议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 张毅蕾
- 经典诵读的语文阅读教学实践性研究 / 程乔夏
- 以《平凡的世界》为视角看现状文学教育 / 雷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融合策略 / 张立英 朱敏
- 关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探讨 / 南君
- 语用课堂:为言语生命的发展奠基 / 欧加刚
- 高校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进路 / 王玲玲
- 《草原日出》生态主义叙事声音研究 / 冯平
- 论作家曼斯菲尔德小说体裁的文本创新 / 高向晔
- 海明威《老人与海》空间与叙事探析 / 郭菲 李晶
- 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叙事艺术探微 / 胡文涓
- 毕淑敏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评析 / 李艳云 李彩霞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刘翠萍
- 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虹》中的厄秀拉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形象分析 / 马义
- 哥特小说传统下的《哈利·波特》创作研究 / 蒙静
-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解析 / 王凡
- 川端康成小说中“女性救赎”主题解读 / 吴小梅
- 简·奥斯汀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比较 / 闫俊玲
- 黑色幽默与身份构建 / 杨坤 马永良
- 霍桑《红字》中的象征主义解读 / 张科
- 真实的世界:《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 / 徐晓芳
- 论《爱的牺牲》中的悲观主义爱情 / 刘俊丽
- 凯鲁亚克《孤独旅者》的文化记忆述略 / 杨昕璐
- 解读《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苦难意识的书写 / 孙艳红
- 简论《约瑟夫·安德鲁传》的艺术特色 / 潘秋阳
- 从林黛玉的“哭”探究其人生的四重悲剧 / 杨彦科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伊莉莎的心路历程解析 / 王书艳
- 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比较研究 / 毛三艳
-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学理论研究 / 辛魁鹏
- 粤语童谣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传承与发展 / 徐艳贞 何志慧
- 探析《一把尘土》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黄玉梅
- 网络媒体标题语言特点与新用词研究 / 李婧
- 华兹华斯《水仙》的诗歌语言评析 / 李丽英
- 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意象与语言隐喻 / 李月圆
- 钱钟书《围城》文学修辞语言研究 / 梁造禄
- 近十年网络语言及其使用现状分析 / 娄博 李改婷
- 认知语言学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 宋新克
-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评析 / 孙远
- 先秦汉语时间词汇系统研究 / 滕华英
- 论爱德华·萨丕尔语言与文学关系理论研究 / 王惠欣
-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评析 / 王晶
- 认知转喻视域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 邢大红
- 海明威《一天的等待》语言特色与表现手法 / 张明梅
- 雷蒙德·卡佛的文学语言观念之解读 / 胡海青
- 语言规范的预测性问题 / 杜兰兰
- 语文教学下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素养的优化路径 / 谢晓信 梁汉平
- 语文教育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研究 / 项丽娜
- 试论英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 / 马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