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67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67
真实的世界:《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
◇ 徐晓芳
摘要:V.S.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移民作家和旅行作家。《游击队员》是奈保尔后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游击队员》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体现出多重主题的写作特点。
关键词:奈保尔 自然主义视角 《游击队员》
引言
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写作生涯获奖无数。他在受奖时曾说过:“我认为,我是我所有作品的总和。我的书都基于直觉的体验,小说则是凭借直觉写就。”作为后殖民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奈保尔的作品大多出自他密切的观察。他在题为《两个世界》的获奖演说中说过:“小说和旅行记录这两种创作方式,给了我自己观察世界的方法。”[1]而以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认为作家不能凭想象和观念,而应该以真实的体验或经验为基础进行写作,文章才会出现“真实和自然”。这与奈保尔的创作理念是完全相符的。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在《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写道:“60年代社会的变化的激素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治地位的某些小说形式的枯竭,给作家们创造了新的机会,一个最有趣的表现是杂交形式的产生,它混合了小说的技巧和新闻报道的细致观察。”[2]奈保尔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作家。他善于用后殖民社会人群为原型进行小说创造,也善于用真实事件作为小说的题材。他一直反对过分追求戏剧化的情节。[3]所以说奈保尔小说带有明显的纪实性、传记型和自然主义倾向。本文试从自然主义视角来解读奈保尔的经典小说《游击队员》,揭示其自然主义倾向。
一、真实的人性:人的动物性和遗传性
自然主义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强调人的动物性,人往往被欲望所支配,是本能的载体,缺乏理性和自制力。人的动物性,在《游击队员》中,首先体现在人的种族、肤色等遗传性和无法选择性。主角吉米一出场,奈保尔就通过简的视角充分地展示给读者:吉米没有简原以为的难看,也不那么像黑人。简以为他至少跟那些男孩子一样黑,但眼前这个人很像中国人。[4]而描写简时奈保尔也突出了白人的显著特征:她的白跟当地白人的白根本不一样。她白得难以捉摸,连年龄都叫人猜不出。[5]寥寥几笔,却使得读者对于两者的不同种族身份了然于心。
左拉指出:“人的生理条件,人这架机器如何运转,如何思想,如何热爱,如何从激情发展到疯狂,这些现象都是由与遗传有关的生理器官控制的。”[6]正是因为吉米的印度和中国的混血儿身份,使得其名义上是领导革命运动的黑人领袖,其实只是个傀儡。他内心更是充满了自卑和自怜以及虚妄的自大。而简的白人身份也赋予了她处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她看来,英国才是世界的中心。次要人物布莱恩特是个当地的非洲男孩,生来就被抛弃,只能加入吉米的“革命”组织,并对吉米产生了畸形的爱恋。
而书中几段人物之间的性关系更是充满了动物本能性的描写。简与丈夫离婚之后,换了一个又一个的情人,甚至被强迫堕胎。各种政治事件、动荡不安的社会、男人的本性,以及她作为女人的需求把她推进了性的丛林,让她在未知中危险地摸索。[7]简对吉米充满了好奇心和征服欲;而吉米则被这个白种女人的仪态所迷倒,在日志里更是展现出一种病态的意淫。人性的本能使两人结合在一起,他们追求的只是亢奋的感觉而已。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奈保尔遵循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原则,重视人的遗传性和动物本能,充分让读者感受到在后殖民社会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人性最原始最真实的一面也往往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
二、冷静的描写:残酷的自然环境
小说《游击队员》充满了性、暴力和残忍的凶杀,弱小的岛国并没有真正地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虽然现实是血淋淋的,但纵观整本书,奈保尔客观冷静地描述和记载,并没有插入作者的主观评价,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思辨色彩。
首先,小说来源于一个真实的谋杀事件。1973年,奈保尔针对这一谋杀事件写成新闻报道——《迈克尔X和特立尼达的黑色权力谋杀》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杂志。1975年,在这篇报道基础上加工的小说《游击队员》问世。所以,与奈保尔的其他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充满了现实与虚构相交织的写作手法。左拉所强调的如实地感受和表达自然,首先取决于作家本身的生活体验,作家应该书写自己熟悉的环境,以主观感受在主体内部沉淀,然后用第三者的态度书写出来。而奈保尔始终以一个移民者的混杂身份观察、分析、论证。当然,这样的写作态度也会引起一些后殖民学家的批评。著名第三世界学者萨义德就宣称:奈保尔持有的是“西方的思想立场”。[8]但笔者认为,正是奈保尔这样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使得奈保尔能始终以“他者”的身份进行真实的书写。
其次,左拉主张“把人重新放到自然中去,放到他所固有的环境中去,使分析一直伸展到决定他的一切生理和社会原因中,而不是把他抽象化”。[9]奈保尔笔下的人物表情、动作、语言、环境,都非常真实,既不夸大事实,也不粉饰太平。这样的平实而细致的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
当罗奇和简第一次来到画眉山庄,书中描写到:走进小屋,一脚从黏土地踏上水泥地,简和罗奇看见一个未打扫过的角落放着一个钢制档案柜和一把旧餐椅,一张落满灰尘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看似报废的打字机、一台报废的复印机和几个铁文件盘。[10]细腻又写实的描写展现了在画眉山庄这美好的名字下,革命公社真正的情况:缺电缺水,没有必须的设备,昏暗的光线让人觉得压抑。不需要任何评论,大师笔下的寥寥几笔,会让读者觉得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令人压抑的环境里,吉米的革命梦显得那么地荒诞和可笑。
三、自然主义宿命论:灰暗与绝望
在自然主义者看来,人像动物一样,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对外界的力量和内在的冲动消极地做出反应;对于这些力量与冲动,他既无法控制也难以理解。[11]《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也表现在书中几个人物悲惨的命运。奈保尔在书中阐述的观点和自然主义文学家一样:他们的命运由遗传基因和自然环境所支配,人无法与自然和命运抗衡。奈保尔的早期作品,如《米格尔街》,虽也是小人物的悲歌,但体现了笑中含泪的诙谐悲喜剧风格。然而在《河湾》《游击队员》《魔种》等中后期作品中,早期小说轻松的格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悲观主义: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世界上没有位置。[12]奈保尔用平实的文风、清醒的洞察力冷静地向读者揭示了后殖民世界中边缘人的艰难处境和悲剧宿命。
在小说《游击队员》中,不论是白人革命者罗奇,还是黑人领袖吉米,都是失败的革命者。书中在开篇就指出,革命组织所谓的机密文件就如一篇小学生作文。而革命根据地画眉山庄则缺水缺电,被荒地环绕;“革命者们”行动原则混乱不堪,一事无成。在奈保尔看来,这样的革命运动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奈保尔在开篇就暗示读者: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小说中是否有真正的游击队员?答案是否定的。吉米虽身为黑人领袖,但是他中印混血儿的身份注定了只是一个局外人和边缘人。面对政府的清算,吉米昔日的黑人手下纷纷离他而去,而同性恋人布莱恩特则要守在房子外面等着杀死他。简更是可怜又可悲的一个人物,她觉得她的英国籍身份可以让她拥有随时离开非洲的特权,然而尽管行李箱已经收拾了一半,她还是被吉米强暴之后残忍地杀害了。她的情人罗奇,在发现简被杀害后,佯装不知,只顾着自己抽身离去。表面上看,奈保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读者能够清楚地预测,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任何人都只是身在其中的棋子,无法抗争悲惨的命运。
结语
总体来看,奈保尔在《游击队员》中有效地表达了他的自然主义观点:通过对第三世界无名小国革命的细节描写,读者最终领略到奈保尔一个悲观的自然主义宿命论者对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取得独立后混乱无序社会的担忧和失望。语
参考文献
[1]V.S.Naipaul. Two Worlds, in literary occasions[M]. New York & Toronto: Alfred A. Knopf, 2003.
[2]约翰·霍洛韦尔.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M].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3]奈保尔.奈保尔家书[M].北塔,常文琪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4][5][7][10] 奈保尔.游击队员[M].张晓意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6]左拉.实验小说论[A].文学中的自然主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8]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3.
[9]曾繁亭.“真实感”——重新解读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论[J].外国文学评论, 2009(11).
[11]侯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12]奈保尔.河湾[M].方柏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项目:泰州学院校级课题:文化身份的书写:奈保尔小说解读(项目编号:TZXY2013YBKT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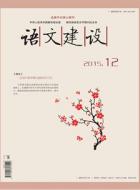
- 论写作教学模式建构的方法 / 彭小明 刘亭玉
- 语文课堂情感教学的再思考 / 赵爽 王相文
- 错位的教育何时能归位? / 张春梅
-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的概念图阅读策略培训设计 / 李艾平 王欣春
-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价值特性分析 / 刘品端
- 将情感注入学生 / 心田 牛永刚
- 浅论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渗透问题 / 叶敏
- 语文教学目标的价值诉求及有效生成 / 程颖
- 论ZHC测试与广西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结合 / 冯海英
-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目的观演变及启示 / 李文华
- 农村语文教师朗读教学能力亟待提升 / 苏洁梅
- 写作教学还可以这样教 / 王伟
- 语文学科性质观之争及滥觞追溯 / 赵东阳 王春梅
- 刍议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 张毅蕾
- 经典诵读的语文阅读教学实践性研究 / 程乔夏
- 以《平凡的世界》为视角看现状文学教育 / 雷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融合策略 / 张立英 朱敏
- 关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探讨 / 南君
- 语用课堂:为言语生命的发展奠基 / 欧加刚
- 高校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进路 / 王玲玲
- 《草原日出》生态主义叙事声音研究 / 冯平
- 论作家曼斯菲尔德小说体裁的文本创新 / 高向晔
- 海明威《老人与海》空间与叙事探析 / 郭菲 李晶
- 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叙事艺术探微 / 胡文涓
- 毕淑敏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评析 / 李艳云 李彩霞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刘翠萍
- 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虹》中的厄秀拉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形象分析 / 马义
- 哥特小说传统下的《哈利·波特》创作研究 / 蒙静
-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解析 / 王凡
- 川端康成小说中“女性救赎”主题解读 / 吴小梅
- 简·奥斯汀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比较 / 闫俊玲
- 黑色幽默与身份构建 / 杨坤 马永良
- 霍桑《红字》中的象征主义解读 / 张科
- 真实的世界:《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 / 徐晓芳
- 论《爱的牺牲》中的悲观主义爱情 / 刘俊丽
- 凯鲁亚克《孤独旅者》的文化记忆述略 / 杨昕璐
- 解读《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苦难意识的书写 / 孙艳红
- 简论《约瑟夫·安德鲁传》的艺术特色 / 潘秋阳
- 从林黛玉的“哭”探究其人生的四重悲剧 / 杨彦科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伊莉莎的心路历程解析 / 王书艳
- 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比较研究 / 毛三艳
-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学理论研究 / 辛魁鹏
- 粤语童谣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传承与发展 / 徐艳贞 何志慧
- 探析《一把尘土》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黄玉梅
- 网络媒体标题语言特点与新用词研究 / 李婧
- 华兹华斯《水仙》的诗歌语言评析 / 李丽英
- 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意象与语言隐喻 / 李月圆
- 钱钟书《围城》文学修辞语言研究 / 梁造禄
- 近十年网络语言及其使用现状分析 / 娄博 李改婷
- 认知语言学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 宋新克
-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评析 / 孙远
- 先秦汉语时间词汇系统研究 / 滕华英
- 论爱德华·萨丕尔语言与文学关系理论研究 / 王惠欣
-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评析 / 王晶
- 认知转喻视域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 邢大红
- 海明威《一天的等待》语言特色与表现手法 / 张明梅
- 雷蒙德·卡佛的文学语言观念之解读 / 胡海青
- 语言规范的预测性问题 / 杜兰兰
- 语文教学下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素养的优化路径 / 谢晓信 梁汉平
- 语文教育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研究 / 项丽娜
- 试论英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 / 马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