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58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ID: 422858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刘翠萍
摘要: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丰碑人物,他富有争议的性描写虽然一度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但是终于依靠深刻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肯定。劳伦斯的小说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仅通过性描写表达了对健康和谐两性关系的关注和憧憬,而且通过对自然和女性关系的刻画表现了其浓郁的生态意识。本文主要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梳理分析,试以揭示劳伦斯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和女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劳伦斯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生态女性主义
引言
劳伦斯(1885 -1930)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命运多舛的作家,在有限的年华里创作了数量不菲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大。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却因为过多“性描写”被扣上“淫秽色情”的罪名,屡遭禁止,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非议,作者一度陷入“被驱逐出境”的窘境,但是后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舆论开始认同劳伦斯的小说作品,并为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容而折服。得到“平反”之后,劳伦斯的诸多小说先后步入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殿堂,其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就是此类大作的典范。略读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它好像一部纯粹的情色小说,实际上劳伦斯不仅仅通过对性爱生活的艺术描写来关注工业化以来扭曲变形的两性关系,而且通过对自然和女性紧密关系的描绘表达出对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1]
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兴理论,最初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她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中不仅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而且系统论述了自然遭受破坏和女性受到压迫的内在联系,比如女性特有的月经、怀孕、分娩等生理现象与自然孕育生命的功能如出一辙,同时也强烈呼吁女性进行一场旨在挽救自然和呵护女性的生态革命,构建一个平等和谐的新世界。[2]在德奥博纳的积极倡导下,苏珊·格里芬、斯塔霍克、瓦伦、玛丽·达利、麦茜特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该领域研究,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延伸到文化、政治、哲学等领域。作为一个近来流行并不断发展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在始终没有背离“女性与自然和谐统一”原则的基础上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互相依存的新型关系,其最终目的是希望以这种新的思维方法与生活态度来颠覆男权社会凌驾自然、男人凌驾女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大自然继续受人类剥削,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
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劳伦斯生活的时代英国早已经步入了机器主宰的工业化时代,人们就像没有生命力的零件一样在机械运转,毫无往昔的精气神儿可言,而且之前淳朴真诚的两性婚姻关系也变得“捉摸不定”,很难寻觅到“真情”的存在。作为一个忧虑生态和关怀女性的现代小说家,劳伦斯一方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保持抵触情绪,一方面对以父母婚姻为代表的不和谐两性关系保持反对态度,于是在文学创作中着意关注了生态和女性,而在创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劳伦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更是发展到了高峰。[3]
康妮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主人公,也是劳伦斯小说作品中最具个性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既是传递劳伦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线索,也是这种思想亲历实践者。小说以康妮的视角展现了大自然惨遭人类践踏的境况,首先读者可以清晰看到米德兰矿区衰败不堪的景象:这里没有鸟语花香,甚至连衰败的杂草都难以看见,只有轰鸣不断的机器嘈杂声、四处飞扬的黑色煤灰以及漫天扩散的刺鼻气味。康妮嫁人之后生活的区域就在煤矿附近,同样显得肮脏丑陋、荒凉无趣:一排排低矮的丑陋房子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外在看点”,房间内部也是十分阴森凄凉,而且整日笼罩在“矿上筛子机的沙沙声, 起重机的喷气声, 载重车换轨时的响声, 和火车头粗哑的汽笛声”中。之所以描写康妮嫁人后生活区域的破落,劳伦斯是从女性视角衬托女性深受男性社会压迫的社会状况,这也是工业化以来女性沦为父权制社会附庸现象加剧的表现。[4]在出嫁之前,作为一个天性活泼、向往自由的女孩,康妮一直过着多姿多彩的快乐生活,但是追随丈夫克利福德来到拉格比之后一切都变得“无精打采”,尤其是丈夫残疾以后,她就过上了遥遥无期而备受煎熬的日子。丈夫的致残不仅代表着工业化对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摧残,而且预示着对女性的摧残,使得女性应有的幸福生活变得黯淡无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男性在女性生活中的地位。
尽管康妮生活在了无生机的矿区,和没有爱情的婚姻坟墓中,就像劳伦斯在作品中描述的一样: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但是她没有放弃、也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是在静谧和谐的大自然中发现了“奇迹”。康妮在距离矿区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自然乐园,这里没有受到工业化的任何浸染,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伊甸园:茂密的林子里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畅快,鸟儿愉快地歌唱,各种花儿竞相绽放。当徜徉于自然美景的康妮在林子里发现了健康的守林人梅勒斯时,她一下子就被梅勒斯强健的体魄、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充沛的精气神儿等“自然人”的特征深深吸引了。或许是被压抑得太久,康妮第一次就深深喜欢上了这片富有生机的树林,也对守林人梅勒斯产生了无穷的幻想和迷恋。透过康妮的举动,我们可以感受到劳伦斯对纯净大自然的向往以及他对健康女性世界的期愿。也正是在自然的“牵线”之下,向往自由的康妮和充满自然本性的梅勒斯相爱了。出于身体和心理本能,康妮和梅勒斯在林木环绕的小木屋中深深相爱,迷失已久的康妮终于被唤醒,开始感受到了生命的精彩魅力。他们的交流融合可以说是大自然所赐,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的和谐融合。康妮的行为虽然从伦理上看属于“偷情”,似乎不合人类道德,但这恰恰是对传统畸形两性婚姻生活的反叛,是对自由爱情的追求。[5]
某种程度上说,自然拯救了孤独的康妮,使其重新回到了自由的怀抱,但是在其大部分时间里她依旧生活在无比压抑的拉格比,时时刻刻接受着丈夫无处不在的“囚禁”。与活力四射的“自然之子”梅勒斯相比,康妮的丈夫克利福德如同一个机械人一样毫无情趣与活力,他自身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受害者,而且也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典型施暴者。克利福德身上散发着太多的非自然因素,被现代战争摧毁的他整天就被囚禁在轮椅上,每天依靠妻子康妮的服侍过着重复无味的生活。这把时刻出现的轮椅既是丑恶工业文明的象征,也是男性统治的代表。当克利福德坐着轮椅来到小树林时,自然就受到了空前的摧残,不仅林中绽放的小花儿被碾碎,就连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和引吭高歌的鸽子也成了他仇视的对象。克利福德对自然的态度和对女性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每天的生活起居离不开妻子康妮的照顾,而且空虚的心灵也依靠康妮妻子身份的存在维系着,他甚至认为妻子的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但他却无法给妻子带来任何的回报。他只能紧紧抓住婚姻这个绳子,让康妮处在无性、无爱、无情的婚姻枷锁中。更加令人不齿的是,克利福德虽然失去了生育能力,但为了继承人居然同意妻子康妮和别人怀上孩子,他真的是把女性和婚姻当成了功利的工具。克利福德眼中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婚姻伦理道德意识,他只是试图通过女性的存在来维护自己虚伪的尊严和所依存的男权社会体系。不光对妻子充满了功利化态度,对其他人,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矿工们保持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而只在乎他们能够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价值,根本不会考虑到丝毫的人文情怀,正如他对女性和自然的态度一样。
可喜的是,陷入孤独的康妮及时碰见了守林人梅勒斯,逐渐从男性统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梅勒斯的小木屋,康妮可以像以前一样与绿树、青草、猎狗、土鸡等自然生灵在一起接受自然的沐浴,也可以与梅勒斯过上完整幸福的两性生活,实现人类淳朴本真的欲望。我们说梅勒斯是“自然之子”,并不是说他不懂现代文明,而是他不屑于与遭受工业文明和父权体系玷污的世俗社会同流合污,因为除了说土语之外,梅勒斯完全可以说出流利标准的现代语言,也可以成为一个上尉、步入上流社会。康妮与梅勒斯的一次次身体欢愉都代表着对人类本真需求和自我解放的追求,特别是最后他们在滂沱大雨中裸奔和爱抚的场面成了一个永恒的瞬间,这是他们对传统父权制社会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出的最强音挑战。康妮最后怀上了梅勒斯的孩子,也预示新生的到来,体现了劳伦斯对构建新型社会的憧憬。[6]
结语
作为劳伦斯的封笔之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无愧于经典的称号,它以富有争议的形式向世人充分证明了“是金子总要发光”的道理。在小说中,劳伦斯通过对主人公康妮爱情生活的描述一方面揭示了女性与自然遭受压迫的根源,隐喻出女性与自然的内在必然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康妮与守林人梅勒斯爱情的唯美描绘不仅揭示出对传统世俗爱情的不屑和对男权社会的对抗,而且也体现出对完美和谐两性关系的殷切期冀。语
参考文献
[1]刘聪.女性解放与男权主义的交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叙述声音与角色声音的对立[J].贺州学院学报,2013(01).
[2]苗琴.从生态批评视野下解读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J].语文建设,2013(14).
[3]熊蕾.生态批评视域下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解读[J].语文建设,2015(14).
[4]杨长荣.“生命”在旷野的呼唤中再生——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探索劳伦斯及其作品的生态批评观[J].青春岁月,2013(10).
[5]谯莉.浅析劳伦斯作品中的两性观和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J].语文建设,2012(14).
[6]龚敏.劳伦斯小说创作中的文学传统解读[J].语文建设,201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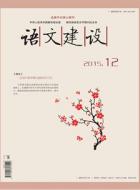
- 论写作教学模式建构的方法 / 彭小明 刘亭玉
- 语文课堂情感教学的再思考 / 赵爽 王相文
- 错位的教育何时能归位? / 张春梅
-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的概念图阅读策略培训设计 / 李艾平 王欣春
-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价值特性分析 / 刘品端
- 将情感注入学生 / 心田 牛永刚
- 浅论小学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渗透问题 / 叶敏
- 语文教学目标的价值诉求及有效生成 / 程颖
- 论ZHC测试与广西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结合 / 冯海英
-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目的观演变及启示 / 李文华
- 农村语文教师朗读教学能力亟待提升 / 苏洁梅
- 写作教学还可以这样教 / 王伟
- 语文学科性质观之争及滥觞追溯 / 赵东阳 王春梅
- 刍议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 张毅蕾
- 经典诵读的语文阅读教学实践性研究 / 程乔夏
- 以《平凡的世界》为视角看现状文学教育 / 雷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融合策略 / 张立英 朱敏
- 关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探讨 / 南君
- 语用课堂:为言语生命的发展奠基 / 欧加刚
- 高校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与实现进路 / 王玲玲
- 《草原日出》生态主义叙事声音研究 / 冯平
- 论作家曼斯菲尔德小说体裁的文本创新 / 高向晔
- 海明威《老人与海》空间与叙事探析 / 郭菲 李晶
- 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叙事艺术探微 / 胡文涓
- 毕淑敏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评析 / 李艳云 李彩霞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刘翠萍
- 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虹》中的厄秀拉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形象分析 / 马义
- 哥特小说传统下的《哈利·波特》创作研究 / 蒙静
-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解析 / 王凡
- 川端康成小说中“女性救赎”主题解读 / 吴小梅
- 简·奥斯汀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比较 / 闫俊玲
- 黑色幽默与身份构建 / 杨坤 马永良
- 霍桑《红字》中的象征主义解读 / 张科
- 真实的世界:《游击队员》的自然主义倾向 / 徐晓芳
- 论《爱的牺牲》中的悲观主义爱情 / 刘俊丽
- 凯鲁亚克《孤独旅者》的文化记忆述略 / 杨昕璐
- 解读《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苦难意识的书写 / 孙艳红
- 简论《约瑟夫·安德鲁传》的艺术特色 / 潘秋阳
- 从林黛玉的“哭”探究其人生的四重悲剧 / 杨彦科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伊莉莎的心路历程解析 / 王书艳
- 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比较研究 / 毛三艳
-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学理论研究 / 辛魁鹏
- 粤语童谣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传承与发展 / 徐艳贞 何志慧
- 探析《一把尘土》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黄玉梅
- 网络媒体标题语言特点与新用词研究 / 李婧
- 华兹华斯《水仙》的诗歌语言评析 / 李丽英
- 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意象与语言隐喻 / 李月圆
- 钱钟书《围城》文学修辞语言研究 / 梁造禄
- 近十年网络语言及其使用现状分析 / 娄博 李改婷
- 认知语言学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 宋新克
-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评析 / 孙远
- 先秦汉语时间词汇系统研究 / 滕华英
- 论爱德华·萨丕尔语言与文学关系理论研究 / 王惠欣
-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评析 / 王晶
- 认知转喻视域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 邢大红
- 海明威《一天的等待》语言特色与表现手法 / 张明梅
- 雷蒙德·卡佛的文学语言观念之解读 / 胡海青
- 语言规范的预测性问题 / 杜兰兰
- 语文教学下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素养的优化路径 / 谢晓信 梁汉平
- 语文教育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研究 / 项丽娜
- 试论英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 / 马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