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12期
ID: 142021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12期
ID: 142021
《呼兰河传》中的绘画追求
◇ 徐君善
一、散文式架构是实现小说绘画化的基石
萧红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呼兰河传》几乎以散文式的结构来构架小说。小说共七章,可分可合,形散而神聚,形成了伸缩自如的开放性的散文化结构形态。传统用于构架小说的时间因素在这里成了一个个碎片。这种时间的断裂导致小说情节的不连贯性,同时也拉大了人生的喜怒哀乐,极大地凸显了深沉的生命意识。
《呼兰河传》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小说常在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不断切换。如:“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儿丈K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这是小说的开端,这里,具体时问被隐藏了。小说中描写的年复一年的“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单调地重复着。呼兰人的“生、老、病、死”都足那么的自然,他们在死人埋好之后,那活着的人“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地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了个不休。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了。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这样地过去了。”整个过程完全没有清晰的时间概念。然而时间的不确定,却给小说带来了高度概括的可能性。
《呼兰河传》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或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一个个画面和场景的描写叙述,展现生活的本真状态。而这些零散的场景给了作者发挥的空间,更有利于加入大量的图威场景,从而使小说里到处充斥美丽的图画效果。胡适曾批评说“伞篇显得足一些散漫的素描。”而正是这些“素描”显现出作者的绘画化追求。
二、绘画因素的多层面呈现
萧红在中学时曾学过画画,具有良好的美术素养,绘画美也是促使她小说诗化十分重要的内在因素,这也是她小说的绘画化追求的诱因。中国画求神韵而不重形似,多用象征而少用写实。沈从文在《断虹》里说,“我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景画集成”。萧红在小说中努力实践着这种绘画追求,构图、色彩,甚至画外的意境,作者都凝聚着百般的热情去构建,使之成为一幅幅永不褪色的域卷。《呼兰河传》中随处可见意韵深远的画境,真正实现了叙事艺术、诗歌艺术、绘画艺术的深度融合。
首先,在场景的描摹中,她富有强烈的构图意识。
在《小城三月》里就有过这样的描写。“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这是一幅色彩凄凉的墓穴图。“草籽芽”“粘成一片的土”“淡青色的坟头”“白色的山羊”组合起来,寄寓着“我”悲凉的忆旧之情和作家自己的身世之叹。
像这样情画交融、意境深远的精彩段落在《呼兰河传》中随处可见。“每到秋天,在篙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寥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蜒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文中通过“秋天”“蒿草”“蜻蜒”“蝴蝶”几个鲜明的要素构筑了呼兰小城的荒凉,作者实际是告诉人们,生活在荒凉家园里的呼兰人的精神也是荒凉的。
再如,“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冒着烟,雨本来下得不很大,若一看那蒿草,好像那雨下得特别大似的。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迷漫得朦朦胧胧的,像是已经来了大雾,或者像是要变天了,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混混沌沌的,在蒸腾着自烟。”几句话中,“蒿草”“烟”“毛毛雨”“大雾”“霜”构筑了一幅朦胧的图画,写出了院子的荒凉。
其次,作者创设的画面色彩丰富,极具美感,像是用画笔一笔一笔勾勒着作者理想中的画面。比如第一章描绘呼兰河城的火烧云的图画可谓色彩绚烂,“地面上是红通通的小孩子的脸,红色的狗,金色的公鸡,紫檀色的母鸡……天上是红堂堂的、金洞洞的、半紫半黄的、半灰半白合色的等等各色变化着的火烧云。”这还是一幅动态的图画,不仅云的颜色在变,而且云的形状也在变,“一会儿像匹马,一会儿变成了凶猛的狗,不会儿又成了一只大狮子了。”作者在用单纯的画笔作画,却画出美妙绝伦的景致,让人惊叹。
再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写道:“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蜒、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色彩之丰富,可谓达到极致。
再次,作品中展现了浓重的的色彩隐喻。
萧红在小说里明显传达着一种“色彩意识”,常常有大密度的色彩涂绘,更善于通过色彩表现某种象征或隐喻。她喜欢和歌颂象征温暖和爱的红、黄、绿,而厌恶、憎恨、否定相当于冰冷和憎恶的黑、白、灰。《呼兰河传》更多的是对“灰色”的描写。“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到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的气象。”“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在灰白色的背景下拉开了整部小说的序幕,也渲染了整部小说的氛围。
作者笔下的呼兰小城充斥着黑白灰世界,而小团圆媳妇们正是生活在这张灰白大网之中,她们代表的温暖色调和呼兰小城的灰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隐喻出作者心中的悲怆和浓郁,形成巨大的心灵震颤,传递着浓浓的悲情。结尾处黑色的乌鸦和白色的灵幅的强烈对比更加凸显了作者的这一美学意图。
三、民风习俗描写增强了小说的风俗画色彩
民风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的心理寄托方式。民俗中往往能透视出世间百态,’萧红在小说中十分重视对东北民俗的描写,有时甚至不惜中断情节。在《呼兰河传》中,作者正是通过呼兰小城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凄清婉丽的风俗画。
作者在小说中向我们展现了呼兰人大量的民俗,将跳大神治疾病、放河灯送冤魂、逛庙会求子孙、唱秧歌、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诸多民俗都写得娓娓动人,写出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浓浓的民间烟火气息。为此,茅盾誉之为“一幅多彩的风土画”。
同时,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于民俗描写中,看到了积淀在他们身上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呼兰河畔人们的愚昧,在遥远的呼兰河小城里,生命的存在方式是如此地混沌且处于非自觉的状态。也对他们的麻木、自私,有时甚至是残忍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这时,她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诅咒,而是扛起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大旗,促使读者去审视几千年传统文化中腐朽意识毒化人们灵魂的真正原因。这也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大量民俗的又一意图。
歌德有句名言:“必须把写实的东西上升到诗的高度才行。”也有一些研究者称萧红小说是“文中有诗,文中有画”。正是绘画因素在其中的渗透,使得作者在创作中如鱼得水,尽情抒写着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份感动。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A],萧红全集(上卷)[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2]杜玲,论萧红“越轨的笔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4
[3]沈巧琼,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特征[J],广州: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第24卷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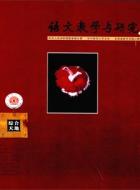
- 如何激发初中生的阅读兴趣 / 蒋兴娟
- 还原生活真实 个性解读文本 / 董书芝
- 平安夜 / 顾前
- 实现寓言的艺术手法 / 夏元明
- 对《文心雕龙》文体观的解读 / 郭艳珠
- 论《学记》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 高静
- 多元化评价学生作文探微 / 季国英
- 基于对话理论的阅读教学实施策略 / 马世海
- 论写作教学中合作学习策略的运用 / 常翠
- 议论文写作随感 / 姜志岗
- 关于作文教学有效性的几点建议 / 王亚敏
- 阅读教学呼唤精彩的对话 / 柏千风
- 浅谈高考作文如何出彩 / 万利芹
- 坚守自我 个性阅读 / 费彦芳 彭 静
- 个性化作文的要求与方法 / 田宜华
- 多样化写作教学实践的探索 / 邓晓丽
- 初中作文现状及应对策略 / 陈立新
- 诗歌鉴赏中的几个术语 / 段学政
- 做景与作文 / 罗先奎
- 意境与风格的区别 / 程萍
- 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 刘兴华
- 找准复习切入点 写就考场规范文 / 潘卫成
- 新阅读下的个性写作 / 于卫成
- 如何增强课内作文指导的实效性 / 张海英
- 强化“读”的意识 培养“悟”的能力 / 赵世坡
- 勤于积累 抒写真情 / 王雪梅
- 课前口头作文教学的一种尝试 / 王梅花
- 试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关怀 / 吴明为
- 中职语文有效性教学举隅 / 李兆民
- 语文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导』 / 王盈盈
- 语文教学中的问题与思考 / 张洪峰
- 在小说教学中介入影视手段 / 杨舒慧
- 语文个性化学习促进策略初探 / 朱恩定
- 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训练 / 宋苏杰
- 语文教学与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 刘子锐
- 在比较中学习语文 / 刘金顶
- 初三语文教学中的加减乘除 / 成丽君
- 语文教学如何教出语文味 / 陈小云
- 怎样使备课设计有深度 / 许怎红
- 巧用网络学语文 / 邓素梅
- 课堂教学中的设疑 / 王树芳
- 让学生体验学习的快乐 / 郭文菊 郭文梅
- 课堂教学有效性初探 / 龚小群
- 语文课堂教学要善于营造磁场 / 吴永君
- 语文教学课堂延伸的重要性探讨 / 童孝平
- 生态语文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 蔡丽霞
- 语文高效课堂的起承转合 / 吉顺武
- 点击课堂品质 展示语文魅力 / 肖庭兰
- 语文理想课堂的构建 / 陶振环
- 应对课堂上意想不到的质疑列谈 / 刘晖
- 巧妙设计 成就精彩课堂 / 淡娟
- 语文课堂预设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 陈桂海
- 高效课堂没有“看客” / 朱加银
- 古典诗词教学的朗读艺术 / 仇美丽
- 高超的劝谏艺术 / 殷大荣
- 语文味与多媒体的抉择 / 李尽海
- 高职语文汉语应用能力教学新探 / 邵家勇
- 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微 / 李晓碧
- 希腊海神波塞冬与中国四海海神之异同 / 孙丽
- 《呼兰河传》中的绘画追求 / 徐君善
- 试论语文活动课的实效性 / 杨加萍 殷金河
- 张爱玲作品中的『颜色』 / 沈丽洁
- 教师课堂机智例谈 / 李俊 魏国
- 《陪读》的解构意味 / 周聪
- 让语文课堂在师生的交融和碰撞中绽放 / 陈志贞
- 《给李风叔叔帮忙》的对比新用 / 黄春黎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吴吉珍
- 《梅花岭记》对话析微 / 曹如银
- 试论《社戏》中的美 / 曹利玲
- 浅析阿Q形象的悲剧意义 / 孙发根
-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 刘淑云
- 从《报任安书》中获得的启示 / 关凤
- 《蔚蓝的王国》教学设计 / 袁国
- 简析祥子命运三部曲及成因 / 徐应华
- 《信客》教学实录 / 程建波
- 《夕阳真美》文本解读 / 祁亚琴
- 《醉花阴》公开课课堂实录 / 徐培宏
- “策勋十二转”另解 / 杨建忠
- 《屈原列传》教学反思 / 许维英
- 《琵琶行》中“江”与“月”的意象 / 洪春燕
- 中职语文教学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 唐晓堃
- 语文教学五个『丢不得』 / 陈佃红 唐晓红
- 清泉 / 陈兆刚
- 愿教育多散发一些芬芳 / 王德凤
- 初秋的菱角湖公园 / 李鑫阳
- 还语文应有的地位 / 李志宏
- 用先进文化凝铸和谐校园之魂 / 胡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