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5期
ID: 422744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5期
ID: 422744
归程何处
◇ 罗艳梅
摘要:作为“秦淮八艳 ”之一的柳如是,一身傲骨,才气纵横,志在家国。自我觉醒后的她主动追求自由、独立和个人价值,但现实的残酷使其认识到自我身份无法带来其所追求的一切,最终她选择以依附的形式实现个人有限的独立和自由。
关键词:柳如是 赠别诗 自我意识 独立
引言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名隐,又改名为是,字如是,号河东君。柳如是传世的赠别诗不过十篇左右,且主要集于《戊寅草》《湖上草》两部诗集中。这些赠别诗创作于柳如是艳名大炽、广交名流、诸段情缘和明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的历史阶段,也正是河东君自我意识朦胧觉醒并做出努力和挣扎的时间段。这一时期后,便是柳如是儒服访半野堂的行为选择和人生走向。
一、天下豪雄游侠的激赏
柳如是传世的赠别诗,无论是《赠友人》还是《朱子庄雨中相过》还是其他赠别的篇章,伟岸的强有力的男性形象一直是诗人倾慕激赏的对象。“他”壮怀激烈、意气飞扬、才能卓著、以身许国,正是一伟男子,真英雄。然而在此男子“强”和“力”这两大特质外,似乎还游逸于正统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观念之外,拥有一种游侠的气质和精神。
对游侠的定义自古就存在争议,但游侠的一些特质却是得到公认的:见不义而起;受恩勿忘,施不望报;振人不瞻,救人之急;重然诺而轻生死;不矜德能;不遵礼教。千百年来,游侠精神,正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所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赠宋尚木》里那个读书射猎、傲视功名权贵而又重然诺轻生死的男子,每一处都显现出少年游侠的任侠风姿。而“朱郎才气甚纵横,少年射策凌仪羽。岂徒窈窕扶风姿,海内安危亦相许”(《朱子庄雨中相过》)的“朱郎”重然诺而轻生死,以救天下为大义,分明游侠之行。
《送别二首》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为柳如是送别赴京赶考的陈子龙所作。无论柳氏送别的是否为陈子龙,但根据两首诗的情感表达,对象为柳如是深情眷恋之人当无疑。
在第一首的惜别与嘱咐之后,柳氏没有凄凄而语而是超脱一般的女性话语,道出了激励之言。在她看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乃为实现“大道”之道,虽然不舍,但诗人还是鼓励男儿志在家国,“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因”。最后,诗人以“游侠”视之爱人,告诉即将远行的爱人,游侠志在四方、不惧远途,此时全诗豪气顿生,在缠绵之外更多了一股阔大的气魄。在诗人的理想之中,她的爱人当拥有游侠精神,自由、独立、扶危救弱、报国安民。
河东君诗中的游侠无疑具有部分传统救世的英雄气质,正气凛然、甘赴国难,重义轻生。游侠是自由主义者,他的心中道义和自由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报国救民之外,他对于世俗的种种规则持轻视的态度而能对世上之人皆平等相看、等同相待。他们有鲜明的个性,追求自由和独立,不受世俗准则的束缚。不矜德能,不眷恋于高位厚禄。在《赠友人》一诗中,柳如是道“一朝拔起若龙骧,身帅幽并扶风儿”。古代幽、并二州之人尚气任侠,多豪侠之士,因而诗歌中常以“幽并儿”代指任侠、豪侠。
总的来说,柳如是赠别诗中的男性形象是极其复杂的,他拥有儒家式“大丈夫”的气质,同时也蕴含着游侠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在晚明的风气下,文士固然风流潇洒,却缺乏一种豪气与霸气,柳如是的赠别诗中所书写的俊爽豪侠的男性既是对友人、爱人的赞美,更是一种激赏和砥砺。毋庸置疑,他高于真实赠别的对象孙临、朱茂景、曹溶等人,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是想象的产物。然而,这一形象事实上也是柳如是对自我的一种隐性书写与期待。
二、琉璃梦碎的沉痛
柳如是的赠别诗篇充满双向互动,在这种双向互动中,男性形象和诗人本身的内心逐渐展露,诗歌展示给我们诗人和诗中的豪杰游侠是难得的知己,“天下英雄数公等,我辈杳冥非寻常”,他们引为同调,灵犀一气。柳如是是一身侠骨才气之人,陈寅恪先生故称其为“女侠名姝”。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同样地在现实面前显得逼仄无奈。傅青主就认为,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无异。故而,诗中的男性形象在某种程度是柳如是的自画像。
在男权社会,名妓较闺秀所受的伦理道德的束缚和限制要少得多。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记道柳氏“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柳如是等名姝面对比闺秀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人生经验得以更加丰富,生命体验得以复杂深入,也让她对自身有更大的期待。
名妓之所以所接受的有制度规定的限制较少,是由于一方面男权社会将她们排除于社会秩序和伦理框架之下,从而成为在正统社会看来“不存在的存在”(以满足男性的自身欲望);而另一方面,为维持男性社会的稳定性,她们又被置于伦理的重重压迫之下,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晚明之前,女性往往停留在追求爱情和人生的自由方面,她们的目光驻留在自身。但柳如是以更宽广的心胸、更高远的抱负跳脱伦理道德所规定的女性空间,不仅从爱情层面追求个体独立自由,更从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政治层面解放和实现自我价值。
在《初夏感怀》中她感叹“千金元节藏何易,一纸参军答亦难。位于荥阳探龙蛰,心雄翻是有阑珊。”女子即使心雄万夫,但终究壮志难酬。故而,在柳如是赠别诗中充满了有志难伸、夙愿难酬的痛苦和惆怅。“我徒壮气满天下,广陵白发心恻恻”,这是其书写的豪杰所不能摆脱的痛苦。从中我们虽能感到柳如是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和赞赏,却也摆脱不了那无处不在的忧伤与痛苦。进,不得有任何施展才华的舞台;退,则不甘亦不愿。
《朱子庄雨中相过》言“我辈杳冥非寻常”,但事实上,无论是诗中的男性还是现实中的男性都不可能真正与柳如是这样身份的女子成为同辈,这是欺人也是自欺。种种世俗的规则如鸿沟将彼此隔在了世界的两端。傅青主有言:“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名士落魄,但仍有在某种情境实现理想,其发展自己价值的权利和能力并未被夺取,可以千秋垂美名,四海争心期。
不难发现在《赠友人》《赠宋尚木》等篇章中,诗人对诗歌中的男性形象充满了期待,也充满欣羡,而对自身却显得有几分自卑与怀疑以及对前途的深沉忧患,“时时怅望更叹息,叹吾出处徒悲伤”。
三、独立之路与依附之痛
柳如是赠别诗对于自身男性化一面的不断强化,便存在在男性面前对自身女性身份的一种自卑与否定的原因,诗人向男性强调自己与他们是相同的,以希求获得平等的角色定位和人生舞台。在自卑与怀疑、否定传统却又难以突破现实的困境,一部分觉醒女性选择了退避自守,或退居红楼,或飘泊江湖,或青灯古佛。与柳如是同一时期的才妓王微感叹“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尤事一室。参诵之余,一言一咏。”高傲如王微也只能对“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的境遇屈服而名其诗集为《焚余草》。
在近乎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另一部分自我意识朦胧觉醒的女性采取了“取悦”并效仿拥有强权的男性的方式,在文人前淡化抹杀自身的女性身份而采取“文人化”行为和赞誉男性以融入男性团体、取得近于男性的地位,以实现己之抱负和价值。柳如是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时,独立与依附成了解不开的结,相互缠绕。
早在魏晋,王孝伯便号称:“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名士的标准很难统一,在诸多融入男性的手段中名士姿态无疑难度较低,做到真、做到傲再有几分才情便已有了几分名士风致。明朝中期以后,士人对“情”之一字重新重视起来并有了自己的理解,也产生了当时一大批追求真性情的名士,他们自豪地歌唱“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因此,在晚明社会,名士化的女性更符合当时文士对名妓的期待与想象,而名士之风与柳如是等人本身的性格就有相契合之处。
后世之人多津津乐道于柳如是、钱谦益白首红颜,感深相知,欣羡于其惊世姻缘,当是时,柳已23岁,对女子来说美好华年已无多,而同时由于其与谢象三绝交,故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多年后柳如是言:“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靡,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债负不赀,交游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事佛。”此时的柳如是必须找一个能够托付终身的人,而早已心慕柳如是的钱谦益无疑是相对而言的“最佳选择”。
对于情感,柳如是是执着、坚定而独立的,但她的心底却始终充满了散不去的担忧。她高度理性,对于世人凉薄和爱情的出路有着清醒而痛苦的认识。与在《赠友人》等诗所反映的坚定倔强而刚强的一面相反,在有关离别的词与赋中认识到,分别必然更多是红颜对离别和分离的悲叹凄语,“不是情痴还欲住,未曾怜处却多心,应是怕情深”。几度情殇后,柳如是退却了,不再执着于两心相知,两情相投的纯粹爱情。
在初访半野堂时她奉赠诗钱谦益言“近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不辞从”,以谢安喻钱谦益,以东山妓说自己,并“不辞相从”,这是柳如是前期的诗歌中所没有的一种卑微的姿态。在《戊寅草》《湖上草》的赠别诗中,在庚辰访半野堂前,柳如是与诗中的男性形象和日常所交往的文人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相互欣赏相互鞭励的知己。而在此时,却成了东山妓相从谢安的关系,云泥之别的差别中,有退却,有无奈,有伤痛。语
参考文献
[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明·楪权.贤博篇·奥剑篇·原李耳载[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柳如是.柳如是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刘燕远.柳如是诗词评注[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5]柳素平.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J].史学月刊,2006(06).
[6]谭德红.侠气·才气·骨气——试论柳如是作品的须眉之气[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01).
[7]刘琪莉.侠女柳如是与晚明声色文化[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1(05).
[8]郭皓政.论人学和文学上的柳如是[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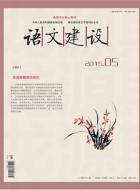
- 言语体裁理论研究 / 付晓
-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浅析《纯真年代》 / 杜冰月
- 当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杨军
- 浅析新疆少数民族预科汉语教学模式 / 郭美玲
- 华裔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解读 / 刘畅
- 以生为本,点亮语文课堂 / 孙火丽
- 励志文学作品阅读与大学生德育的融合 / 但家荣 朱兰
- 基于培育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经典诵读 / 王素娟
- 萨克雷《名利场》中的人物分析 / 胡艳
- 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月亮意象差异比较 / 刘琳
- 认知语言理论下《傲慢与偏见》的篇章解读 / 卢丙华
- 女性主义视域下《钢琴教师》人物形象塑造研究 / 王盈盈
-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文学价值研究 / 闰从山 杜鹏
-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赏析济慈的《秋颂》 / 封娇
- 女性主义理念中简·奥斯汀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 / 张智明
- 论《无名的裘德》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 吴佩君
- 浅析爱伦·坡文学创作中的死亡之美 / 朱君梅
- 穿透生命温度的视线 / 刘佳人
- 语用视角下对《警察与赞美诗》的解读 / 唐余俊
- 冷雨中的文化寻根 / 王芹
- 理性与人性 / 周晓春
- 欧·亨利小说的创作风格及其语言特色 / 田晓芳
- 态批评视域下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解读 / 熊蕾
- 《哈利·波特》中蕴含的时代特点及文化渊源 / 王敏
- 《外婆的家当》中的文化语境解读 / 刘文俊
- 看《名利场》与《围城》两部作品的异同 / 欧阳娜
- 童话般的故事 / 王英
- 看《聊斋志异》叙事意象的艺术魅力 / 伍双林
- 归程何处 / 罗艳梅
- 以文化角度为切入点评析《四世同堂》 / 王颖
- 试析《呼啸山庄》旁观式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创新 / 任伟亚
- 中国与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 / 陈珊 王瑾
- 论广告语借鉴和传承古典诗歌的实绩概述 / 杨莉
- 《道德经》的文学价值及德育启示 / 赵雪 张博
- 解析《论语》独具文化本源的叙事特点 / 阳卓军
- 先秦文学中体育意象语言描写研究 / 曾伟
- 对言语社区进行语感测量的新视角研究 / 刘亚楼 景淼淼
- 优选论视域下的句子主语研究 / 尚光琴
- 从同位短语来看复合词的构词方式 / 张然
- 英国作家王尔德文学作品语言研究 / 单雅波
- 修辞学视野中马克·吐温文学语言研究 / 杨丽君
- 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声调习得实验研究 / 常乐 刘飞 董睿
- 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 / 郭娟
- 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创作语言风格 / 王金玉
- 语意视角下“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分析 / 马芝兰
- 修辞结构理论视角下的语篇结构分析 / 胡茵芃
- 语用学视角下对《名利场》人物对话语言的解读 / 于嘉琪
- 语言经济学的定义争端 / 郑丽萍
- 跨文化视角下古典文学对外翻译传播的研究 / 彭东晓
- 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规范化研究 / 徐峰
- 语言模糊问题在文学翻译中的研究 / 原灵杰
- 大学语文的思想教育功能与实现路径 / 王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