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5期
ID: 422716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5期
ID: 422716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浅析《纯真年代》
◇ 杜冰月
摘要: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门年轻但极富生命力的新的理论体系,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创始者和领军人物。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叙事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她的重点在于把文学作品语境化 、性别化,同时引入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具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则。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叙事学中作者型声音和女性形象与男性声音两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一下伊迪斯·华顿的《纯真年代》。
关键词:社会风俗小说 《纯真年代》 叙事学 作者型声音
引言
伊迪斯·华顿出生于纽约上流社会,和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同属“风俗小说家”,她的文体明丽自然,优美雅致,堪称是19 世纪末美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女作家。凭借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她的很多社会风俗小说深刻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具有道德洞察力和很高的美学价值。《纯真年代》作为华顿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展现了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的全景,旨在引起人们对当时女性地位的重新思考。该作品曾获普利策奖,文笔优美且结构精巧,有力地渗透了华顿的创作意图,尤其是其想表达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主题意义深远。伊迪斯·华顿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她的作品却关注那个时代的女性问题,从女性视角出发,审视女性心理情感,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特色,其中以《纯真年代》为代表。在那个男人凭借性别建立的男权体制社会,华顿质疑男性权力,借《纯真年代》表露了女性不甘沦为悲哀而发出的反抗声音和日益觉醒的女性意识。
1986年,苏珊·S·兰瑟首次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发表了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从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欧美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女性主义叙事学从作品的情节、结构、人物等方面着手,分析性别对叙事的影响。与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比较,女性主义叙事学更注重对于文本的细读,倾向于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女性主义叙事学也不同于经典叙事学,突出表现在它把文学作品语境化、性别化,这是叙事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它丰富了西方文论,同时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阈。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性别因素,把女性叙事经验视为叙事文本分析的基础,同时引入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具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则。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
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门年轻但极富生命力的新的理论体系,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创始者和领军人物。苏珊·S·兰瑟把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且几乎没有发生任何联系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有效的融合,把原本属于结构主义的叙事学融入自己的作品里面,创立了发展势头强劲的跨学科流派——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突出贡献,苏珊·S·兰瑟曾任教于乔治敦、马里兰大学。“曾获美国马凯特大学学士学位,威斯康辛大学硕士学位,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兰瑟主要从事18、19 世纪英、法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及妇女和女同研究,尤其是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开创有突出贡献。”[1]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鲜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1年,兰瑟率先在《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文评相结合,第二个阶段是1986 年,兰瑟首次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发表了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自此之后,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欧美的发展势如破竹。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丰富了西方文论,使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将经典叙事学理论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构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女性主义叙事学吸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和观点,同时挣脱了叙事学崇尚形式、疏离文本的枷锁,对“叙事”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特点是分析性别与叙述的关系,关注人物、情节、叙事过程,通过分析性别对叙事的影响,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事形式的影响。叙事空间、叙事结构、 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等多个层面的定向研究都包含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其中尤以叙事声音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改变脱离语境、 男性化的叙事语法和女性边缘化的局面,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把焦点放在了叙事结构上面,从性别这个角度来考虑结构差异。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叙事模式、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这些都和声音休戚相关。
女性主义叙事学自被提出并运用之后,其新颖的视角、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并推动着叙事学的发展,它的价值一目了然,当然它的发展势头也一直很乐观。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女性是叙事主体同时又是叙事客体,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其本质所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叙事文本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丰富了叙事学理论,在多学科交叉的层面上做出了自身的贡献,为西方文学评论带去了新的希望。
二、《纯真年代》与女性主义叙事学
(一) 作者型声音
叙事声音简单来讲就是叙事者的声音,所以要解决“谁在说话”以及“谁在讲述”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兰瑟将叙述声音区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三种。第一,“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处于故事之外的作者是叙述者,并且叙述者会将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作者的叙事意图结合起来,此时作品之外的读者便是受叙者,这是一种“集体的、 异故事的且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第二,“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为同一人,这和作者型声音截然不同。第三,兰瑟对“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区分为经典叙事学模式带去了福音,丰富了其内容和模式。
作者型叙事声音是《纯真年代》这部作品的重要特征和特色,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以纽兰视野为中心。因为声音对情节的推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为了达到阐释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如何获得话语权利的叙事立场这一目的,作者用纽兰的所见所闻所说所为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纽兰的眼里,梅的形象是美丽清纯、端庄大气和枯燥呆板,而艾伦却是独立自由、豪放不羁和活力妩媚的代表。在故事里,梅和艾伦是部分或全部丧失话语权的“非叙述性人物”,但是作者却经常利用作者型叙事声音为艾伦说话,增加读者对艾伦的喜爱和同情。在文本中,华顿嘲弄了梅的虚伪和自私,同时也讽刺了纽兰的自以为是和挑剔苛刻,但是作者从未丑化过艾伦。华顿对艾伦的强烈同情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密切关注也正是借《纯真年代》里作者型叙事声音所表达出来了,同时,《纯真年代》里作者型叙事声音也明显而细致地表达了作者华顿对艾伦的欣赏和赞美之情。例如,“奥兰斯卡夫人面朝鲜花半倚半坐,一只手托着头,她那宽松的袖筒一直把胳膊露肘部。……晚上在气氛热烈的客厅里穿戴毛皮,再加上围拢的脖颈和裸露的手臂,给人一种人性与挑逗的感觉。但不可否认,那效果却是十分的悦人。”[2]华顿在《纯真年代》里一直都是用赞美的角度来描写艾伦的,作者用了各种好的、积极的、正面的和细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热烈的声音来描画艾伦的形象的。
(二) 女性形象与男性声音
《纯真年代》中女性人物通过男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天使”或者“怪物”。纽兰是文本中的观察者,他眼光挑剔地审视着女性,在他认为,梅美丽端庄却又似乎呆板幼稚,艾伦生活自由不羁却又不合规范。伊迪斯·华顿以纽兰的口吻,在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的同时,也反应了她对残酷的男权社会深刻的体会和观察,以及她对女性现实的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文本中梅是传统思想的化身,她具有保守的女性主义思想,受社会和历史环境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她扮演了男权社会制度维护者的角色,因此梅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梅也是一个在有限条件下尝试主宰自己命运的反抗者。在故事里,虽然梅知道纽兰欺骗了自己,但梅仍然只是镇定地对纽兰说:“你可不要认为一位姑娘像她的父母想象的那样无知,人家有耳朵,有眼睛——有自己的情和思想。”[3]梅对纽兰的欺骗十分愤怒,但是她仍然愿意给纽兰机会选择,同意纽兰追求自己的内心所想要的生活。这也说明了梅没有像那个时代其他的所有女性一样沉默和忍受,但是梅的反抗没有成功,她最终还是沦为了男权社会的产物。
但是伊迪斯·华顿对梅的描写和塑造也可能是她保守思想的反映。“梅的胜利很可能是华顿保守思想的反映,华顿还是很赞成传统的家庭模式并赞扬女人们在维护传统道德和维持家庭方面所作出的努力。”[4]伊迪斯·华顿冷静地批判了作品中男性人物的指手画脚、挑剔的性格,不动声色地讽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做作,彰显了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伊迪斯·华顿掩饰女性声音来突出强调男性声音的背后,体现了对男性文学潮流的迎合以及对男权社会的残酷的讽刺。
结语
《纯真年代》是伊迪斯·华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一直以来广受读者喜爱。众所周知,伊迪斯·华顿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她深切关注和思考女性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尤其在《纯真年代》这部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和深刻。伊迪斯·华顿虽是一位女性作家,但是她却有很深沉的历史感和极度敏锐的观察力。在勾画作品中的人物时她永远笔触冷静,语言优美,对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叙事技巧的灵活运用程度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作品中声音的独特而又恰好的运用,产生的不同层面下的多重叙事效果以及其美学价值和个性化特点,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华顿虽然同情、关注女性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但是她却从未给女性摆脱现有命运提供任何方向。 在《纯真年代》里,她批判男权主义,作品中也到处洋溢着她的女性意识,但是她却从未真正地塑造一个具有榜样力量的“新女性”形象,就连她所偏向和极力赞美的艾伦也不是。语
参考文献
[1]王茜.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探微[D].辽宁大学,2011.
[2][美]伊迪斯·华顿.纯真年代[M].赵兴国,赵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91-92.
[3]伊迪斯·华顿. 纯真年代[M].赵明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4]张晓青.绚丽的火百合——评《纯真年代》中的女性形象[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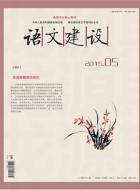
- 言语体裁理论研究 / 付晓
-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浅析《纯真年代》 / 杜冰月
- 当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杨军
- 浅析新疆少数民族预科汉语教学模式 / 郭美玲
- 华裔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解读 / 刘畅
- 以生为本,点亮语文课堂 / 孙火丽
- 励志文学作品阅读与大学生德育的融合 / 但家荣 朱兰
- 基于培育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经典诵读 / 王素娟
- 萨克雷《名利场》中的人物分析 / 胡艳
- 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月亮意象差异比较 / 刘琳
- 认知语言理论下《傲慢与偏见》的篇章解读 / 卢丙华
- 女性主义视域下《钢琴教师》人物形象塑造研究 / 王盈盈
-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文学价值研究 / 闰从山 杜鹏
-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赏析济慈的《秋颂》 / 封娇
- 女性主义理念中简·奥斯汀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 / 张智明
- 论《无名的裘德》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 吴佩君
- 浅析爱伦·坡文学创作中的死亡之美 / 朱君梅
- 穿透生命温度的视线 / 刘佳人
- 语用视角下对《警察与赞美诗》的解读 / 唐余俊
- 冷雨中的文化寻根 / 王芹
- 理性与人性 / 周晓春
- 欧·亨利小说的创作风格及其语言特色 / 田晓芳
- 态批评视域下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解读 / 熊蕾
- 《哈利·波特》中蕴含的时代特点及文化渊源 / 王敏
- 《外婆的家当》中的文化语境解读 / 刘文俊
- 看《名利场》与《围城》两部作品的异同 / 欧阳娜
- 童话般的故事 / 王英
- 看《聊斋志异》叙事意象的艺术魅力 / 伍双林
- 归程何处 / 罗艳梅
- 以文化角度为切入点评析《四世同堂》 / 王颖
- 试析《呼啸山庄》旁观式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创新 / 任伟亚
- 中国与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 / 陈珊 王瑾
- 论广告语借鉴和传承古典诗歌的实绩概述 / 杨莉
- 《道德经》的文学价值及德育启示 / 赵雪 张博
- 解析《论语》独具文化本源的叙事特点 / 阳卓军
- 先秦文学中体育意象语言描写研究 / 曾伟
- 对言语社区进行语感测量的新视角研究 / 刘亚楼 景淼淼
- 优选论视域下的句子主语研究 / 尚光琴
- 从同位短语来看复合词的构词方式 / 张然
- 英国作家王尔德文学作品语言研究 / 单雅波
- 修辞学视野中马克·吐温文学语言研究 / 杨丽君
- 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声调习得实验研究 / 常乐 刘飞 董睿
- 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 / 郭娟
- 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创作语言风格 / 王金玉
- 语意视角下“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分析 / 马芝兰
- 修辞结构理论视角下的语篇结构分析 / 胡茵芃
- 语用学视角下对《名利场》人物对话语言的解读 / 于嘉琪
- 语言经济学的定义争端 / 郑丽萍
- 跨文化视角下古典文学对外翻译传播的研究 / 彭东晓
- 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规范化研究 / 徐峰
- 语言模糊问题在文学翻译中的研究 / 原灵杰
- 大学语文的思想教育功能与实现路径 / 王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