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5期
ID: 42273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5期
ID: 422735
冷雨中的文化寻根
◇ 王芹
摘要:余光中作为中国文人,接受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他的“乡愁”以文化寻根为显在形态,其隐性内涵却丰富、复杂得多。《听听那冷雨》紧扣“听”字和“雨”字,驰骋想象,在跨越时空的联想与想象之中,集描写与抒情于一体,形象而传情地描绘了“雨与中国历史”“雨与中国文字”“雨与中国诗词”“雨与中国音乐”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完成了一次心灵上的文化寻根之旅。
关键词: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文化
引言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1950年迁居台湾,1974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并于同年写下了《听听那冷雨》这篇散文。1992年,终于得以回到他思念已久的大陆。余光中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说“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所以,余光中的“乡愁”情结,总是以大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是一种文化寻根的结果。以《民歌》《白玉苦瓜》《布谷》等为代表的诗歌,寻觅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声音和灵魂;以《听听那冷雨》为代表的散文,寻觅的是“乡愁”的文化之根。
作为一个文人,牵动他“乡愁”的往往不是政治制度,也不是经济基础,而是剪不断、磨不灭、铭刻心底、融入血液的文化。余光中作为中国文人,接受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这就使他的“乡愁”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文化上的认同与制度差异之间的矛盾,种族上的相同与地域上的阻隔之间的矛盾,东西方文化撞击产生的矛盾,因此,他的“乡愁”以文化寻根为显在形态,其隐性内涵却丰富、复杂得多。
《听听那冷雨》全文紧扣一个“听”字,展开联想,思绪上溯千年;围绕一个“雨”字,驰骋想象,神游跨越万里。在超越时空的联想与想象之中,集描写与抒情于一体,形象而传情地描绘了“雨与中国历史”“雨与中国文字”“雨与中国诗词”“雨与中国音乐”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完成了一次心灵上的文化寻根之旅,从而深情地告诉读者:乡愁之根在民族文化之中,只有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下,才可以抚平乡愁,慰藉飘零的游子之心。
一、雨与中国历史——历史的乡愁
“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是文章的开头部分作者由雨产生的第一个联想。作者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联想?历史的黑白是造成作者与“古大陆”久违的根本原因,也是“乡愁”生成的根本原因。这是从“乡愁”生成根源方面进行的联想。
历史是一个政治大舞台,也是一个文化大舞台。作为政治舞台,它是冷酷无情的;作为文化舞台,它是温暖深情的。温暖深情的文化让冷酷无情的政治逐步地退居幕后,使历史呈现其应有的温暖和明亮,即使只有黑白两色,也不至于令人窒息。中国文化是灿烂辉煌的,它孕育出了“杏花春雨江南”的清新。
“黑白片”的历史阴暗、沉重、冷酷,是一个沉甸甸的背景,但挡不住作者的思念之情。25年的离别之情,那种沉重的背景已经淡去,凸显在作者心头的是对“古大陆”的“孺慕之情”。思念让人看到优点;情感让人忽略不足。对于“游子”来讲,“黑白片”“下着雨”的历史,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阴暗,而是“杏花春雨江南”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清新美好,那里有他的“少年时代”——未离开“古大陆”、还被称为“川娃儿”“五陵少年”的时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乡愁之根。
二、雨与中国文字——文字的乡愁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一种带有审美情感的文字符号,是华夏祖先聪明智慧的灵感记录,它是形象的,立体的,传情达意的,是华夏儿女心灵和希望的寄托。从造字方法上讲,“雨”是合体象形字,可以理解为“天上落下的水滴”(这是正解),也可以理解为“脸上的泪珠”(这是别解)。“雨”让这种载体由表义符号变为充满“云情雨意”的美好图画,它们有了灵性,有了脾气,成为海外游子传情达意的最佳媒介。余光中说:“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中文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美丽的文字”。《白玉苦瓜》的颜色里透着悠悠怀古情,《布谷》叫声里传达着款款思归意,《民歌》的旋律中承载着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冷雨”的潮润中浸透着拳拳游子心。这种审美效果的产生都应归功于美丽的中文。
由“雨”而想到汉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联想,像写诗一样,有跳跃性;但文断意连。余光中笔下的“雨”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意义上的“雨”,而是被赋予了特定内涵的文化意义上的“雨”,或者说是“杏花春雨江南”中的“雨”,是“丁香空结雨中愁”的“雨”。它如同“春草”“杨柳”等词语一样,已经成为诗歌、散文中的一个特定意象。所以,“雨”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就要通过“汉字”这种文化载体来表达,二者之间产生联想,也就顺理成章了。不止如此,“雨”与汉字的结合,派生出了许多新的字形,不仅丰富了汉字的形态,还呈现出特有的“视觉上的美感”。这是其他文字难以媲美的。
三、雨与中国诗词——诗词的乡愁
“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在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态中,诗词是最感性的表现形态,也是与“雨”关系最密切的形态。没有哪种形态能像诗词那样把“雨”表现得感性、多情,“雨”是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中一个多愁善感的不老意象。所以,余光中把“雨”看作“女性”。从《诗经》中的《风雨》,到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雨巷》,“雨”以多情的形象贯穿于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诗歌发展的历史有多久,“雨”的抒情形象有多久。面对知时节的“好雨”,诗人可以喜,因为它“当春乃发生”;面对孤独,人们可以借“雨”写“悲”,因为“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白居易《长恨歌》);面对寂寞,人们可以借“雨”抒“愁”,因为“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雨”成就了无数诗人,诗人又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净化、美化、情化了“雨”,让它成为一个抒情意象。
雨“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呼唤诗人们的灵感。诗人与“雨”的联姻,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现象——诗词人生、风雨人生,诗人的人生都是漂泊不定的,他们往往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王禹偁贬官黄冈,写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借听雨抒写人生;姜夔一生漂泊,深谙“商略黄昏雨”的滋味;蒋捷历经亡国之痛,于雨中听出人生况味。风雨给诗人们的人生造成了大不幸,却让他们的诗文大放光彩。
余光中在台湾厦门街住了20年,他在梦里寻根寻了20年,古典诗词是他寻根的得力助手。他总说自己是厦门人,是江南人,日夜思念“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含杨柳风”的杏花春雨,思念“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江南。作为一个中国人,余光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时刻不忘寻找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他到达美国,看着那蓝天,白云,雪峰,想到的却是“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的豪迈,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情趣”;到达台湾,在对故乡雨声回味的同时,想起的是晏殊“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元好问“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故国之思像雨声一样,点点滴滴,淅淅沥沥,无尽无止。
四、雨与中国音乐——音乐的乡愁
“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是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从雨到音乐的联想,是一种相似联想:二者都有节奏。但又不是普通的相似联想,与前面的其他联想一样,作者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形态联系在一起,这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已经化为作者的无意识行动,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自古以来,音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它与诗歌一样,是人们抒发感情的重要工具。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是表达自己独居的恬淡惬意;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是追忆自己的美好时光;白居易“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是感叹自己的“迁谪之意”。音乐大多与人物的命运关联着,音乐是无字的诗。余光中把“雨”看成是“一种回忆的音乐”,一方面是因为雨声有节奏、有韵律,“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更重要的是,“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能安慰作者的“乡愁”,能把作者带到温暖的回忆中。余光中在《民歌》这首诗中曾写道:“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具母性的鼻音”。音乐也好,民歌也好,都是用“母性”的鼻音唱出来的,听着这样“柔婉与亲切”的声音,会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安慰。
诗、乐、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形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评王维语),诗是无声的音乐,音乐是无字的诗,它们之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艺术形态之间关系的认识,作者在“听雨”之中,展开联想和想象,从历史到汉字,从诗词到音乐,还涉及到传统绘画(“米家山水”),让思绪浏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典型形态,借以慰藉自己的心灵,在文化寻根中找到了灵魂和希望的寄托。
结语
诗歌也好,散文也罢,作家总是喜欢以他熟悉的、有体验、有感悟的对象作为传情达意的意象。余光中作为受中西文化影响的文人,主张既“能够融贯中外,吸收外来的营养,又能保留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样才能成气候。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主动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便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借助文学的力量,通过深情的呼唤表达自己渴望统一的心声。因此,他的“乡愁”不是简单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思念一个“民族整体”,呼唤民族整体的“和合”。语
参考文献
[1]高军.《听听那冷雨》教学设计[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8(10).
[2]周良华. 冷雨之愁 冷雨之美——《听听那冷雨》教学简案及思路解说[J].语文教学通讯,2010(0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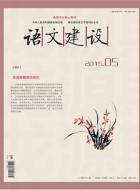
- 言语体裁理论研究 / 付晓
-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浅析《纯真年代》 / 杜冰月
- 当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杨军
- 浅析新疆少数民族预科汉语教学模式 / 郭美玲
- 华裔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解读 / 刘畅
- 以生为本,点亮语文课堂 / 孙火丽
- 励志文学作品阅读与大学生德育的融合 / 但家荣 朱兰
- 基于培育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经典诵读 / 王素娟
- 萨克雷《名利场》中的人物分析 / 胡艳
- 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月亮意象差异比较 / 刘琳
- 认知语言理论下《傲慢与偏见》的篇章解读 / 卢丙华
- 女性主义视域下《钢琴教师》人物形象塑造研究 / 王盈盈
-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文学价值研究 / 闰从山 杜鹏
-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赏析济慈的《秋颂》 / 封娇
- 女性主义理念中简·奥斯汀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 / 张智明
- 论《无名的裘德》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 吴佩君
- 浅析爱伦·坡文学创作中的死亡之美 / 朱君梅
- 穿透生命温度的视线 / 刘佳人
- 语用视角下对《警察与赞美诗》的解读 / 唐余俊
- 冷雨中的文化寻根 / 王芹
- 理性与人性 / 周晓春
- 欧·亨利小说的创作风格及其语言特色 / 田晓芳
- 态批评视域下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解读 / 熊蕾
- 《哈利·波特》中蕴含的时代特点及文化渊源 / 王敏
- 《外婆的家当》中的文化语境解读 / 刘文俊
- 看《名利场》与《围城》两部作品的异同 / 欧阳娜
- 童话般的故事 / 王英
- 看《聊斋志异》叙事意象的艺术魅力 / 伍双林
- 归程何处 / 罗艳梅
- 以文化角度为切入点评析《四世同堂》 / 王颖
- 试析《呼啸山庄》旁观式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创新 / 任伟亚
- 中国与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 / 陈珊 王瑾
- 论广告语借鉴和传承古典诗歌的实绩概述 / 杨莉
- 《道德经》的文学价值及德育启示 / 赵雪 张博
- 解析《论语》独具文化本源的叙事特点 / 阳卓军
- 先秦文学中体育意象语言描写研究 / 曾伟
- 对言语社区进行语感测量的新视角研究 / 刘亚楼 景淼淼
- 优选论视域下的句子主语研究 / 尚光琴
- 从同位短语来看复合词的构词方式 / 张然
- 英国作家王尔德文学作品语言研究 / 单雅波
- 修辞学视野中马克·吐温文学语言研究 / 杨丽君
- 巴基斯坦留学生汉语声调习得实验研究 / 常乐 刘飞 董睿
- 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 / 郭娟
- 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创作语言风格 / 王金玉
- 语意视角下“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分析 / 马芝兰
- 修辞结构理论视角下的语篇结构分析 / 胡茵芃
- 语用学视角下对《名利场》人物对话语言的解读 / 于嘉琪
- 语言经济学的定义争端 / 郑丽萍
- 跨文化视角下古典文学对外翻译传播的研究 / 彭东晓
- 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规范化研究 / 徐峰
- 语言模糊问题在文学翻译中的研究 / 原灵杰
- 大学语文的思想教育功能与实现路径 / 王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