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924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924
试论《百年孤独》的“狂欢”性
◇ 陆璇璇
摘要: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具有多重深厚的意蕴,其中之一便是它的“狂欢”性。马尔克斯站在拉美混合文化的基石上,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重点记述了孤独的狂欢,死亡的狂欢,非理性的狂欢,大自然的狂欢。通过对这些“狂欢”的描写,作者意欲探究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与自身生存的秘密。
关键词: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狂欢
引言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世界文学殿堂里的一部不朽之作,其非凡的魔幻现实主义魅力吸引了人们的狂热解读。小说被发掘出了多重意蕴,狂欢性便是其中之一。
巴赫金称赞狂欢节,认为狂欢期间的生活,是相对的,两重性的,脱离常规的。《百年孤独》里便有类似的狂欢场景。如吉普赛人的耍戏表演,奥雷良诺第二开办的一次次大型宴会,马贡多举办的女王选举及加冕仪式,梅梅和众多同学的家庭宴会等等。但是,小说的狂欢性不仅仅限于此,它具有更深层次、更广泛、更富有寓意的“狂欢”。《百年孤独》的“狂欢”,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凸显人事万物或抽象或具体的特色与内涵。
一、孤独的狂欢
自人类具有思想意识起,孤独便如影随形。顾名思义,《百年孤独》的主人公是孤独。马尔克斯用史诗的笔触,记录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兴衰,以及伴随他们的孤独。孤独无处不在,它是个人,家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情感体验。
小说中几乎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气质”是布恩迪亚家族成员的标志。“他们都带有落落寡合的神情,这种神情足以使人不论在地球哪个角落都能把他们认出来。”[1]第一代老布恩迪亚受吉普赛人影响,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竟奇迹般地推断出地球像个橘子。但家人及乡邻却把他当作疯子,在树上捆绑了老布恩迪亚的后半生。文中着墨较多的奥雷良诺上校,由于孤傲,他从小屋走向革命的风浪尖口;因为迷茫,他又把革命果实拱手相让,重新回到了小屋,孤独终生。乌苏拉是家族百年命运的见证者。她善良、坚毅、爱憎分明、任劳任怨,至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可就是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一己之力无法与厄运抗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滑向悲剧的深渊,她自己则在清醒的孤独意识中老去。他们都偏爱闭关自守,无论是在正常的生活中还是遭受事故后。如雷蓓卡在丈夫死后把自己深埋在屋里,直至老死;梅梅的恋情被母亲扼杀,极度悲伤的她麻木地接受了被关修道院的协定……孤独像一张严实的网,紧紧笼罩着布恩迪亚世世代代的上空。
孤独往往由众多冲突而起,布恩迪亚家族就是深陷在多种矛盾中不能自拔,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理想与现实的抵牾。这个羸弱的村庄是如此封闭、偏远、麻木、愚昧,承载不起开放、文明、改变,只能逐渐消失在外来物的一次次入侵中。以老布恩迪亚梦境命名的马贡多,根本不适合他们播种理想,到头来得到的只是失望与孤独的涩果。
马贡多的孤独代表了拉丁美洲的孤独。拉美处于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还未睁眼看世界时,西方殖民者就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从物质到精神,当地人在巨大而神奇的入侵力量面前茫然若失、手足无措。
孤独意识广泛而平常,但在《百年孤独》中,它却在狂欢。小说的孤独强烈而明显,它赤裸裸地充溢在人物的生命历程中,周而复始地导演一出出悲剧。孤独在狂欢,其摄人的威力足以使每个人窒息。
二、死亡的狂欢
拉尔斯·吉伦斯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授奖辞》中曾指出,《百年孤独》整个情节围绕着死亡——一个已经死亡,正在死亡,或即将死亡的人展开。作为“生”的对立面,“死亡”是小说的一大主题。马尔克斯用一种习以为常的语调来写“死亡”,还原了它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时,他又集中笔墨突出“死亡”,揭示出它随时随地的发生性。“死亡”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像在开一场“死亡”的狂欢。
家族中的每个人都活在先知默尔基阿德斯的“死亡预言”中。在这一总的死亡框架中,马尔克斯描写了多样死亡模式。其一是正常死亡,即人物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下,自然而然地衰老而死。如老布恩迪亚、奥雷良诺上校、乌苏拉和阿玛兰塔就是正常地寿终而寝。其二是非正常死亡。小说的人物大部分死于暴力,如奥雷良诺上校的十七个孩子全死于枪杀;第五代阿卡迪奥丧命于暗杀;香蕉园三百多名工人遭受了政府的屠杀。家族的女性多选择以活埋阻止自己的生命力,如雷蓓卡封死了门窗,以后从未踏出过屋子;菲达南不仅禁锢了自己本该美丽异常的生命,也把亲生女儿活埋在了修道院里。此外,正是豆蔻年华的蕾梅苔丝凋零在毒素中,第六代奥雷良诺被飓风卷走,最后一位长着猪尾巴的孩子被蚂蚁所吞噬……
更让人惊奇的是“死亡”之后的“死亡”。在马贡多世界里,人死后仍存在,以幽灵的形式继续生活,老下去,直至又一次死亡。如默尔基阿德在新加坡的沙洲上,在马贡多等地,不断地死去又复活,其灵魂一直驻扎在实验屋里。老布恩迪亚死后多年一直栖息在院里的大栗树下,乌苏拉常常因儿孙之事在他膝上哭泣。
这些离奇的死亡现象充满了魔幻色彩,既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又反映了人生都要谢幕的真实——死亡是任何历史中任何人的宿命。但是,马尔克斯不仅仅营造了对死的恐惧,更流露出对生的敬畏。表面看似生与死的对立,其实是二者的统一。所以,人要怎么活便成为永恒的话题。终点不可改变,路途却可由自己选择。死赋予生非凡的意义——爱恋生命,且行且珍惜。在饱受苦难的拉美大地上,作者见证了太多的死亡与毁灭,他用各种艺术手法使其在小说中一一重现。死神在马贡多狂欢歌舞,马尔克斯虽无法让其闭幕,却可以在狂欢中解说出生的意义。
三、大自然的狂欢
拉丁美洲被太平洋、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环绕,西边绵延着世界上最长的安第斯山脉,全洲一半被森林覆盖。葱郁梦幻的热带美景不仅哺育了当地居民,也让外来人陶醉不已。但同时,大自然的破坏力也让人惊秫不已。因拉美大陆坐落在五个地壳板块上,地震、火山喷发、雪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不断,一次次摧毁着当地的生灵。《百年孤独》虽未正面描写大自然的动植物与地质灾害,但马贡多奇特的自然风物与气候风雨,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热带大自然的图景。无论是美幻的动植物还是恐怖的自然灾害,全在这片大地上狂欢着,疯狂证明着大自然的神力。
早期的、未被入侵的马贡多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动植物在充足的阳光与雨水中开着“狂欢模式”,狂欢地生长,繁衍。布恩迪亚家的院子,也许是热带美景的代表。花园里载满了玫瑰,建有一条能遮风避雨的长廊,长廊外的栏杆上摆满了欧洲蕨与海棠花。香蕉园虽然被殖民者用来剥削工人,但其葱葱郁郁的绿意却是马贡多一道风景线,园子里的宁静仿佛来之另一个世界。然而,自然灾害时时破坏着马贡多。如下了四年多的大雨“空气是那么潮湿,甚至鱼儿也完全可以从门里进来,从窗子里出去,在房间的空气中畅游。”[2]雨停之后,十年内再也没下过雨,马贡多从此变为一堆废墟。此外,村落里还往往出现一些奇异的风物。如老布恩迪亚死后,天空下起了小黄花,“镇上下了整整一夜,小黄花盖满了屋顶,堵住了门口,闷死了睡在露天的动物。”[3]再如梅梅的男友身旁总是飞舞着黄色的蝴蝶,它们有时铺天盖地地弥漫着整间房屋。此外还有大批大批的燕子,一夜之间繁衍满院子的兔子,吞食一切的红蚂蚁……这些大自然的生灵,以其独特的生命形式,昭示了火热的生命力。它们往往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凝聚着从大自然攫取的力量,疯狂地生存着,灭亡着。
风雨雷电,植被生灵,给当地人提供充足资源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悦目的自然美景与惊心的环境灾害,都在小说中显示着震人的威力,开着大自然的“狂欢”。
四、非理性的狂欢
近现代科学技术催生了理性。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在他的著作《魔术、科学、宗教与理性的范围》中说,理性最大的诱惑,在于它能够提供其他知识形式、其他宗教信仰都无法提供的、最稳固的安全感。它清楚坚定地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排除掉,告诉人们此类事情不会发生,达到韦伯所说的“除魅化”的现代社会状况。然而,《百年孤独》却抛弃了“理性”的规矩,那非凡的人物,离奇的故事,迷幻的情节,多彩的环境,展示了一幅未被“除魅化”的、五彩斑斓的拉美图景。生活其中的人们往往躁动不安,心理扭曲,一任“非理性”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在《百年孤独》中,“非理性”的心理意识突出体现在人物的俄尔普斯情结上。“孩子的第一个爱的对象为他的母亲,在恋母情结成立时持续不变,以至终身。”[4]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情结往往受社会理性的压制而深藏心底。可是,在《百年孤独》中,这种心理似乎是自由的,它疯狂地在“非理性”的庇护下代代延续。乌苏拉和老布恩迪亚明明知道表亲结合的悲剧,却还是执意作了夫妻。从此,他们开启了家族的乱伦模式,其儿孙们总会爱上亲人或类似亲人的女性。如第二代阿卡迪奥爱上了母亲般的庇拉·特内拉,他俩的儿子又恋上了自己的生母。第三代奥雷良诺一心想与姑妈阿玛拉塔结婚,而第六代奥雷良诺却与自己的姨妈发生乱伦关系。“非理性”的情欲总会战胜“理性”的道德意念,后者在小说中是那么微不足道。
“被虐”心理也是“非理性”心理意识之一。“女人由于自己的体格和社会压制她们的攻击性,这便有助于发展强烈的被虐待冲动;而这种冲动转向于内的破坏趋势和本能相结合。”[5]正是源于此,布恩迪亚家族才上演了一出出女性悲剧。雷蓓卡和阿玛兰塔同时恋上了钢琴师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但雷蓓卡突然放弃了温顺俊朗的未婚夫,转而投向粗暴鲁莽的阿卡迪奥,甚至被逐出家门也在所不惜。阿玛拉塔终于等到了意中人的求婚,但她却毫无道理地一口回绝,最终造成了钢琴师的自杀事件。中年的阿玛兰塔被上校赫里奈多痴痴追求,明明心动的她却再一次否认了自己的情感,至死都未出嫁。这一出出爱情悲剧,归根到底是她们的“被虐”心理在作祟。这“非理性”的心理使行为与心意相违背,痛苦的快感压制着真正的快乐。
这些扭曲的心理,在小说中随处可见。“非理性”好像不受任何正常思想意识的规范,疯狂地诱惑其主人公作出超常规的行为。在“非理性”狂欢的背后,也许隐含着作者对人性本初的思考与探究。
总之,尽管一切都可以投入“狂欢”中,现代人却用理性压制自己的“狂欢”冲动,用科技遏制事物的“狂欢”意图。但马尔克斯却不屑于这样做。他在拉美大陆的混合文化基石上,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解开了“理性”的绳索,引导万事万物走向“狂欢”,并从中揭示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和自身的生存秘密。语
参考文献
[1]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宋鸿远译.北京:北岳文艺出版,2001:168.
[2]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宋鸿远译.北京:北岳文艺出版,2001:244.
[3]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宋鸿远译.北京:北岳文艺出版,2001:109.
[4][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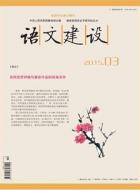
- 论阿克罗伊德与莫言作品的民族关怀 / 郭瑞萍
- 论卡夫卡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特征 / 徐利君
- “Mooc”时代高校基础写作教学的变革 / 柳杨
- 小学语文教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 万桂红
- 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 / 覃俏丽
- 留学生汉语写作课程任务教学方法研究 / 王犹男
- 基于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 王正中
- 论历史语境的甄选引入对古文史讲授的影响 / 李延玲
-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评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得失 / 姜瑞云
- 语言的文化功能对高校英美文学教育的影响 / 张婧
- 大学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作用 / 沈黎
- 语文教学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功能与优化路径 / 孔好为
- 成长视角下薇拉·凯瑟小说中的拓荒者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技术恐惧主义背景下的文学批评 / 邢凡夫
- 论澳大利亚文学的多元化创作研究 / 季戈宁
-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作家菲茨杰拉德的悲剧思想 / 刘小蓉
- 分析斯特恩《项狄传》的艺术特色 / 邹灿?曾剑
- 解读《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成长之旅 / 李敏?窦琴
- 剖析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叙事结构 / 牟英梅
- 自尊与反叛 / 杜磊?李哲?郭洁
- 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 李景
- 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浪漫主义手法解读 / 阙红玲
- 理想的方向 / 刁曼云
- 对顾拜旦《体育颂》的文学价值解读 / 胡朝霞?白侠
- 从《傲慢与偏见》解析简·奥斯汀的婚姻观 / 李慧?邹爱荣?赵青
- 海明威作品语言与写作风格研究 / 唐琛
- 《西风颂》赏析 / 乔玉芳
-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研究分析 / 罗丽娅
- 英美文学评论的文化差异探析 / 罗雨
- 刘庆邦小说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 盖伟
- 抗争与妥协 / 贺晓梅
- 试论《百年孤独》的“狂欢”性 / 陆璇璇
- 从不同角度看《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色彩 / 赵慧
- 郑观应的书法教育观 / 于有东
- 论宋代诗词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 / 叶向东
- 网络环境下的口语交际教学指导策略 / 耿红卫?李英
- 认知语言学理论下伍尔夫《到灯塔去》语篇探析 / 马红英
- 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词典比较与分析 / 高惠宁
- “登陆”与“登录”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 / 王定康
- 分析现代汉语中的对称结构及其句法功能 / 贾琼
- 论现代汉语新词汇在语言生态建设中的体现 / 朱萍
- 校园流行语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论析 / 陈亚芳
- 论模糊语的言语交际与语用功能探索 / 刘彬
- 新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功能与路径 / 陈志娟
- 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的作用探析 / 李军
- 人文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优化路径 / 吴琼石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两种模式评析与启示 / 孙英林
- 语文教学思维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 叶美丽
- 安全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莫莉秋
- 英语教学中汉语文化影响研究 / 王瑾丽
- 从《史记》中看刘邦的“人才观” / 张敏
- 汉语文化对英语教学的影响与改进路径 / 李旭
- 汉语对英语口语教学的负迁移及其应对机制 / 陈玲?何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