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893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893
论卡夫卡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特征
◇ 徐利君
摘要:工业革命将欧洲由宗法制社会拖入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但情感却愈发地隔膜。敏感的卡夫卡准确地把握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陌生与恐惧,并以崭新的变形、夸诞手法将之表现出来。
关键词:卡夫卡 现代主义
引言
卡夫卡是伟大的,他深刻揭示出十九世纪初期因工业文明发展而导致的异化现象,为“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奠基。本文拟先行厘定现代主义的理论外延,进而以卡夫卡作品为依据,并结合其创作主张、写作态度和生平经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主义
必须承认,谁都无法对现代主义进行精确的定义,现代主义并非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或一种创作主张,而是由许多具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派别汇成的一股文艺思潮,涉及建筑、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现代主义又称“现代派”,其在文学领域也分化出不同的流派,具体到卡夫卡,评论家则一般将其归入表现主义一派。当然,表现主义也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关联领域众多,甚至“表现主义”一词也是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埃尔韦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大体而言,表现主义认为人依靠感官(视觉、听觉等)所能认知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当然也不应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表现主义反对琐碎的自然主义和注重形似的印象主义写作,认为文学不应停滞于对偶然现象的记述和事物外形的摹写,而是应该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揭示人的灵魂以及表现作家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因而,表现主义的创作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扭曲和变形,着力表现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惶惑、陌生、孤独和恐惧,作品基调大都显得灰暗和阴冷。从艺术手法的角度,表现主义者认为直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人的感觉决定的,因而其创作中重视表现人“瞬间的直觉”,表现个人的感受和幻想。
二、卡夫卡的“现代性”特征
卡夫卡生于1883年,卒于1924年,而这个时段正是现代主义突破现实主义发展成熟的时间,卡夫卡以其创作切实地成为了现代主义观念在小说领域的践行者。
第一,对内心世界的细腻挖掘是卡夫卡创作的基本主张和作品的基本面貌。通观卡夫卡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作家的内心。在对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处理上,卡夫卡显然更重视个人主体的价值与内心的思考,他认为任何伟大的作品均源自对主体思想的细致挖掘,认为人的主观臆想和生存体验才是事物的本质,而作家也应该倾尽全力去表现这个本质。因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明显的时代标记,倒向是一个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寓言,读者无论身处何时何境似乎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迷茫与不安。《地洞》是作家诉说内心惶恐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绘了一只小动物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而不断想方设法布置地洞和机关,因为“意外遭遇从来没有少过”,甚至任何一个细微的响声都会令其感到恐惧。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工业文明发展初期,处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客观地说,这种“困境”在今日之中国也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弱势群体总会为他们收入低廉而又朝不保夕的工作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拨开一切现象的烟雾,直接表现现代社会的本质。
第二,“解释不可解释的事情”是卡夫卡的创作追求。不可否认,在现实的世界中,的确存在一些事物是人的常识和经验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物与科学的发展无关,人在面对它们时通常会感到突兀和茫然。人在异化的现代社会中,自身也被异化,不可理解的事物或现象会被每个人遭遇,而卡夫卡的创作目的之一便是解释那些无法解释者。作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1]当然,从现实的情况看,卡夫卡失败了,那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并未因他的解释而变得清晰起来,反而更加地突兀和难以理解。在其作品中,有很多情节是人们以常识所无法理解的,比如格里高尔清晨醒来就变成了甲虫。然而,卡夫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艺术的方式将“不可解释的事情”直观地表现了出来。同时,卡夫卡准确地揭示出这些“不可解释的事情”是无形的社会所强加于人的。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经济联系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乃至地球成为“地球村”,也就是说,人是无法摆脱社会而独立存在的,鲁滨逊似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之中。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并没有因紧密的经济联系变得同样亲密,反而更加疏远和冷漠,萨特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他人就是地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必须承受他人或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一切,然而社会又是无形的,这就使一些事情变得“不可解释”。在《诉讼》中,约瑟夫·K被判有罪,但指控来自何方却始终不得而知,K想尽办法关注案情的进展,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和不着边际的。
第三,以梦幻的方式来表现真实。每个人都有过做梦的经历,在一般语境中,梦代表着虚幻和不真实,但事实远不是如此的简单,一般来说,没有到过南美的中国人不会梦到热带雨林中的场景。也就是说,梦的内容是现实世界的重新拼接,梦可能是杂乱无序的,但距离做梦人所处的世界不会太远。现代主义作家主张揭示事物的本质,但他们又力主抛弃对事物外在表象的记述或描写,这样一来,直觉或梦境就成为他们沟通艺术与现实的重要途径。卡夫卡认为梦幻能够表现和揭示真实,在其作品中多次运用梦幻的手法。比如早期作品《梦》,主人公K莫名地来到墓地的一座新坟前,他看见有人在墓碑上写着字,K想看清楚一点,但却被气流裹挟到坟墓之中,而此时他看到墓碑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此时梦醒了。小说戛然而止,似有未尽之意,不太容易做出清晰的解读。但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从创作伊始就偏爱用“K”命名小说的主人公,而“K”也正是作者名字(kafka)的首字母,那么K是否就是作家本人呢?卡夫卡有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梦境的习惯,而很多被记录下来的片段后来成为其创作的素材或灵感的源泉。《变形记》中,开篇就提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巨大的甲虫”。[2]显然,小说是从梦境中延伸出来的,是梦的继续。正是在“梦境”之中,格里高尔才看清的亲情的冷漠,他曾经为之倾其所有的家人此时嫌恶他和排斥他,现实的残酷与真相的锥心就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作家彻底颠倒了梦幻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梦幻才是真实的,而现实可能只是梦幻。
第四,对现实世界的夸诞变形。美国评论家奥斯卡沃伦曾对卡夫卡做过这样的评述:“卡夫卡的世界既不是世俗的常人世界,也不是幻想。这是一个在眼睛斜视下微微瞥见的世界,就像人们从两条腿中间或倒立着所看到的,或者在一面不反射事物本相的哈哈镜中所看到的那样。”[3]显而易见,卡夫卡所描绘和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幻想的境遇,他的作品不是科幻小说,更不是穿越剧,而是其所生活的真实世界。不过,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卡夫卡的表现方式乃是一种夸诞的变形,而这种变形是通过隐喻性的语言、怪诞的情节设置和“动物视角”的运用来实现的。首先,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反映,因而一种语言中的许多语汇往往具有某种隐喻性含义,但随着时代风气的变化和语汇的高频使用,某些语汇的隐喻含义可能会逐渐弱化而被人们所忽视,而只残存了语汇本身的抽象意义。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红领巾”出现在上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是一种借代辞格,通常还隐含着活力、健康、善良等含义,但在当下,“红领巾”可以直接意指小学生,但其中的“健康、善良”等隐喻性含义则荡然无存。在卡夫卡的创作中,作家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将语言的隐喻性含义重新挖掘出来加以还原,或者说这是一种对比喻的反向运用。其次,怪诞的情节设置也是卡夫卡实现“变形写真”的手段之一。《诉讼》中,法庭设立在嘈杂的农家小院之中,平时这里只有粗鄙的农妇和肮脏的马槽,以及挤在马槽里过夜的妓女,只有开庭时这里才变成“庄严的”法庭。显然,在作家眼中,法律不过是人尽可夫的玩物。卡夫卡本人是法学博士,他对当时的法律是谙熟的,这样的嘲讽绝非空穴来风。再次,转变叙述视角,从动物的角度直视人类也是卡夫卡常用的艺术手法。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专有一类“动物小说”,表面看来,此类作品是在叙述一个生动的动物故事,但作品的主题却是在揭示人类生存的真相。《地洞》《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一条狗的研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是卡夫卡“动物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关于《地洞》前文已提到,其实还可以做更深一层的解读,作品是通过描写小动物想要建筑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洞而不可得来表现人类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致某科学院的报告》是卡夫卡揭示人类未来的巅峰之作。作品讲述了一只来自黄金海岸的猿猴——红彼得,成功地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成为一个达到欧洲中等文化水平的“文明人猿”,并且“在人类文明世界的所有杂耍舞台拥有如磐石般牢固的地位”,甚至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看似红彼得成功了,它终于摆脱了牢笼,过上了“体面人”的生活。但却进入了人类世界这个孤独的真正的牢笼,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作家通过红彼得的形象再现了人类进化的苦痛经历。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是刚刚开始——当人类进化到某一极限之时又该走向何方呢?当然,卡夫卡并没有找到答案,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发展将会给人类带来的必然结果——灭亡。作家一反隐喻的常态,而是明白无误地使用了“科学”这个字眼。科学究竟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无比舒适还是为人类敲响了丧钟?这里不妨做一点联想,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端》,在历史语境中,杞人愚不可及;但在当代语境中,杞人却是个明白人,科学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必将导致人类灭亡已经成为共识。语
参考文献
[1](奥)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奇译.天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321.
[2] (奥)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M].叶廷芳,洪天富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6.
[3]叶廷芳.论卡夫卡[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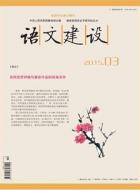
- 论阿克罗伊德与莫言作品的民族关怀 / 郭瑞萍
- 论卡夫卡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特征 / 徐利君
- “Mooc”时代高校基础写作教学的变革 / 柳杨
- 小学语文教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 万桂红
- 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 / 覃俏丽
- 留学生汉语写作课程任务教学方法研究 / 王犹男
- 基于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 王正中
- 论历史语境的甄选引入对古文史讲授的影响 / 李延玲
-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评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得失 / 姜瑞云
- 语言的文化功能对高校英美文学教育的影响 / 张婧
- 大学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作用 / 沈黎
- 语文教学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功能与优化路径 / 孔好为
- 成长视角下薇拉·凯瑟小说中的拓荒者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技术恐惧主义背景下的文学批评 / 邢凡夫
- 论澳大利亚文学的多元化创作研究 / 季戈宁
-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作家菲茨杰拉德的悲剧思想 / 刘小蓉
- 分析斯特恩《项狄传》的艺术特色 / 邹灿?曾剑
- 解读《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成长之旅 / 李敏?窦琴
- 剖析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叙事结构 / 牟英梅
- 自尊与反叛 / 杜磊?李哲?郭洁
- 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 李景
- 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浪漫主义手法解读 / 阙红玲
- 理想的方向 / 刁曼云
- 对顾拜旦《体育颂》的文学价值解读 / 胡朝霞?白侠
- 从《傲慢与偏见》解析简·奥斯汀的婚姻观 / 李慧?邹爱荣?赵青
- 海明威作品语言与写作风格研究 / 唐琛
- 《西风颂》赏析 / 乔玉芳
-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研究分析 / 罗丽娅
- 英美文学评论的文化差异探析 / 罗雨
- 刘庆邦小说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 盖伟
- 抗争与妥协 / 贺晓梅
- 试论《百年孤独》的“狂欢”性 / 陆璇璇
- 从不同角度看《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色彩 / 赵慧
- 郑观应的书法教育观 / 于有东
- 论宋代诗词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 / 叶向东
- 网络环境下的口语交际教学指导策略 / 耿红卫?李英
- 认知语言学理论下伍尔夫《到灯塔去》语篇探析 / 马红英
- 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词典比较与分析 / 高惠宁
- “登陆”与“登录”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 / 王定康
- 分析现代汉语中的对称结构及其句法功能 / 贾琼
- 论现代汉语新词汇在语言生态建设中的体现 / 朱萍
- 校园流行语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论析 / 陈亚芳
- 论模糊语的言语交际与语用功能探索 / 刘彬
- 新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功能与路径 / 陈志娟
- 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的作用探析 / 李军
- 人文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优化路径 / 吴琼石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两种模式评析与启示 / 孙英林
- 语文教学思维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 叶美丽
- 安全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莫莉秋
- 英语教学中汉语文化影响研究 / 王瑾丽
- 从《史记》中看刘邦的“人才观” / 张敏
- 汉语文化对英语教学的影响与改进路径 / 李旭
- 汉语对英语口语教学的负迁移及其应对机制 / 陈玲?何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