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922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922
刘庆邦小说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 盖伟
摘要:对乡村女性的执着书写是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从幼女到少女,从少女到母亲,刘庆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乡村女性王国。在对这些乡村女性生存境遇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与“美”,无论是对“美”的张扬还是对“丑”的批判,都体现着刘庆邦对人性的呵护和对乡村女性的人文主义关怀。
关键词:刘庆邦 乡村女性 母性
引言
对于女性的书写一直是二十世纪文学关注的中心。素有“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称誉的刘庆邦,由于其成长经历和个性气质,在作品中执著于对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的书写。他曾说:“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作为一个男作家,谁都愿意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写到女性,才容易动情,容易出彩,作品才好看。第二个原因,大概因为我少年丧父,是母亲和姐姐把我养大,供我上学。对她们的牺牲精神和无私的爱,我一直怀有愧疚和感恩的心情,一写到女性,我的感情就自然而然的寄托其中”。[1]这种对女性的崇拜,转化成了他笔下一个个善良淳朴、坚强执著、忍辱负重的乡村女性形象。
一、坚韧淳朴的母性之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性别特征受到了明显的关注,身体描写在不断蔓延,母爱与母性则黯然退场,而刘庆邦在作品中则更多地展示了女性的善良淳朴与母性。
(一)坚韧如水的母性之美
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乡村生活中,妻子把自己的丈夫称为“当家的”,这充分体现了男人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在家庭中所享有的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个家庭如果缺少了男性劳动力,那就意味着这个家庭缺少了顶梁柱,意味着这个家庭在乡村的生存力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个家庭中的女性就会承受更多的艰辛,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母亲形象在刘庆邦笔下大都是独自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坚强女性。
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坚强勇敢的母亲——魏月明。面对丈夫的死去,她没有退宿,也没有想到改嫁,而是一个人独自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以超乎常人的坚韧度过了大饥荒的年代,把孩子培养成人。这是一位地母般温厚的女性,她为了家、为了孩子而顽强地活着,并且充满同情地对待身边遭遇不幸的人。
《枯水季节》中的母亲,仍旧是一位没有了丈夫,家境贫寒,挣扎于苦难岁月中的母亲。为了撑起贫寒的家,把孩子拉扯大,母亲每天和男人们干着一样的活,因为这样才能和男人得到一样多的工分。虽然生活环境很艰难,但母亲心灵却是那样地纯洁。当母亲见证了男社员杀干部家的猪时,母亲虽然从情感上理解社员们的行动,但她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做人原则,不参与其中。面对公社干部的调查,母亲虽然没有说出真相,但却把男社员偷偷送来的猪肉悄悄地埋掉,母亲用无言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准则。
面对命运的不公、丧夫的痛苦和性别的歧视,在乡村,母亲们的处境是艰难的,但这些并未压倒母亲们坚挺的脊梁,也并未消弱她们坚韧的意志,她们用汗水和行动为孩子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二)“小姐姐”们的母性传承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2]发现和挖掘少女身上与生俱来的母性,是刘庆邦小说中对于母亲的书写很特别的一点。
《梅妞放羊》讲述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与大自然和羊群那样一种和谐的爱的世界。梅妞与羊互爱着,当雷鸣雨猛时,梅妞不怕雨浇,却怕小羊淋出病来,当把羊带到废砖窑里避雨时,又怕传言中的蟒蛇吃她的水羊、驸马和皇姑,胆小柔弱的梅妞紧握镰刀做好了随时与蟒蛇生死相搏的准备。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母性之大爱,梅妞陡然勇敢起来,为了羊的安全,她愿意应对人类和大自然的任何威胁。
同样,在《小呀,小姐姐》中,刘庆邦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小女孩对罗锅弟弟的母性之爱。在父亲缺席的家庭里,面对残废的儿子,母亲虽然很爱他,但被过多的烦恼所淹没。当别人都不在乎这个一无所能的弟弟时,小姐姐倒把弟弟看得很重,并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母性之爱去关心体贴他,在平路的心里,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小姐姐才是他的亲人。当快要死去的弟弟想吃鱼时,她便独自到鱼塘给弟弟摸鱼,由于太专注而涉入水深处沉入水塘……小姐姐对平路近似母亲的爱,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幼小的小姐姐并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也未意识到她该有这样一份责任。但是她的心灵中这种责任却是与生俱来的,与血缘并无多大关系,更多的是她对弱者的同情悲悯和对生命的呵护与尊重。
二、执著追求的女性光辉
《响器》中的髙妮,《听戏》中的姑姑则又以另一种执著感动着我们。高妮与姑姑在刘庆邦所描述的上百个乡村女性中是特殊的,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并且有为之奋斗的一种执着。在中国乡村,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都有一种不平等的文化理念:那就是作为女人,不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他们应服从于家庭与男权,这种乡村文化对女性的干预犹如一条铁链困住了千千万万像姑姑和高妮一样的乡村女性。而高妮和姑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对艺术的热爱又是执著的,表现了乡村女性聪慧、灵秀的人性之美。
农村少女高妮痴迷于响器,父亲的软硬兼施都没有改变她学大笛的决心。音乐世界是高妮的光明领地,她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家长制抗争,终于“两三年后,高妮吹出来了,成气候了,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3]她的成功,看似是事业上的,是人生的辉煌,其实是生命自在而勇敢的喷涌。
《听戏》中的姑姑。“不听戏,就不能活!”听戏,成了她最大的精神追求。一个女人,满脑子装着魂牵梦绕的戏,这对于村里人和姑父来说是荒谬的,但面对村里人的议论和姑父的毒打恶骂,姑姑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刘庆邦向我们折射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乡村女子难得的心灵之光。姑姑和高妮这样一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执著追求,在本质上可以说是对于生命意义的艺术化追求,贫瘠荒凉的山村正是因为有了她们这样一种女性才变得丰富靓丽起来。
三、期待无奈的待嫁少女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对美好婚姻的渴望与期盼是每一个女孩心中的梦想。刘庆邦在向我们展示乡村女性诗意浪漫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她们面对爱情、面对婚姻的期待和无奈。
《鞋》中守明的那种淳朴的感情一直被人们所赞颂,但是在赞颂的同时我们是否看到了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当把那双鞋退给那个姑娘时,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守明用心做好的鞋终于送到了她“那个人”的手中,此时对于守明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到“那个人”穿上这双带有爱的针脚的鞋子,但几次要求都被拒绝了,我们也似乎看到了守明眼中的泪水,无奈的哀伤。
在《红围巾》中,喜如姑娘当得到相亲被拒绝的结果后,只能将委屈压抑在心里,并把自己被拒绝的原因归结为相亲时缺少一条红围巾,并为了得到红围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我们可以看到喜如面对爱情的无奈,自觉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以外表来判断女性的价值。
在传统的角色安排中,女性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顺从的、被情感所支配的地位,虽然心存对爱情的期盼、对婚姻的憧憬,但是面对感情,女性却只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而没有挑选的权利。
四、忍辱反叛的失贞女性
刘庆邦在为我们塑造温柔的、坚强的带有母性之光与执著追求的乡村女性的同时,也关注了乡村的另一类特殊女性——失贞女性,对这类女性生存境遇的血泪书写,更让我们看到了千百年来乡村固有的文化认知对女性的残害。在以前的论述中,我曾把这些女性划分为“掌握主动权的乡村失贞女性”和“被引诱或强迫的矿区失贞女性”两类。其实还有一类失贞女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失贞之后的她们选择了艰难地皈依、复仇与反叛之路,我们以《玉字》中的玉字和《东风嫁》中的米东风为例来讨论。
《东风嫁》中的米东风用自己在城里挣来的钱让父母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而她却因在城里曾经当妓女的经历遭到人们的唾弃,没有媒人为她介绍对象。她的父亲米海廷不得不四处求人,并且一再降低择婿标准,无奈地把闺女倒贴给了穷得叮当响的无赖王新开。米东风也带着赎罪的心情决心相夫教子、从良为善、忍辱重生,然而她“不光彩的过去”却招致了丈夫和婆婆从精神到肉体的侮辱和糟践,战战兢兢地过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日子,只有她的小叔子,王新开的残疾弟弟王新会同情嫂子的遭遇,在米东风万念俱灰的关键时刻,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让米东风逃出了王家。她的出走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但却是对千百年来乡村固有陋习的一种反叛,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光明。
《玉字》中的玉字在一次看完电影回村的路上被流氓强暴,她的失贞不仅受到了别的男人的鄙视,连她的亲哥哥也让她去死,在有了很多次想死的念头之后,玉字坚强地活了下来,以她的身体为武器走上了含泪的复仇之路。玉字以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未来人生幸福为代价的复仇,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沉痛与思考。
玉字和东风的悲剧是大部分乡村失贞女性的悲剧,她们不管是因何种原因而失贞,但都遭到了她们所处的这个底层社会的唾弃,因为在传统封建文化意识里,男性尤其在身体上要求女性绝对的忠贞,不允许有任何的背叛。失贞后的玉字和东风也想到了皈依,但现实社会不给她们一席立足之地,她们没有归宿感,甚至连亲情也显得那么的微弱无力。
刘庆邦为我们展现了底层乡村女儿国丰富的女性形象,从她们的坚韧、她们的泪水、她们的伤痛、她们的执著、她们的勇气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底层乡村女性生存的艰辛,也看到了人性的“丑”与“美”。刘庆邦曾说:“文学的本质是劝善的,我们创作的目的主要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改善人心,提高人的精神品质。”[4]虽然在《玉字》和《东风嫁》中,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在写“丑”写“恶”,但是“丑”“恶”的背后是作家对美好和谐的人性的一种呼唤与张扬。在这个女儿国中,无论是对“美”的张扬还是对“丑”的批判,都体现着作者对人性的呵护和对底层女性的人文主义关怀。语
参考文献
[1]北乔、刘庆邦对话录.刘庆邦的女儿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94.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0.
[3]刘庆邦.民间·响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4]刘庆邦.从写恋爱信开始[J].作家,20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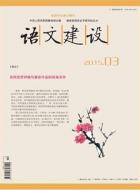
- 论阿克罗伊德与莫言作品的民族关怀 / 郭瑞萍
- 论卡夫卡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特征 / 徐利君
- “Mooc”时代高校基础写作教学的变革 / 柳杨
- 小学语文教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 万桂红
- 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 / 覃俏丽
- 留学生汉语写作课程任务教学方法研究 / 王犹男
- 基于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 王正中
- 论历史语境的甄选引入对古文史讲授的影响 / 李延玲
-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评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得失 / 姜瑞云
- 语言的文化功能对高校英美文学教育的影响 / 张婧
- 大学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作用 / 沈黎
- 语文教学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功能与优化路径 / 孔好为
- 成长视角下薇拉·凯瑟小说中的拓荒者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技术恐惧主义背景下的文学批评 / 邢凡夫
- 论澳大利亚文学的多元化创作研究 / 季戈宁
-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作家菲茨杰拉德的悲剧思想 / 刘小蓉
- 分析斯特恩《项狄传》的艺术特色 / 邹灿?曾剑
- 解读《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成长之旅 / 李敏?窦琴
- 剖析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叙事结构 / 牟英梅
- 自尊与反叛 / 杜磊?李哲?郭洁
- 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 李景
- 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浪漫主义手法解读 / 阙红玲
- 理想的方向 / 刁曼云
- 对顾拜旦《体育颂》的文学价值解读 / 胡朝霞?白侠
- 从《傲慢与偏见》解析简·奥斯汀的婚姻观 / 李慧?邹爱荣?赵青
- 海明威作品语言与写作风格研究 / 唐琛
- 《西风颂》赏析 / 乔玉芳
-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研究分析 / 罗丽娅
- 英美文学评论的文化差异探析 / 罗雨
- 刘庆邦小说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 盖伟
- 抗争与妥协 / 贺晓梅
- 试论《百年孤独》的“狂欢”性 / 陆璇璇
- 从不同角度看《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色彩 / 赵慧
- 郑观应的书法教育观 / 于有东
- 论宋代诗词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 / 叶向东
- 网络环境下的口语交际教学指导策略 / 耿红卫?李英
- 认知语言学理论下伍尔夫《到灯塔去》语篇探析 / 马红英
- 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词典比较与分析 / 高惠宁
- “登陆”与“登录”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 / 王定康
- 分析现代汉语中的对称结构及其句法功能 / 贾琼
- 论现代汉语新词汇在语言生态建设中的体现 / 朱萍
- 校园流行语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论析 / 陈亚芳
- 论模糊语的言语交际与语用功能探索 / 刘彬
- 新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功能与路径 / 陈志娟
- 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的作用探析 / 李军
- 人文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优化路径 / 吴琼石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两种模式评析与启示 / 孙英林
- 语文教学思维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 叶美丽
- 安全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莫莉秋
- 英语教学中汉语文化影响研究 / 王瑾丽
- 从《史记》中看刘邦的“人才观” / 张敏
- 汉语文化对英语教学的影响与改进路径 / 李旭
- 汉语对英语口语教学的负迁移及其应对机制 / 陈玲?何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