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892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3期
ID: 420892
论阿克罗伊德与莫言作品的民族关怀
◇ 郭瑞萍
摘要:阿克罗伊德与莫言虽然在不同的国度进行创作,但其作品彰显出共同的审美诉求:即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地方文化的历史书写表征“民族性”。阿克罗伊德通过“伦敦”表征“英国性”,莫言则以“高密”为背景书写 “中国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展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关怀,可被视为当下艺术审美与国家认同研究完美结合的典范。
关键词:彼得·阿克罗伊德 英国性 莫言 中国性
引言
彼得·阿克罗伊德是当代英国文坛的一朵奇葩。从20世纪7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他共发表作品50余部,包括诗歌、传记、小说、改编作品和文学论著等,并撰写了140多篇散文和文学评论,其中他的传记和小说曾获得过众多文学奖项,被誉为“当代最有才华的传记作家之一”和“历史小说大师”。当代作家阿普尔亚德曾预言,阿克罗伊德是最有可能被阅读上百年的少数当代英国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从1981年到2011年,他共创作11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篇小说,和80多部短篇小说,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在2012年,莫言作为第一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外掀起了“莫言热”,研究成果颇丰,硕博论文,期刊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
阿克罗伊德和莫言的创作年代,正值后现代语境中。和其他作家一样,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有文学理论的影响,其作品均吸收了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借鉴与移用了一些当代文学元素。但两位作家又与众不同,他们在采纳和吸收现代因素的同时又与它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坚持独特的审美诉求,对“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
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虽然体裁多样,但具有内在一致性。他试图在每部作品中从不同侧面对英国文化、英国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进行多维阐释和表征,因此“英国性”成为其传记、改编作品和历史小说的共同主题与灵魂。莫言的作品也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性”进行表征。如他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张扬着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民族精神,《丰乳肥臀》通过描写个人家庭历史反映中国社会的宏大历史,《生死疲劳》展示了50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充满苦难的蜕变史。另外,在他的散文和剧本中,作者同样从不同维度阐释“中国性”,与其小说形成互文。事实上,莫言之所以能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作品中所彰显的“中国性”。
可见,两位作家的创作理念极为相似,彰显着强烈的民族关怀,这主要体现在其浓厚的地方意识、动态的历史观与自觉的文化意识。
一、地方意识:阿克罗伊德笔下的“伦敦”与莫言笔下的“高密”
地方意识是阿克罗伊德和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因为他们都有一块魂牵梦绕、为之钟情的土地,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共和国”[1]。
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性”的探讨主要通过对“伦敦”的历史书写而实现。在1993年,阿克罗伊德就被誉为“伦敦小说家”和“伦敦幻想家”。刘易斯甚至说:“伦敦是阿克罗伊德的缪斯,在许多方面,阿克罗伊德堪称是都市小说家之王”。阿克罗伊德曾在一次访谈中表明,“伦敦是激发我想象的灵感源泉,并成为我每部作品中的一个鲜活人物。我一直在间接地为它写史、写传。因此,我认为我现在所写的作品,包括传记和小说都是到我生命结束时才能完成的整部作品的其中一章而已”。鉴于此,阿克罗伊德的作品大都与伦敦有不解之缘,强调“地方影响论”的重要性。因此,伦敦既是他的小说,也是其传记的共同背景,伦敦的人和事、伦敦的风景、街道、房屋、教堂和监狱等都是他描写的对象。
莫言创作的地理背景是他的“高密”家乡。自从他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有意识地对“高密东北乡”[2]认同后,故乡的风景就变成了他小说中的风景。在以后的创作中,他始终把目光集中在此,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描写它多姿多彩的历史和人事景物,写出一部部传奇。例如,他说:“1978年,在枯燥的军营生活中,我拿起了创作的笔,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军营小说,但涌到我脑海里的却都是故乡的情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梁……”[3]。于是,他怀着深厚的故乡情结,以豪放、粗疏的笔触,描写故乡的一草一木,因为,在他看来,“故乡是血地”。因此,《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都以“高密”为背景,而在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他直接利用了故乡的经历。
阿克罗伊德和莫言的作品虽然分别限定在 “伦敦”和“高密”,但他们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是想以小环境为象征表现民族大环境,映射更深厚的主题。如阿克罗伊德说:“从伦敦的点滴生活中可以发现整个宇宙”。莫言也曾说:“我的《丰乳肥臀》超越了‘高密东北乡’。我想,时至21世纪,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4]。因此,阿克罗伊德和莫言笔下的“伦敦”和“高密”既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又是隐喻,是作者表征“民族性”以及“全球化”的载体。
二、动态的历史观
深厚的历史意识是阿克罗伊德和莫言作品的共同特征。虽然在后现代语境中创作,但两位作家都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竟相给历史怯魅,甚至解构历史,而是尊重历史。
细读文本会发现,阿克罗伊德的作品之所以厚重,是因为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英国历史事件与人物,从历史中寻找创作素材与灵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传记创作中,在他的小说和改编作品中也是如此。同样,莫言之所以能逐渐在中国占据寻根文学的中心地位并成为一面旗帜,也在于他对重建中国历史的一种敏感与自觉,因此,他才创作出许多有历史纵深感的作品。
当然,历史意识不仅指两位作家的作品取材于历史,更体现在两位作家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想象大胆改变历史和传统,彰显出动态的历史观。因为他们的历史书写不是照抄历史,而是将地方、历史和现代意识融合在一起,注重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想象使文学与历史完美统一。如阿克罗伊德的历史小说《霍克斯默》中的戴尔和霍克斯默两个人物形象是作者根据英国17世纪一位杰出的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默而创造的人物,在改编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时,他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拜伦、雪莱等通过合理想象植入作品中,不仅使故事更为真实可信,还使改编后的作品更具人文关怀和现实感。莫言持同样的创作观,他曾说,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5]。瑞典文学院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也指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见,在阿克罗伊德和莫言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的秉承与回归,又有对历史的质疑和改变。艾略特曾说,伟大的作家不但继承传统而且还改变传统,以此为标准,阿克罗伊德和莫言都在其作品中展示了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
三、自觉的文化意识
阿克罗伊德和莫言在表征“民族性”时充分展现出自觉的文化意识。他们均能以后现代视野审视本民族文化,在作品中,并不一味地赞美或批判,而旨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根脉进行追寻和认同,是“审美”与“审丑”的结合。一方面,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和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丑陋文化因素进行深层挖掘和反思, 做到了对“民族性”的多元阐释。
阿克罗伊德不仅赞美英格兰文明的伟大与光明,而且揭示英格兰文化的丑恶与黑暗。例如,在小说《霍克斯默》中,他通过将真实的历史人物霍克斯默分为一正一邪(霍克斯默和戴尔)两个人物阐明“英国性”的“双面性”特质,犹如光与阴影,指出伦敦不仅是“天使之城”,也是“魔鬼之家”和“黑暗之都”,体现出他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意识。在传记中,他也能对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和艾略特等经典作家做出令人信服的客观评价,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关怀。
莫言在创作中也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例如,在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中,作者塑造的余占鳌不是完美的爱国英雄,而是正义与邪恶的化身,是特属于红高粱的英雄,表现的是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他对“高密”的描写同样显示出自觉的民族意识,他说:“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6]。因此,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人们经常会看到,杂草和香花共生,美丽和丑恶并存,爱和恨缠绕,好与坏同体。
阿克罗伊德和莫言的作品展示的这种文化自觉,不仅很好地诠释了两位作家海一般的博大胸怀,而且还蕴含着他们对“民族性”所应具有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
结语
阿克罗伊德和莫言在作品中各自对“英国性”和“中国性”的表征,体现出作者在“全球化”浪潮中清醒的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 “全球化”被过分强调的后现代语境下,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对外国文化则积极拥抱。于是,很多寻根文学作家没有真正做到寻根,从而造成了“寻根文学”的逐渐衰微。
事实证明,一位作家只有立足于本民族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不离不弃,才能真正把握民族精神,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盲目追随异族文化、作家和流派的创作不可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异族文化只能是民族文化的补充,决不能代替民族文化。如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应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可以说,阿克罗伊德和莫言在各自的创作中都做到了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创作了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可谓当下文学创作的典范之作。语
参考文献
[1][3]莫言.我的高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256.
[2]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99.
[4]莫言.莫言讲演新篇[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32.
[5]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025.
[6]莫言.红高梁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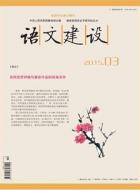
- 论阿克罗伊德与莫言作品的民族关怀 / 郭瑞萍
- 论卡夫卡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特征 / 徐利君
- “Mooc”时代高校基础写作教学的变革 / 柳杨
- 小学语文教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 万桂红
- 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 / 覃俏丽
- 留学生汉语写作课程任务教学方法研究 / 王犹男
- 基于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 王正中
- 论历史语境的甄选引入对古文史讲授的影响 / 李延玲
-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评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得失 / 姜瑞云
- 语言的文化功能对高校英美文学教育的影响 / 张婧
- 大学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作用 / 沈黎
- 语文教学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功能与优化路径 / 孔好为
- 成长视角下薇拉·凯瑟小说中的拓荒者形象解读 / 刘建平
- 技术恐惧主义背景下的文学批评 / 邢凡夫
- 论澳大利亚文学的多元化创作研究 / 季戈宁
-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作家菲茨杰拉德的悲剧思想 / 刘小蓉
- 分析斯特恩《项狄传》的艺术特色 / 邹灿?曾剑
- 解读《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成长之旅 / 李敏?窦琴
- 剖析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叙事结构 / 牟英梅
- 自尊与反叛 / 杜磊?李哲?郭洁
- 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 李景
- 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浪漫主义手法解读 / 阙红玲
- 理想的方向 / 刁曼云
- 对顾拜旦《体育颂》的文学价值解读 / 胡朝霞?白侠
- 从《傲慢与偏见》解析简·奥斯汀的婚姻观 / 李慧?邹爱荣?赵青
- 海明威作品语言与写作风格研究 / 唐琛
- 《西风颂》赏析 / 乔玉芳
-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研究分析 / 罗丽娅
- 英美文学评论的文化差异探析 / 罗雨
- 刘庆邦小说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 盖伟
- 抗争与妥协 / 贺晓梅
- 试论《百年孤独》的“狂欢”性 / 陆璇璇
- 从不同角度看《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色彩 / 赵慧
- 郑观应的书法教育观 / 于有东
- 论宋代诗词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 / 叶向东
- 网络环境下的口语交际教学指导策略 / 耿红卫?李英
- 认知语言学理论下伍尔夫《到灯塔去》语篇探析 / 马红英
- 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词典比较与分析 / 高惠宁
- “登陆”与“登录”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 / 王定康
- 分析现代汉语中的对称结构及其句法功能 / 贾琼
- 论现代汉语新词汇在语言生态建设中的体现 / 朱萍
- 校园流行语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论析 / 陈亚芳
- 论模糊语的言语交际与语用功能探索 / 刘彬
- 新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功能与路径 / 陈志娟
- 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教学的作用探析 / 李军
- 人文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优化路径 / 吴琼石
- 汉语文化下英语教学两种模式评析与启示 / 孙英林
- 语文教学思维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 叶美丽
- 安全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 莫莉秋
- 英语教学中汉语文化影响研究 / 王瑾丽
- 从《史记》中看刘邦的“人才观” / 张敏
- 汉语文化对英语教学的影响与改进路径 / 李旭
- 汉语对英语口语教学的负迁移及其应对机制 / 陈玲?何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