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3期
ID: 137081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3期
ID: 137081
浅谈语文课程中文学教育的课堂模式
◇ 田 芸
【摘要】为了克服中学语文课中文学教育的科学主义倾向,我们必须在师生互动的基本框架中重建文学教育的课堂模式,使之成为“民主”的课堂、“建构”的课堂、“审美”的课堂,从而赋予文学教育更多的人文内涵,充分发掘和释放语文课程的人文精神和活力,使语文课堂真正散发出“人性”的力量和美感。
【关键词】语文课程 文学教育 民主 建构 审美
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文学教育。然而文学教育又常常由于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诉求而被简化为一种“技术”的习得过程,诸如叙述的技术、议论的技术、说明的技术、起承转合的技术、渲染铺垫的技术,甚至抒情的技术。语文课程对“技术”的执迷,逐渐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性文学观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对文本不厌其烦地解构与重构中,文学变成了一堆僵死、冰冷的符号,而本该最有魅力、最有人情味的文学教育课堂成为教师空洞地说教与学生机械地模仿的场所,师生关系成为技术上的师徒关系,而非人与人的心灵交往。这样的文学教育使我们的心变得坚硬冷漠。文学的一种伟大意义就是要使人与人的心靠近一点,她给予我们的应是一种对他人的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一种生命的尊严,一种大慈悲。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走在与此相反的道路上,它并不能够让我们拥有真正的“文学”。
基于以上中学语文课中文学教育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我们试图在师生互动的基本框架中重建文学教育的课堂模式,赋予文学教育更多的人文内涵,这样的课堂应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民主”的课堂
这是要求师生以人格平等的姿态共同进入学习情境,课堂应该充满一种宽容、和谐、平等、开放、自由、民主的氛围。“教师引导课堂”、“教师设计课堂”、“教师将课堂交还给学生”等等曾经流行的口号几乎构成教育“新理念”的发展脉络。“引导”与“设计”应该是隐性的还是强制的?“将课堂交还给学生”之后呢?教师何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明确,又似乎晦暗。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引导”变成教师的“埋伏”,“设计”变成学生的“陷阱”,“将课堂交还给学生”使课堂四十五分钟变成图像的轰炸、虚假的活跃和思想的真空。我们期望的文学教育课堂应该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课堂,一个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课堂,一个捍卫每个参与者言说权力的课堂,一个没有强制和推销而有尊重和选择的课堂,一个人与人之间真诚对话、思维互动的课堂;而不是教师用老套而“蓄意”的问题去“引导”学生、“设计”课堂,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威形象,学生则察言观色地应对并努力扮演好教师分配给自己的角色。民主的文学教育课堂应成为所有参与者精神遨游的殿堂,思想诞生的摇篮,一个自由而美的空间。
二、“建构”的课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对新信息的理解是通过已有经验,超越所提供的信息而建构成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的意义的建构,同时又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从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的理解,同时应重视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建构”的文学教育课堂应表现为师生共同参与,分享意义,发现问题,合作探究,将思考引向深入。教师与学生将成为课堂中平等的“主体”,对话交流,互相启发,互相感动,互相欣赏。这样的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不仅是个性化的解读过程,由于有超越文本的意义的生成,因此也是创造的过程、创新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教师应积极创设有利于学生对文本进行个性化解读的课堂情境,给予学生充分的想象权力和表达空间,激发学生主动生成阅读意义。
文学教育的理想不是培养某种教育的适应者与因袭者,而是培养有创造性、个性化思维的独立的人格。在文学文本的阅读中,由于每个学生生活背景和感知角度的不同,文本将呈现出异质的、复数的、携带着学生鲜明个性痕迹的解读意义,学生将会从自我狭小的理解范围和思维定势中超越出来,学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自由思考和判断,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和被接受、被同意的从属感和安全感所形成的强大惯性和惰性将不能够完全发挥限制作用。当学生逐渐懂得了在“肯定”与“否定”之外还有“批判”的立场时,思想的解放将成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因为“个性化”发展首先意味着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判断,拥有足够的理性,时刻提防“顺从”所带来的对自已生命彻底取消的危险。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告诫人们: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培养“自由思想者”应是文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三、“审美”的课堂
“新课标”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明确提出:“语文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能力。”而语文美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写作实践来落实的,文学教育的课堂应是一个审美的课堂。
美育是感性的教育,这一命题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中被明确地提出。席勒认为人性的和谐在于理性与感性的协调发展,而在充斥着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中,美育尤其呼唤人的感性能力的发展。他指出:“理性虽然要求统一,但是自然却要求多样性,因此人需要这两种立法。”(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3页)席勒严肃地提出:不仅需要理性的一般法则,而且需要感性的特殊法则,以保持或恢复个体性格的多样性,从而保证人格的完善。席勒提倡美育是试图在理性占主导的文化和教育中保护和发展人的感性,使人能重新获得感性和理性的协调平衡。
杜卫在《感性教育:美育的现代性命题》一文中认为:“感性以人的本能冲动和情感过程为特征,感性的发达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充沛。文明人日渐远离自然,理性的发达和物质生活的富足使人的感性枯萎,从而引起生命力的渐渐丧失。”(《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感性的美育强调对于保护和提升个体原发性的生命活力的意义。感性还意味着以情感为核心的心理能力。人的感性能力包括直觉、知觉、想象、情感等,尤其是直觉体验能力在创造性、个性化的工作中极为重要。美育应在开发人的理性能力的同时,促进人的感性能力的发展,即审美发展。
基于以上对美育的理解,文学教育的审美功能主要体现在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感性能力上。文学教育可以给学生丰富的思想,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判断能力,但使学生在文学的感召下情感得到净化和升华,心灵更加敏感和纯洁,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张扬,生命活力更加充沛和生动可能尤其显得重要。文学教育中师生双方都应放下已有的智虑成见,用一颗“赤子”之心去领会文学作品中表达的真情,这样才会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情感自然汇通的渠道,充分领略作品的美感。如《琵琶行》中“司马青衫”的悲伤凄切之情,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同命相怜;《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缠绵离别之情,是因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独在异乡的绝望的思念;《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沉悲凉之情,是因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难忘的心痛。在文学教育中应提倡学生以真诚的态度、真实的情感进入阅读情境,同作者一起感受生活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从而丰富学生的审美经验,增强其感性能力。而且,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学作品无疑给学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因为这些作品是生活的浓缩与写照,故学生可以通过审美鉴赏吸收其中的观念性倾向而落实于自己的生活中,学会在生活中保持真实的自我,得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发展。
概言之,我们的文学教育课堂应体现民主、建构、审美的品格,充分发掘和释放语文课程的人文精神和活力,使语文课堂真正散发出“人性”的力量和美感。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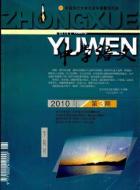
- 浅谈创建新课标下的开放式语文课程体系 / 张学勤 孙春华 唐 俊
- 团体动力学对语文新课程教学的启示 / 程俊花
- 试论语文教学的传统与现代 / 段德李
- 提高中学语文有效教学的研究 / 谢友明
- 语文探究性学习的思考 / 孙 泽
- 新课程对教师素质的基本要求 / 陆忠德
- 传承汉语文明,感受经典魅力 / 彭伟志 潘 靓
- 浅谈语文课程中文学教育的课堂模式 / 田 芸
-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陈秀云
- 《散文的写作和欣赏》教案 / 陈学书
- 探寻知识序列 提高写作素养 / 明学圣
- “饥饿疗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 蒋树勇
- 《雷雨》教案 / 王志敬
- 如何培养高中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 / 王佳明
- 《装在套子里的人》说课教案 / 武 晖
- 《失街亭》中的“三”字妙用 / 吴京华
- 文言文教学的点滴之见 / 吴建雄
- “走过2008”课堂作文实录 / 谢爱华
- 浅评“黛玉之死” / 杨 敏
- 新课标下文言文课堂教学刍议 / 唐开发
- 课堂阅读教学之重:主体\方法\能力 / 曹国庆
- 简析《荷塘月色》通感手法的运用 / 潘先武
- 自主学习大有成效 / 杨 眉
- 以民歌之“石”,攻《诗经》之“玉” / 龚祥亮
- 读.想.品.得 / 陈世萍
- 初中学生朗读现状分析及对策 / 王建平
- “阅读”杂感 / 刘 丹
- 古典诗词中的笑\哭\无语之浅析 / 梁世全
- 在清澈的小溪里歇脚 / 王文雄
- 我看陶渊明的一生 / 黎碧云
- 项羽和刘邦:谁是真英雄 / 王 琰
- 放飞思维天地宽 / 彭春炜
- 试论《亮剑》现象的文化生成因素 / 华 丹
- 高考阅读的辐辏式评价之弊 / 高西栋
- 让作文教学在互批\互改\互助\互学中熠熠生辉 / 肖清育
- 钓翁之钓不尽同 / 杨绍斌
- 作文备考更应向满分作文看齐 / 张新慧
- 浅谈如何巧妙利用教材写出个性作文 / 蒋 丽
- 解除作文束缚 激发创意表达 / 侯喜君 李红亚
- 民主 平等 和谐 / 刘丽梅
- 作文抄袭现象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 吕俊春
- 激趣:调动学生写作的有效途径 / 甘文中
- 语文教学要充分体现人文韵味 / 梁巧芬
- 如何让影视元素巧入文章 / 王华清
- 明确思路 把握要点 / 湛承芳
- 好钢用在刀刃上 / 凌春江
- 让课堂见证诗意的存在 / 罗秉相
- 现代文(散文)阅读答题六要领 / 张祥进
- 例谈记叙文对微型小说写作技法的借鉴 / 朱紫彪
- 硬性规定讲授时间 扭转讲风过盛现象 / 王绍平
- 细析考点 交融层级 活化方法 / 赵长河
- 积理炼识,成就议论文的浩然之气 / 邝培祥
- 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凌节而施”现象 / 徐 刚
- 好题细读 / 李慧婉
- 怎样写思想评论 / 卢文锋
- 现代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怡鸣
- 长句变短句有巧妙 / 杨显龙
- 师生同题作文 / 宫纪仁
- 在质疑问难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 / 路金改
- 语言表达中产生歧义的原因及修改策略 / 许明涛
- 重视 训练 习惯 / 邓学东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假若你是某某某” / 于卓琳
- 高考成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 付培同
- 口语交际能力: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 / 卢燕平
- 如何提高考场作文的应试能力 / 徐冬梅
- 看热播电视 明育人之法 / 陶玉鑫
- 高考作文获得高分的几项技巧 / 陈开庆
- 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 / 陈学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