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6期
ID: 137361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6期
ID: 137361
项羽悲剧的生命意义
◇ 吴贵阳
【摘要】刘邦与项羽都有伟大与崇高的一面。刘邦的伟大与崇高是理性的、政治的;项羽的伟大与崇高是感性的、生命的。理性使刘邦的政治生命具有了思想高度,感性使项羽的自然生命具有了情感境界。
【关键词】项羽 悲剧 感性 生命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李清照《夏日绝句》中对项羽的思念与悼念之词。在楚汉争霸后的千百年历史中,还有像杜牧、陆游、王安石等文化名人或历史名人,都对失败后的项羽给予褒奖性祭奠。
歌颂失败者,悼念失败者,祭奠失败者。这是为什么?
祭奠秋风中的落叶,其实就是祭奠悲剧性的生命。没有鲜花,却比鲜花的凋零更加灿烂;没有硕果,却比沉甸甸的果树还要沉重。
乌江,虽然无法重现两千年前悲壮的战场,但江风也一定会撩起千年的回忆与思考。
秋叶飘落,飘落了秋树热闹的附加;寒风凛冽,冷回了寂静的本体。乌江边的那一抹血红的残阳是项羽自然生命最后的挥洒。
两千多年前,北风凛冽,四面楚歌夹杂着将士的呜泣声回荡在耳畔,似水的虞姬跳完那最后一支舞倒卧在霸王的怀中,项羽紧握着追随已久的那把饱饮鲜血的天子剑,回想自己经历大大小小七十余场战役,就在今天,终于输了,输给了醉人的虞姬!他跪在这异乡的土地,抱着心爱的女人,那些拔山盖世的豪气全已不在,换来的却是英雄的默默两行泪。回想起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红颜知己,不可一世的霸王居然哭了,这满腔深情将刘邦比了下去。这种从强悍的生命原型中流淌出的贯穿千年的情节,让后世女子心动不已。
所有的悲愤,所有的怨恨终于迸发,项羽让脸上的最后一滴泪陪伴着心爱的虞姬.然后提起宝剑……
终于,终于来到了乌江亭边,乌江亭长的告慰无法让一代枭雄苟延残喘,断然拒绝是想以鲜血的形式告诉世人什么是霸王,万夫莫敌的霸王。
此刻项羽之前的残忍幻化成了一种人格力量,蕴涵着巨大的美学魅力,真情与坦荡使失败上升为高贵。
血色的残阳应该非常美丽、动人,乌江也为之汹涌,为之呜咽……只为了让生命与大地作一次亲近,秋叶甘愿飘落,这种飘落是为了让生命更好的抵达,让敏感而痛苦的灵魂更好地亲近江水。
从古至今,多少敏感的灵魂总是躲藏在一个个孤独的角落,可以是孤舟上狭窄的船舱,可以是旅夜里一间冰冷的小屋,可以是骄阳中一片浓郁的树阴。乍一看,一种精致的生命形态似乎几经构建起来了,但是这种精致的生命形态难以与大众相呼应,所以总是孤独的,即使崇高,但也是寂寞的。
项羽并不孤独寂寞。
苍天与大地的守候已有漫长而无尽的历史,生命的匆匆一瞥只是一瞬,在后人的祭奠中,这一瞬却让生命找到了默契的对应。
对于刘邦,我们歌颂他的成功;对于项羽,我们祭拜他的失败。歌颂而不祭拜,是因为刘邦背离了生命的自然生态和审美生态;歌颂而祭拜,是因为项羽的生命走向了自然生态和审美生态。双方都可以成为永恒,刘邦只能是政治军事的永恒;项羽却是自然生命的永恒。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登上胜利者的巅峰去纪念失败者的原因。
黑格尔曾说过,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片面的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崇高,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崇高又都无法退却。
从刘邦和项羽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庄严的持守,可以品味出他们在相互欣赏中的生死对立,体验出他们相顾无言的冤家知己。
楚汉争霸,由于没有明确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战争的每一方都可以找到一点朦胧的借口,成为堂而皇之的作战的理由;都可以找到一点拐弯抹角的事实,成为东征西伐的旁证,双方都没有孰是孰非的区别。就像自然界中,弱肉强食不存在是非之别,优胜劣汰不存在对错之分。战争中的一切生死博弈都回到了自然的生存法则上来,任何一方的怒吼都是义愤填膺的;任何一次的砍杀都是理直气壮的;任何一个人的倒下都是慷慨悲壮的。战争的双方都没有超越社会的底线、人类的公理,成功与失败都以悲剧的形式成为文学创作与审美倾向所关注的对象。而失败的一方更以生命为代价提升了创作与审美的悲剧性境界,超常地显现出生命的爽朗与纯美。
对失败者的纪念就成了生命与生命遥遥相通的对应。
刘邦与项羽没有明确的阶级对立,也没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胜利者与失败者的战争态势从本质上而言是对生存态势的极力构建。胜利者应该得到赞扬与歌颂,对失败者也应该祭奠凭吊。
我们发现,如果将难以裁断的历史都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在情绪化黑白思维之下,历史永远就会以一种简单的政治军事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自然生命的本质,我们就会忽略生命在历史事件中的伟大与崇高。
刘邦与项羽都有伟大与崇高的一面。刘邦的伟大与崇高是理性的、政治的;项羽的伟大与崇高是感性的、生命的。理性使刘邦的政治生命具有了思想高度,感性使项羽的自然生命具有了情感境界。《大风歌》的理性成分高于《垓下歌》,故具有政治思想高度;而《垓下歌》的感性成分绝对高于《大风歌》,故具有精神情感境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种理性总是依附于政治军事,与政治军事共沉浮,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情感却是依附于生命的,与生命共患难,故能贴近大众、呼应大众。无论是文人还是大众,拒绝刘邦就是拒绝与权谋相勾结的理性;接纳项羽就是接纳与生命相始终的感性。
《鸿门宴》上,项羽一意孤行的放走了刘邦,这是项羽军事上的自信和人格上的善,而人格上的善是最为高贵的天性,是生命的基座。只要这个基座没有倒塌,总会矗立成一座生命的丰碑。刘邦政治生命的真实远不及项羽自然生命的真实显得可爱。毕竟政治生命总是与权谋、倾轧勾结在一起的,总是多了一些非自然生命的东西,总是带着欺骗与伪善。
刘邦创立了西汉政权,从政治与军事的角度他也会永载史册,也必将会得到后世的赞美与歌颂,但他绝不会像项羽那样可以成为后世生命中永远的丰碑并得到永远的祭奠。这种祭奠远比赞美与歌颂更加的真诚动人,更加的可贵。赞美可以是口头上的,但祭奠却一定是内心的。
如果说刘邦是一篇政治军事的文章,那项羽就一定是一首境界高远的诗歌。而诗歌化的生命是一种天真、自由、率性的生态,洋溢着一种真诚、坦率的风度。
★作者单位:贵州省兴义市第四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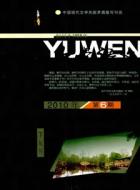
- 新课改 / 马顺云
- 语文教学中几个心理问题的探讨 / 贺兴进
- 新课标“语文素养”略探 / 曹 金
- 享受快乐,享受成功 / 陈树锦
-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与人格教育 / 陈业祥 李冬梅
- 高中语文教学节奏把握刍议 / 张代明
- 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学的几点反思 / 梁 文
- “说”的三种境界 / 黄海春
-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思考 / 凌云峰
-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几点缺失 / 鲁静萍
- 以诗意的眼光学习新课程语文 / 胡淑英
- 谈淡课改下的合作学习 / 陈跃生
- 高中语文课堂应融入时代气息 / 陈 磊 董玉叶
- 如何活跃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 / 杨建红
- 开放语文教学,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 李亚芳
- 构建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课堂 / 付和敏
- 用活“五要”,有益于语文教学的高效 / 雷许歆
- 新课程背景下的讨论式教学 / 张世虎
- 弥补思维缺陷 提高学生素质 / 杨奇平
- 自由的光辉 / 陈正喜
- 利用结课养成学生语文素养 / 宁守安
- 让语文教学走出低效之谷 / 胡建社
- 中学语文教学应重视“联想” / 李启荣
- 普通高中应该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 周剑英
- 对高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一些思考 / 张 波
- 试论有效阅读教学的策略运用 / 肖美香
- 情感是语文教学的润滑剂 / 李 旭
- 浅谈农村中学语文口语交际的教学 / 郑 阳
- “读” / 苏兴汉
- 初中语文激发学生情感的有效方法 / 佘晓芹
- 活动单导学:实现语文课堂高效教学的普适之路 / 丁国林
- 充分发挥文本“例子”作用提高语文阅读教学效率 / 周承旺
- 浅议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 / 林梦杰
- 以声演文 以诚会人 / 张志云
- 深入解读文本 还需咬文嚼字 / 石 璟
- 让课堂作文轻舞飞扬 / 蓝 玉
- 高中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初探 / 周旭东
- 授生以“鱼”,不妨授生以“渔” / 梁启堂
- 作绿色文 塑健康魂 / 陈惠红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阅读探究 / 徐 蕾
- 浅谈中小学应用文教学 / 佚名
- 让学生成为文言文阅读的主角 / 吴蔚华
- 中学作文教学现状及对策 / 陈佩洁
- 《故都的秋》的修辞及语法分析 / 陈明学
- 废弃与高歌 / 匡海霞
- 模糊思维的妙用 / 王先权
- 利用多媒体优化作文教学之我见 / 杨翠青
- 时代变迁中的中国妇女 / 刘梦霞
- 借助想象的力量,领会小说的思想 / 田丽维
- 让作文与网络同行 / 高正峰
- 感性\理性\诗意的互补与整合 / 张静媛
- 古典诗歌鉴赏引导方式探究 / 彭欣欣
- 浅谈我的作文教学 / 全 侠
- 试论赏析古典诗词的方法 / 樊培如
- 新课标下记叙文写作创新指导 / 王桂霞
- 《寡人之于国也》课堂实录及反思 / 李小丽
- 人生如何选择才有价值 / 赵茂云
- 心往彼处驰去 诗从对面飞来 / 吴先进 游卓亚
- 巧妇“善”为有米之炊 / 王旭平
- 《鸿门宴》中的传统文化常识摭谈 / 郑月丽
- 古典诗歌学习中的审美体验 / 王彩凤
- 描写反常人物 突出人物个性 / 甄慧云
- “断肠”是“销魂”吗? / 李秀江
- 议论尤需赋真情 / 杜 艳
- 一天风露藕花香 / 梅培军
- 年少的蜗牛没有壳 / 杨术明
- 文言文阅读中的信息筛选 / 郑 炜
- 与你结缘,我无悔 / 喻体芬
- 掀起你的盖头来 / 刘 建
- 利用教材资源,培养正确爱情观 / 何力群
- 2009 年高考作文命题分类浅析 / 李卫星
- 项羽悲剧的生命意义 / 吴贵阳
- 彰显个性,方显创新本色 / 柳志福
- 酒趣.寄情 / 武育新
- 考场作文取胜要素之思路篇 / 黄胜利
- 高考中常考易错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 / 向 军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龚玉梅
- 例谈长句变短句 / 郭清敏
- 加强分辨,强化规范 / 陈祥书
- 试述探究题有效解答的应对策略 / 周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