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5期
ID: 137282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5期
ID: 137282
伟大的“呐喊”
◇ 郭文生
【摘 要】看客这一艺术形象在鲁迅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看客的理解深度直接影响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深度。从这些麻木看客背后,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与担忧。鲁迅先生提笔“呐喊”,也正是为了唤醒这些沉睡的国民。
【关键词】鲁迅作品 看客 呐喊
鲁迅的小说作品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义在于‘解除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表现人生、改造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在《孔乙己》中看到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祝福》中看到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的鲁镇人……由此我们看到鲁迅振臂“呐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除了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外,还有由下层市民、留洋学生、三教九流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看客。
在《呐喊·自序》中,作者这样写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面自然也比较的多了,我在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作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中我们看出了作者“呐喊”的基调。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到晚年的书信、日记、杂文都有看客的形象出现,其涉及面之广是其他形象所没有的。看客构成了主人公活动的主要文化背景,决定着主人公的命运与作品的结局,因此看客这一艺术形象在鲁迅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看客的理解深度直接影响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深度。
看客有时作为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出现,如《药》中的驼背王老五、花白胡子,《阿Q正传》中居住在未庄的闲人们,《孔乙己》中的短衣帮。作为一个群体,看客的社会构成是耐人寻味的。从年龄层次看,看客老少俱全,上至颇具世故的花白胡子,下至不懂事的儿童。在《狂人日记》中,小孩也同成年人一样,成群结队,在背后议论狂人,给狂人以无形的压力,这不能不使狂人伤心且纳闷。看客们把别人的不幸当作热闹,在别人的不幸中寻找自己的高人一等,看客固有的观念与行为方式陈陈相因、代代相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链,使鲁迅笔下的看客给人一种纵深的历史感。从看客的社会身份来看,看客主要以下层农民为主体,同时也包括城镇居民和某些社会上流人士。在《孔乙己》、《阿Q正传》中,看客主要由下层农民的短衣帮、闲人们组成,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也以欣赏别人的痛苦为乐。
看客这一群体具有强烈的排他意识,而排他意识又来源于其本身固有的封建性。《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赔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他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留下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这些老女人们正是在欣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留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示病态的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这不仅是对人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灵魂的咀嚼。
在鲁迅笔下,看客出现的地点虽然在城镇、乡村间变化,但看客的活动范围却极其有限,基本上静止、停留在某一封闭的村庄、城镇或场景上。《阿Q正传》中的闲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未庄,对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因此遭到阿Q的蔑视、嘲笑。《药》中的老少看客虽然表现得相当活跃,却被鲁迅粘贴在华老栓的茶馆里,活动空间相当狭小。看客们足不出户,形成一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文化心理状态,他们与狭小的活动空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来如此”是他们所信奉的圭臬,因此对于任何异于“从来如此”的行为,他们都会视为一种异端,不能容忍。《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以及孔乙己、祥林嫂等,因为违反了“从来如此”的行为方式,也不能见容于看客们的世界中。值得注意的是,看客的这种吃人行为是在一种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们无法从自身出发去认识社会,也无法通过对社会的认识来反省自己。短衣帮们在嘲笑落魄的孔乙己时,不但没有起码的同情心,而且还不时爆发出阵阵快乐的笑声。柳妈接受了传统的迷信观念,她会在痛惜祥林嫂失去贞节的同时,给她指一条捐门槛的出路。从这一点说,对于祥林嫂的死,柳妈比鲁四老爷更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柳妈本人至死也不会明白承认这一点的。一旦人接受了某一种文化,他就会成为这种文化的俘虏,对接受的文化完全失去了抵御能力,看客们对封建文化的接受也是如此。这正是几千年来封建文化在中国国民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表现。
鲁迅先生对看客曾下过如此的断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都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是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从这些麻木看客背后,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与担忧。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一种怎样扭曲的人生!鲁迅先生提笔“呐喊”,也正是为了唤醒这些沉睡的国民。
★作者单位:甘肃省兰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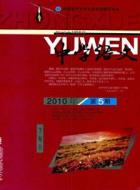
- 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毕琼湄
- 语文学习反思能力培养方法探析 / 朱道军
- 教学高潮是怎样炼成的 / 李 晖
- 语文新课改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 孙开虎
- 找准切入角度 引爆课堂思维 / 陈爱萍
- 语文教学“过程和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 苏发元
- 让“动态生成”演绎课堂的精彩 / 张小波
- 从问题走向问题意识 / 孟华群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王素贞
- 建构高中生态语文课堂的思考 / 刘晓红
- 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实效性教学初探 / 熊继文 丁 梦
- 对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研究与探索 / 何书毅
- 初中语文教学如何进行情感教育 / 刘国富
- 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探讨 / 卢燕平
- 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利与弊 / 张玉华
- 摒弃虚假繁荣,回归学生主体 / 姜秀丽
- 文言文教学应注重对“文”的讲解 / 李新宇
- 谈谈小说教学中学生探究意识的培养问题 / 杨宁强
- 个性化解读回归了经典 / 范玉红 于宏伟
- 《雷雨》(苏教版)周朴园形象教学设计 / 杨一波
- 模仿经典篇章 训练写作技能 / 容道荣
- 从《归园田居》看陶渊明的归隐境界 / 宋 云
- “生本”教育理念下语文阅读教学模式的探索 / 刘彩云
- 激活材料的方法例说 / 戴家华
-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 李 超
- 关于阅读教学目标问题的思考 / 王万忠 张新慧
- 如何指导学生美化语言 / 胡爱琼
- 论《 种树郭橐驼传 》中人物形象的独到之处 / 杨秀香
- 通过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 杜 瑞
- 例谈句式在写作中的运用 / 暴俊民
- 再造形象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能力 / 刘春霞
- 阅读教学中的几种不良倾向 / 李姗苗
- 真情为文, 细节先行 / 席孝艳
- 玛蒂尔德新论 / 万元洪
- 浅谈猜读法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应江
- 变被动为主动,提倡多写随笔 / 徐 聪
- 读《报任安书》札记三则 / 李曰夏
- 比较阅读 / 黄京琛
- 初中生应用文写作能力欠佳的原因初探 / 程小华 刘清兰
- 作文应该具备的本质理念 / 徐可文
- 关于落实课外阅读的探索和实践 / 刘洁梅
- 走出作文批改的泥淖 / 李 阳
- 作文中如何创新 / 王根军
- 敢于拆分 巧妙整合 / 李慧婉 卢俊勇
- 启发性批语初探 / 李永强
- 文章的写作技法 / 曲 斌
- 从《论语》看孔子的答疑智慧 / 汪荣富
- “转身”新材料作文导写及例文 / 吴和华
- 新课程改革带来的新思考 / 付伶俐
- 浅谈陶渊明诗中所蕴含的诗性智慧 / 李冬慧
- 经纬纵横交织 推断文言实词 / 黄胜利
-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四重四轻” / 张桂霞
- 试论李白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 梁思强
- 破解古代诗歌思想感情密码 / 陈宽明
- 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进行语文基本功训练 / 曹安杨
- 李白七言歌行体诗艺术特色浅析 / 杨云超
- 找准支点,让作文更容易 / 卢文锋
- 语文教学应在读读写写中循序渐进 / 彭 弢
- 试论白居易的诗论 / 王自荣
- 让你的作文文采飞扬 / 胡国俊
- 善待语文, 提升素养 / 胡 慧
- 唐孙过庭《书谱》赏析 / 张 帆
- 两则材料作文训练示例 / 刘占悦 翟凤举
- 一节好课的四个达成 / 王本辉
- 浅析《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 / 叶芬芳
- 诗性唯美与理性世俗 / 颜 敏
- 尊重的艺术 / 杨志发
- 伟大的“呐喊” / 郭文生
- 问渠哪得清如许 / 王 五
- 语文,让诗意栖居 / 康素娟
- 教会学生紧紧围绕三要素解读小说 / 杨 林
- 对语文新课改之路的思考 / 欧阳超
- 巧抓标志词语 快速辨析病句 / 张承香 张兴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