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5期
ID: 137236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5期
ID: 137236
从《归园田居》看陶渊明的归隐境界
◇ 宋 云
【摘 要】《归园田居》是集中反映陶渊明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作品以冲淡、平和的笔调在写景抒情中表达其归隐志趣,充分体现出古代文人一种难得的归隐境界——现实性的身隐。陶渊明的归隐超越了归隐本身,是人格的重塑和精神的涅槃,提升了人们对文人归隐生活的认识。
【关键词】陶渊明 归隐 人格重塑 精神涅槃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普遍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在古代文学史上,多数文人是内心有归隐之意(意隐),心系田园山林,而身在市井宫廷,很难从根本上割舍红尘俗世,达到心随物(物欲)外、物(自然)我相融的做人境界。而被誉为隐者,长期远离官场闹市、隐身田园(身隐),并能自耕自足的文人,是较少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不计荣辱贫富,清心寡欲,怡然自得,是高洁之士的典型。从意隐到身隐,是古代文人归隐的两种不同境界。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作品在写景抒情中表达其归隐志趣,充分体现出古代文人一种难得的归隐境界——现实性的身隐。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杂诗》第五首)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在二十九岁抱着明君贤臣的理想进入仕途。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但在那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陶渊明本有爱慕自然的思想,而在老庄思想和隐逸之风的影响下,这种对自然的爱慕表现为对隐逸的企慕。因此,当仕途不得志时,这种思想便常常刺激着他。十二年中,他抱着希望出仕,碰壁、失望、归隐,然而他没有死心,再抱着希望出仕,再碰壁、再失望、再归隐,先后三仕三隐,任过江州祭酒、桓玄的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直到四十一岁那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二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二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二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一生以彭泽辞归为界,经历着两种不同的道路。前期过着仕隐不定的生活,他的心境也很难真正平静,尽管仕途坎坷,他仍在不断实践着一个传统文人年轻时共有的理想追求,思想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矛盾徘徊。黑暗的现实令他绝望,酷爱自由的本性亦让他彻底走上了长期归隐道路。如果说前期他的归隐只能算是一种意隐的话,那么,后期他已超越了这种寻求暂时安宁的理想化的向往境界,让身与心共同投入田园山水的怀抱,让理想变为现实,让意隐融入身隐,充分享受那份难得的悠闲和自在。这是他历经岁月坎坷后,为守护精神家园而做出的人生的重大抉择。他不像一般人那样观山川以悦目,他是把田园自然风光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是在看透了官场的腐败黑暗之后转向大自然而获得的一种觉悟。这种觉悟是用人格生命换来的,因而他格外珍视。他的归隐没有强迫和苦痛,更多的是从容和豁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亲身躬耕,体验农事,乐于与布衣交往,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确是古代文人高洁人格的典范。
《归园田居》是最能体现其归隐境界的佳作,写于辞去彭泽县令的第二年。用语朴实、亲切,纯为白描,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清新、自然的田园风情图,平淡中有情趣,悠远中有真味,能从不起眼的田园生活中领略出引人共鸣的兴致。这是身隐田园,细心体验、观察的结果,非意隐想象能描摹的境界。
这是一组诗,共五首。第一首写诗人辞官归隐的原因以及归隐后的恬静生活和愉悦的心情。诗人仅把“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烟”、“犬吠”、“鸡鸣”等农村常见的意象罗列在诗中,却有置身田园、轻松脱俗的乐趣生诸笔端,远近互衬,动静结合,创造了分外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格调质朴、明快,弥漫泥土气息,情真意切,“均非尘世吃烟火食人语”(方东树《昭昧詹言》)以如此天籁之音写归田之乐,实乃意隐和身隐境界之大不同。诗人把官场生活喻为“尘网”、“樊笼”,与田园生活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对照,语言感情色彩分明。“‘返自然’三字,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事事俱违本性”(查初白《初白庵诗评》)。
第二首、第三首写归隐后的闲居、劳动生活和感受。从事劳作,这是为古代多数文人士大夫所轻视的,尤其在士族门阀风气甚重的魏晋时期,则更表露无遗。陶渊明却不以为然,抛开俗念,走上田头,从而也体会到一般文人不曾有过的归隐感受。“劳动是艰辛的,而且劳动所得未必真能使他丰衣足食,但他是把劳动与坚持隐居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千载之前的长沮、桀溺不正是坚持着隐居的人生,又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吗?隐居既然是自己的人生理想,劳动便是隐士生活的重要内容了。”(郭兴良《中国古代文学》)诗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起早贪黑,辛苦劳作。不计“道狭”,不计“露沾”,心内唯念农事,担心天气的变化,“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样的生活状态已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儒士生活。尽管如此,他仍然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心中唯念“但使愿无违”。从这儿,我们可看出,他舍得放下文化人的架子,以全新的姿态抛弃了一般文人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清高,而以另一种质朴、自然的清高捍卫了精神上的自由和高洁。他的归隐超越了归隐本身,是人格的重塑和精神的涅槃。
第四首写诗人外出郊游时所看到的农村残败凄凉的景况,感慨人生无常,客观上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饱含对社会、人生的进一步认识。与农民的亲近使他对农民的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而不是一味沉浸在一般文人虚设的意隐境界中,自求其乐。他和农民平等相处,友善相待,一起劳作,一起饮酒。第五首便生动描写了他杀鸡备酒和邻居通宵宴饮的乐趣。身入田园,心胸的无拘无束、宽广醇厚都在欢饮中尽情显现。“荆薪代明烛”更使宴饮有田家风味。这种饮酒之乐也不同于一般文人相邀胜地、举杯共酌的闲情逸致,而是平凡生活中你来我往的随意性情,乐即开怀痛饮,无官场应付之劳心,非身隐无以体验。
《归园田居》一洗文人笔下意隐的浪漫和瑰丽色彩,以冲淡、平和的笔调构筑了陶渊明全身心融入田园的归隐境界。陶渊明从属于文人,而不同于一般文人,他把文人的清高淡雅用最质朴的文字得以抒发,从而提升了人们对文人归隐生活的认识,这也是多年来,人们把他称为真正的隐士的原因所在,人们所敬仰的也正是他那种守节情不移、穷且益坚的身隐境界。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持,是一种难得的做人境界。
★作者单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教育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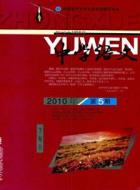
- 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毕琼湄
- 语文学习反思能力培养方法探析 / 朱道军
- 教学高潮是怎样炼成的 / 李 晖
- 语文新课改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 孙开虎
- 找准切入角度 引爆课堂思维 / 陈爱萍
- 语文教学“过程和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 苏发元
- 让“动态生成”演绎课堂的精彩 / 张小波
- 从问题走向问题意识 / 孟华群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王素贞
- 建构高中生态语文课堂的思考 / 刘晓红
- 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实效性教学初探 / 熊继文 丁 梦
- 对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研究与探索 / 何书毅
- 初中语文教学如何进行情感教育 / 刘国富
- 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探讨 / 卢燕平
- 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利与弊 / 张玉华
- 摒弃虚假繁荣,回归学生主体 / 姜秀丽
- 文言文教学应注重对“文”的讲解 / 李新宇
- 谈谈小说教学中学生探究意识的培养问题 / 杨宁强
- 个性化解读回归了经典 / 范玉红 于宏伟
- 《雷雨》(苏教版)周朴园形象教学设计 / 杨一波
- 模仿经典篇章 训练写作技能 / 容道荣
- 从《归园田居》看陶渊明的归隐境界 / 宋 云
- “生本”教育理念下语文阅读教学模式的探索 / 刘彩云
- 激活材料的方法例说 / 戴家华
-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 李 超
- 关于阅读教学目标问题的思考 / 王万忠 张新慧
- 如何指导学生美化语言 / 胡爱琼
- 论《 种树郭橐驼传 》中人物形象的独到之处 / 杨秀香
- 通过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 杜 瑞
- 例谈句式在写作中的运用 / 暴俊民
- 再造形象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能力 / 刘春霞
- 阅读教学中的几种不良倾向 / 李姗苗
- 真情为文, 细节先行 / 席孝艳
- 玛蒂尔德新论 / 万元洪
- 浅谈猜读法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应江
- 变被动为主动,提倡多写随笔 / 徐 聪
- 读《报任安书》札记三则 / 李曰夏
- 比较阅读 / 黄京琛
- 初中生应用文写作能力欠佳的原因初探 / 程小华 刘清兰
- 作文应该具备的本质理念 / 徐可文
- 关于落实课外阅读的探索和实践 / 刘洁梅
- 走出作文批改的泥淖 / 李 阳
- 作文中如何创新 / 王根军
- 敢于拆分 巧妙整合 / 李慧婉 卢俊勇
- 启发性批语初探 / 李永强
- 文章的写作技法 / 曲 斌
- 从《论语》看孔子的答疑智慧 / 汪荣富
- “转身”新材料作文导写及例文 / 吴和华
- 新课程改革带来的新思考 / 付伶俐
- 浅谈陶渊明诗中所蕴含的诗性智慧 / 李冬慧
- 经纬纵横交织 推断文言实词 / 黄胜利
-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四重四轻” / 张桂霞
- 试论李白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 梁思强
- 破解古代诗歌思想感情密码 / 陈宽明
- 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进行语文基本功训练 / 曹安杨
- 李白七言歌行体诗艺术特色浅析 / 杨云超
- 找准支点,让作文更容易 / 卢文锋
- 语文教学应在读读写写中循序渐进 / 彭 弢
- 试论白居易的诗论 / 王自荣
- 让你的作文文采飞扬 / 胡国俊
- 善待语文, 提升素养 / 胡 慧
- 唐孙过庭《书谱》赏析 / 张 帆
- 两则材料作文训练示例 / 刘占悦 翟凤举
- 一节好课的四个达成 / 王本辉
- 浅析《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 / 叶芬芳
- 诗性唯美与理性世俗 / 颜 敏
- 尊重的艺术 / 杨志发
- 伟大的“呐喊” / 郭文生
- 问渠哪得清如许 / 王 五
- 语文,让诗意栖居 / 康素娟
- 教会学生紧紧围绕三要素解读小说 / 杨 林
- 对语文新课改之路的思考 / 欧阳超
- 巧抓标志词语 快速辨析病句 / 张承香 张兴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