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5期
ID: 137251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5期
ID: 137251
读《报任安书》札记三则
◇ 李曰夏
【摘 要】《报任安书》中,“牛马走”句中的“牛”应当是“先”之误字;“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句中的“与”如释为“称许,认可”,“比”字则应删去,不删,“与”只能释为“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句,有数例使用不当。从有关史料来看,似乎司马迁起初并非被处以腐刑,而是“自请腐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司马迁遭受到的精神压力是超出人们所想象的。
【关键词】《报任安书》 考证 指谬 探疑
一、考证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于《汉书·司马迁列传》,与《文选》所录,字句稍异,如《文选》中首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即不见于《汉书》。历来注释都沿用李善《文选》注,释“牛马走”为“像牛马一样奔走的仆役”。实际上,“牛”应当乃“先”之误字。
据《庄子》、《荀子》考证古代天子出行,诸侯为“先马”,《淮南子》中有这样的句子:“越王勾践亲执戈为吴王先马走。”后世太子仪卫中的“洗(读作xiǎn)马”,即“先马”。例如晋李密《陈情表》称:“寻蒙国恩,除臣洗马。”又“先马”与“前马”同义。《国语·越语上》写道:“其身亲为夫差前马。”“先马”初为举动而后为职衔。那么“先马走”犹后世所谓“马前走卒”,和古代书札中自谦为“下走”、“仆”一样。“太史公”为司马迁官衔,“先马走”为司马迁谦称,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考以官衔置谦称前,如泰山刻石“丞相臣斯”,正是确例,足以纠正李善的曲解。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清人王念孙考证,“与,犹谓也”,而“比”乃后人妄加。高中语文教材第六册中解释“与”为“称许,认可”,这解释基本沿用了王念孙的说法。不过,教材对本句后面的“比”置之不理,因为将“与”解释“称许,认可”,而“比”无论如何也讲不通。如果不删去“比”字,此句“与”应解释为介词“和”。
二、指谬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此段文字历来为人所称道,岂不知其中有数例使用不当。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即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创作,怎么会自己破坏自己立的规矩而“作春秋”,周文王“演周易”更是不可据之传说。退一步讲,这两例在当时被认为是真的,司马迁用之尚可原谅,吕不韦和韩非两例就怎么也说不通了。《史记》记载《吕览》作于吕不韦相秦之时,《说难》、《孤愤》也是韩非未入秦时所作,这不是自相违背吗?再者,《史记》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号曰《吕氏春秋》”,这是掠人之美,司马迁将自己“发愤之为作”匠心独运之“一家之言”,比作吕不韦集众人之手的“百衲本”,实在不伦。
三、探疑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揣摩辞意,似乎司马迁起初并非被处以腐刑,而是死刑。否则上面几句实难索解。清代赵铭曾说:
夫迁以李陵得罪,迁但欲护陵耳,非有沮贰师意也。帝怒其欲沮贰师而为陵游说,则迁罪更不容诛。以武帝用法之严,而吏傅帝意以置迁于法,迁之死尚得免乎?汉法,罪当斩赎为庶人者,唯军将为然;而死罪欲腐者许之,则自景帝时为令。张贺以戾太子宾客,当诛,其弟安世为上书,得下蚕室,是其明证。迁惜《史记》未成,请减死一等就刑,以继父谈所为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诛,然则迁之下蚕室,出于自请无疑也。
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汉书·景帝纪》记载:“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汉书·武帝纪》说:“天汉四年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又:“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这所谓“减死一等”,即指改为宫刑。“沮贰师”尚属触武帝之怒,罪不至死;“诬上”却是罪不容诛的罪名。看来早有人怀疑司马迁是“自请腐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司马迁在当时受到世人的讥笑,是可以想见的。司马迁所遭受到的精神压力更是超出现代人们所想象。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说过这样的话:“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者何?一日下蚕室,疮未瘳而宿卫人主,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盐铁论·周秦》)这里所说的和司马迁的遭遇很相像。
★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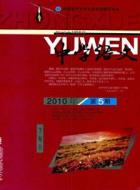
- 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毕琼湄
- 语文学习反思能力培养方法探析 / 朱道军
- 教学高潮是怎样炼成的 / 李 晖
- 语文新课改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 孙开虎
- 找准切入角度 引爆课堂思维 / 陈爱萍
- 语文教学“过程和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 苏发元
- 让“动态生成”演绎课堂的精彩 / 张小波
- 从问题走向问题意识 / 孟华群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王素贞
- 建构高中生态语文课堂的思考 / 刘晓红
- 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实效性教学初探 / 熊继文 丁 梦
- 对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研究与探索 / 何书毅
- 初中语文教学如何进行情感教育 / 刘国富
- 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探讨 / 卢燕平
- 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利与弊 / 张玉华
- 摒弃虚假繁荣,回归学生主体 / 姜秀丽
- 文言文教学应注重对“文”的讲解 / 李新宇
- 谈谈小说教学中学生探究意识的培养问题 / 杨宁强
- 个性化解读回归了经典 / 范玉红 于宏伟
- 《雷雨》(苏教版)周朴园形象教学设计 / 杨一波
- 模仿经典篇章 训练写作技能 / 容道荣
- 从《归园田居》看陶渊明的归隐境界 / 宋 云
- “生本”教育理念下语文阅读教学模式的探索 / 刘彩云
- 激活材料的方法例说 / 戴家华
-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 李 超
- 关于阅读教学目标问题的思考 / 王万忠 张新慧
- 如何指导学生美化语言 / 胡爱琼
- 论《 种树郭橐驼传 》中人物形象的独到之处 / 杨秀香
- 通过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 杜 瑞
- 例谈句式在写作中的运用 / 暴俊民
- 再造形象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能力 / 刘春霞
- 阅读教学中的几种不良倾向 / 李姗苗
- 真情为文, 细节先行 / 席孝艳
- 玛蒂尔德新论 / 万元洪
- 浅谈猜读法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朱应江
- 变被动为主动,提倡多写随笔 / 徐 聪
- 读《报任安书》札记三则 / 李曰夏
- 比较阅读 / 黄京琛
- 初中生应用文写作能力欠佳的原因初探 / 程小华 刘清兰
- 作文应该具备的本质理念 / 徐可文
- 关于落实课外阅读的探索和实践 / 刘洁梅
- 走出作文批改的泥淖 / 李 阳
- 作文中如何创新 / 王根军
- 敢于拆分 巧妙整合 / 李慧婉 卢俊勇
- 启发性批语初探 / 李永强
- 文章的写作技法 / 曲 斌
- 从《论语》看孔子的答疑智慧 / 汪荣富
- “转身”新材料作文导写及例文 / 吴和华
- 新课程改革带来的新思考 / 付伶俐
- 浅谈陶渊明诗中所蕴含的诗性智慧 / 李冬慧
- 经纬纵横交织 推断文言实词 / 黄胜利
-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四重四轻” / 张桂霞
- 试论李白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 梁思强
- 破解古代诗歌思想感情密码 / 陈宽明
- 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进行语文基本功训练 / 曹安杨
- 李白七言歌行体诗艺术特色浅析 / 杨云超
- 找准支点,让作文更容易 / 卢文锋
- 语文教学应在读读写写中循序渐进 / 彭 弢
- 试论白居易的诗论 / 王自荣
- 让你的作文文采飞扬 / 胡国俊
- 善待语文, 提升素养 / 胡 慧
- 唐孙过庭《书谱》赏析 / 张 帆
- 两则材料作文训练示例 / 刘占悦 翟凤举
- 一节好课的四个达成 / 王本辉
- 浅析《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 / 叶芬芳
- 诗性唯美与理性世俗 / 颜 敏
- 尊重的艺术 / 杨志发
- 伟大的“呐喊” / 郭文生
- 问渠哪得清如许 / 王 五
- 语文,让诗意栖居 / 康素娟
- 教会学生紧紧围绕三要素解读小说 / 杨 林
- 对语文新课改之路的思考 / 欧阳超
- 巧抓标志词语 快速辨析病句 / 张承香 张兴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