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期
ID: 353505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期
ID: 353505
过河卒子
◇ 周京昱
《中学语文教学》对我,恩重如山。
一
十三四年前,在最不知天高的年龄上,我在中学里混一碗饭;而真实的心理是“良禽择木而栖”,梦想着有机会脱离苦海。其实,学校对我挺够意思,大学毕业第二年就遣我“由幽谷迁乔木”——从初一翻个筋斗直接任教高三。在一年当五年使的那个1996年,我心无旁骛,除了想办法降服学生和家长外,也进行着一名新任教师的思想改造——“原来高考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中学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师是这个样子的”……
那届学生送走了,考得很不错,我却高兴不起来:一是1997年高考语文学科整体兵败滑铁卢,由此为发端旋即展开了一场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大讨论乃至大批判;二是两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他人六年才能经历的一切,误以为中学语文教学不过如此——特别是高考使我的文学教育梦严重受挫。那一段日子,我一边将这两年里对教育的种种看法写成一部七八万字的中篇小说,一边琢磨着是不是该重新选择生活,干点儿别的。
正当我百无聊赖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是我大学时的论文指导老师臧博平先生打来的。当年,每个毕业生的论文按规定不少于五千字,我竟然一口气分章节写了近十万,害得身材壮硕的臧先生整个夏天都没有过好,看我一个人的作业就相当于给二十个学生做导师,他又认真,一个句子也不肯放过。至今想来,我还常感愧疚。臧老师电话的意思很简单,他说有一篇文章,我来写最合适。我这才知道他已就任《中学语文教学》主编,这篇文章就是这家全国中语界重量级杂志要的。
我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姻缘,由此始。
那篇对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做出解读的文章,各方面反映还不错。事后臧老师对我说,你能写,为什么不拿起笔来闯出一条路呢?如果你还能像上学时那样信赖自己这支笔,你的工作、生活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安于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里做一个卒子,始于《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篇文章和这次谈话。这以后,我从《中学语文教学》中学到很多东西,平凡的精神世界寻到了一种向上的支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全国同类杂志并不少,但像《中学语文教学》这样深刻、大气、严肃,有格调、有尊严、有肚量的刊物并不多见。她不故作惊人语以蛊众,也不投时尚所好以媚俗,更不一味歌功颂德以媚上。安安静静谈语文,从从容容说教学,平平实实话教改,大大方方道争锋——这份神闲气定是很罕见的。
二
由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巨大影响,我被认为有一定的研究能力,1999年由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变成北京最年轻的区级教研员。造化弄人,偏偏搞的是高考——当年我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码子事。做教研员三四年了,我始终怀疑自己干着难登大雅之堂的勾当;只是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对我来说,写作是麻痹自己、与际遇和解的最好方式。2003年,《中学语文教学》责任编辑张蕾老师约我写一篇谈自己成长之路的文章,并要求提供照片。当时我正沉浸在高考模拟题中难以自拔,想来想去除了几年来炮制的各种试题之外,实在乏善可陈。遂决定用散文的笔法遮羞,用朦胧的文字述说自己对语文教学同样朦胧的认识。那篇文章就是迄今为止我业务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地琐屑》。2003年第4期文章刊出后,我接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山东烟台一位姓王的老师谈了他(她?)对中学语文教师生存状态的真实看法,最后写道:不寄希望能与你做双向的交流,只是你的文字使我有一种想倾吐的感觉……
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作者的幸福吧。那期杂志的封二登了我的照片,我很少照相。只好将自己结婚时的一张便装照给了张蕾老师,我宁愿把它看做一个年轻人在最幸福的岁月里特别献给《中学语文教学》的。
其实,《一地琐屑》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有多少人知道了我;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终于看清了自己是怎么回事,终于觉得我的工作价值不在单纯的文学教育之下。教学评价是教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有人批评“应试教育”,对“考是法宝,分是命根”很不屑,我自己也跟着瞎说。几年下来,我终于明白,尽管高考不是语文教学的全部,但它终究是伟大的——不仅在于它能改变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令人重新思考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核心价值和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定位。此中真意,又将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了。
安于在考试研究领域里做一个卒子,于我而言,同样始于《中学语文教学》。
三
时间过得很快。从二十七岁做教研员到今年。我摆弄高考整整十年了。在北京城区毕业班教研员的岗位上,十年如一日做这样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我与高考的关系,用冯小刚的一本书名来表达再恰当不过——“我把青春献给你”。这十年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忽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学语文教学》和《中国考试》这两个中国第一流的专业刊物是我寻求业务成长的向上阶梯。一位读过我的文章的陌生朋友说,我一直以为你至少得有五十岁了。不过这倒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我将自己最成熟最看重的想法诉诸文字,交给了这两家刊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对我来讲,再真实不过。在《中学语文教学》面前,我得格外爱惜自己的名誉。
2008年,我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姻缘又近了一层。蒙她的抬举,我有幸出任“测试与评价”这个栏目的特约编辑。这一年来,我拜读了大量考试研究方面的来稿,获益匪浅。同时,经我手也“毙掉”了很多稿子。《中学语文教学》有自己的风格和要求,我必须将个人好恶关在门外。有时候,为了“打捞”一篇有价值的稿子,我不得不帮助作者进行完善、修改。尽管改稿子是件费力不一定讨好的活儿,但为了《中学语文教学》这块金字招牌,每一个从业者不敢怠慢,也没脸苟且。
在从作者到编者的演变中,我突然有一个发现:稿件阅读量竟与自己的写作速度成反比。稿子看得越多,自己反而写得越慢。先前。下笔千言,不过须臾;而现在,常常是思前想后,慢慢吞吞,一个词颠来倒去也要安顿半天,甚至常常产生一种幻觉——四壁皆人,满屋都是质疑的目光与口诛笔伐的声浪,尽管内心异常平静但手心里全是汗。渐渐地,我竟然喜欢上了这样一种写作的感觉,且固执地认为,在高考研究领域,之所以有分量的文章还不够多,除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作者们的鼠标用得太熟练了。而手心里很少出汗。
北京一位前辈教研员赵大鹏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语文教师的任何一丝中气不足,都可以在命题和评题中显露出来,我们测试评价学生的同时也是在测试评价自己;我们身处的环境无论一时如何狂热,最终是需要林教头而非洪教头的。
看得多了,经得多了,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睿智。所以常常提醒自己:别发飘,离一线老师们近一点儿,再近一点儿;“理念”并不会使一个人突然变得高大,好好干活儿,别耽误你和他人的时间。如果说《中学语文教学》“测试与评价”栏目这一年来有点什么变化,就是力求离广大一线教师更近一些,这源于编者对业务尤其是对生活的理解。
安于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行列里做一个卒子,演一出真诚的“纸为媒”,于我而言,依然始于《中学语文教学》。
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我的体会:《中学语文教学》的意义,不在于她能直接给你什么,更重要的是她能够促使你变成什么。
一个刊物,捧起许多人。回首来路,面对《中学语文教学》,除了乌鸦反哺之心外,我时常告诫自己:检点你的言行,别辜负曾经看好你的人们……
十几年过去了,渡过狂热之河,我还是那枚卒子,左支右绌,左突右杀,总之没有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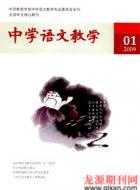
- 呼唤否定和超越 / 张 蕾
- 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一声“惊雷” / 佚名
- 吕叔湘先生的一次重要讲话 / 陈金明
- 当年謦欬犹在耳 / 黄厚江
- 当代语文课堂的“现代病”分析及诊治(上) / 严华银
- 教学艺术 / 余映潮
- 让诗歌充满你的灵魂 / 刘 淼 陈 灿 华 耿 会 芹
-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基础 / 吴永军
- 什么叫读懂了课文 / 牟 靖 李海林
- 新课程视野下的写作知识教学 / 曹勇军
- 略谈苏教版必修教材中写作知识的教学 / 石群英
- 《创造形 / 王 媛
- “散文之部”如何教? / 褚树荣
-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整体感知 / 陆精康
- 倾听那一声婉曲而深沉的叹息 / 时剑波
- 两个“雪藏”:一个温柔,一个刚烈 / 徐社东
- 生命的歌吟 / 张 悦
- 《藤野先生》第一教时教学设计 / 姚友良
- 《装在套子里的人》教学设计两则 / 徐昌才 李惠珍
- 关联词语位置的四种情况 / 严建军
- “潦倒”补注 / 史复明
- “卓异”应如何解释 / 马庆然
- 语文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性质和地位的探讨 / 刘 华
- 语文高考“怎么考” / 潘新和 郑秉成
- 从考纲和试卷的变化看新课程高考语文的走向 / 张新强
- 中考现代文阅读核心能力管窥 / 王轩蕊
- 他山之 / 卢吉增
- 《中学语文教学》带我成长 / 孙移山
- 过河卒子 / 周京昱
- 富有挑战性的美国高中AP类课程(四) / 郭英剑
- 钱理群先生“鲁迅专题学术报告会”在京举行 / 吴 东
- 《语文教师成长丛书》评介 / 周红心
- 总结经验,遵循规律,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 古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