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期
ID: 353497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期
ID: 353497
“潦倒”补注
◇ 史复明
明清白话虽然较为浅近,但是与现代汉语毕竟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当明清的白话小说选人中学语文教材的时候,还是需要人们对文中所涉及的古今异义词作必要的注释,否则极可能以今律古而误解文义。
《林黛玉进贾府》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名篇。其中有《西江月》词两首,第一首中有“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这样两句。对于词中的“潦倒”两字几乎所有的中学教材都没作注释,显然把它看做是一个古今意义变化不大的词,也即“颓丧失意”的意思。有的鉴赏资料如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则直接把“潦倒”注作“失意”。
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从句子的停顿角度来看,应作:“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停顿的前后两部分之间应该是一种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愚顽”的具体表现是“怕读文章”,而宝玉“怕读文章”的行为反映了他“愚顽”的个性;同样道理,宝玉“潦倒”的具体表现是“不通世务”,而“不通世务”的行为正是反映了他“潦倒”的个性。显然这里的“潦倒”所指的应该是人物的一种性格特征,而不是一种“潦倒失意”的人生处境。
再从两首词所表达的内容来看,第一首词侧重表现宝玉的“乖张”个性和“无故寻愁觅恨”的“偏僻”行为,在第二首词中才涉及到人生的顺逆处境,“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所以用“潦倒失意”来解释“潦倒”恐怕与词作原意相违。
那么“潦倒”两字究竟该作怎样的解释呢?启功先生等人校注的《红楼梦》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潦倒,这里是举止不知检束的意思。”
把“潦倒”解释成“举止不知检束”首先是有辞书上的依据的。在权威的辞书如《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中都明确列有“举止散漫,不自检束”这一义项。杜甫《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昨日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王绩《答秦道士书》:“吾受性潦倒,不经世务。”这两处中的“潦倒”所用的正是这一意思。
其二,这样的解释也是符合上下文语境的。从行文来看,“潦倒不通世务”与“愚顽怕读文章”两句构成了对文关系。如果说“怕读文章”反映的是宝玉对时文八股的自觉的拒绝的话,那么“不通世务”所反映的是他对“经济仕途”的极端厌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宝玉的行为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愚顽不化”和“潦倒放纵”是在所难免的。就作者的情感态度而言,《西江月》中的“潦倒”和“愚顽”恰恰是曹雪芹对宝玉叛逆性格的赞美。所以把“潦倒”解释成“举止散漫,不自检束”,在文义上是能说通的。
其三,这样的解释还有一处很好的旁证。那就是《红楼梦》第二回中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发表的“正邪两赋论”,列举了很多人物。这些人物虽然时代、地位、身份不同,但其禀赋的本质确是一样的,“俱是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其中的嵇康,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评价自己的性格“潦倒粗疏,不切事情”(《与山巨源绝交书》)。而“潦倒粗疏”也就是放荡不羁的意思,《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在“潦倒”这一条目下,正是引用该例句来说明“举止散漫,不自检束”这一义项。嵇康和贾宝玉同属正邪两赋类人物,“不通世务”和“不切事情”的意思完全相同,可见宝玉的“潦倒”也就是嵇康的“潦倒粗疏”了。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教材编者对“潦倒”两字加注:“潦倒,这里是举止不知检束的意思。”否则极易让人产生以今律古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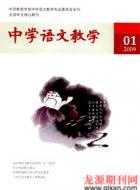
- 呼唤否定和超越 / 张 蕾
- 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一声“惊雷” / 佚名
- 吕叔湘先生的一次重要讲话 / 陈金明
- 当年謦欬犹在耳 / 黄厚江
- 当代语文课堂的“现代病”分析及诊治(上) / 严华银
- 教学艺术 / 余映潮
- 让诗歌充满你的灵魂 / 刘 淼 陈 灿 华 耿 会 芹
-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基础 / 吴永军
- 什么叫读懂了课文 / 牟 靖 李海林
- 新课程视野下的写作知识教学 / 曹勇军
- 略谈苏教版必修教材中写作知识的教学 / 石群英
- 《创造形 / 王 媛
- “散文之部”如何教? / 褚树荣
-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整体感知 / 陆精康
- 倾听那一声婉曲而深沉的叹息 / 时剑波
- 两个“雪藏”:一个温柔,一个刚烈 / 徐社东
- 生命的歌吟 / 张 悦
- 《藤野先生》第一教时教学设计 / 姚友良
- 《装在套子里的人》教学设计两则 / 徐昌才 李惠珍
- 关联词语位置的四种情况 / 严建军
- “潦倒”补注 / 史复明
- “卓异”应如何解释 / 马庆然
- 语文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性质和地位的探讨 / 刘 华
- 语文高考“怎么考” / 潘新和 郑秉成
- 从考纲和试卷的变化看新课程高考语文的走向 / 张新强
- 中考现代文阅读核心能力管窥 / 王轩蕊
- 他山之 / 卢吉增
- 《中学语文教学》带我成长 / 孙移山
- 过河卒子 / 周京昱
- 富有挑战性的美国高中AP类课程(四) / 郭英剑
- 钱理群先生“鲁迅专题学术报告会”在京举行 / 吴 东
- 《语文教师成长丛书》评介 / 周红心
- 总结经验,遵循规律,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 古 晔
